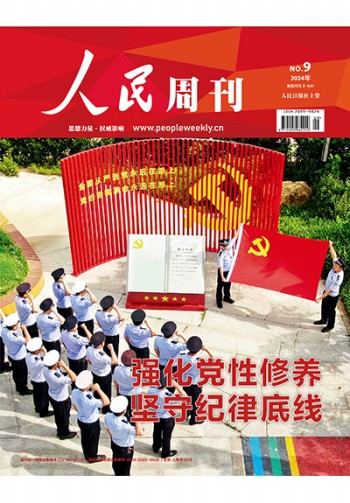尽管诞生背景和根植土壤有着巨大的时空差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某些方面依旧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内在亲和力与契合融通性。相关研究经多年积淀,在“第二个结合”提出尤其是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召开以来,呈现出井喷之势。然而,占比较大的整全之研究难免于精深有损,各有侧重的小切口透视日渐占据重要地位,自然观便因其基础性、重要性而成为其中代表。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其劳动本体论的基础上,通过“人化自然”命题打破了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僵硬对立,自此奠基了自然史与社会史融通的全新世界观——唯物史观。“天人合一”也是传统文化之中一个重大而根本的命题,这一论断自先秦以降影响了中国社会数千年,其中蕴藏着中华文明的核心特质。因此,本文尝试以“人化自然”和“天人合一”两个命题为核心,分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自然观视域下的契合与差异,以期一叶知秋,从中把握“第二个结合”的内在机理与深刻意蕴。
客观实存:自然观中的共同前提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将人与自然的实存当作前提,而不作将二者抽象掉的假设。马克思、恩格斯是以“现实的人”作为起点和基点,构筑起整个唯物史观的大厦。自然界的先在性和实在性是“现实的人”的存在前提,自然界的客观实存便从人本身中得到证明。此外,人与自然的实在性,实际上又是可直接经验到的简单事实。而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也贯穿着现实倾向,因而我们在思想中随处可见朴素的唯物观点。以被称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的《周易》为代表,我们可以清晰看到,承载了物质自然的“天”是最初的存在、是万物之始,构成了人在内的世间万物生成和存在的基础。这里,一方面,现实的、有生命的人的存在是立论前提;另一方面,由于自然界是人的存在前提、也是人可经验的现实,客观实存的自然界的先在性得到理论体认。
一体同构:自然观中的契合论断
在确认了人与自然共同的客观存在之后,一个必然涉及的问题便是二者关系的厘清。代表性的对立观点是通过“主—客”框架中的隔离方式实现的,而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通的一点则是“人—自然”的统一与结合。但“统一”的论断若绝对化又必然与不可避免的、时而以自然灾害等形式凸显的对立现实有所矛盾,因此,就方法论而言,马克思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同贯彻了同一分析方法——辩证法。与马克思认为的人是受动性和能动性统一的论断相契合,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表性命题的“天人合一”展现的人与自然关系也是辩证统一的。
在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视域下,一方面,由于自然界构成了人的外在环境和资料来源,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在生产、生活各方面都必然受到自然界的影响,且这一影响是客观的、物质的、不受人任意支配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另一方面,人与动物的区别正在于人是有意识、有目的、有自觉能动性的自然存在物,人具有改造自然的能力、能够按照自己的愿望去改造自然界,尤其可以通过物质生产活动不断改造自然和改造人本身,从而形塑出一个“人化自然”的新样态。传统文化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分析以一种更为整体主义的“天人合一”方式呈现,在“与天地参”和“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的双向强调中,一方面有奉天弗为、与时偕行的顺应自然强调,另一方面也有自强不息、自求口实的主体性、主动性提倡。而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人的主体能动性都体现为一种自觉的生态靶向,即发现、了解进而顺应自然规律。正如共产主义目标是“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一体强调,“观乎天文”也是为了“化成天下”、达到“天下文明”的状态,人化自然包含着顺应自然的强调,天人合一也以人的参赞化育为指向。因此,“人—自然”的关系体现为人与自然的交互、人的受动性与能动性的综合,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论断。
差异补充:自然观中的结合机理
诸多专家学者都曾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性进行深入阐发,我们对自然观的分析也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理论观点、研究方法、价值追求等方面的契合性。但与“相互契合”互为硬币两面的是,彼此差异也供给了“有机结合”的必要性。这一契合为基础的差异性结合是“第二个结合”之可能性与必要性的生动论证,也是我们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可或缺的着力点。
从自然观来看,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以人为中心内容和实际旨归——一方面,人的实存是自然界实存的确证、人的实践活动是人与自然交互关系的中介、人本身又是人与自然问题的最终目标;另一方面,自然的积极性的判定标准完全取决于人自身的生产和发展需要,人也是导致“人—自然”关系出现问题的唯一责任主体。尽管这与资本主义制度之下片面强调征服和改造自然的“人类专制主义”不同,但却容易从积极意义上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滑向消极的一面。而尽管“天人合一”对“人—自然”的认知因二者分化的未曾澄明具有一定局限性,但这种对自然界本身的混溶性强调却能够引导人们关注自然界本身、对自然界怀有敬畏,从而更好地实现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防止“人类中心主义”走向消极。此外,在人的能动性发挥角度,马克思主义强调人通过劳动等活动影响自然的、生产性的改造实践;传统文化则强调以“德”的方式约束自身进而以“行”影响自然的、伦理性的道德实践,但作为物质生产的劳动实践和作为道德践履的日常实践都为我们所需要。因此,“天人合一”理念为代表的传统自然观因其独特的文化属性而在当代中国存续,因其合乎理性而与现代化本身相融,又因其在一定程度上区别于马克思主义“人化自然”的差异性为我们如今构筑生态文明提供了独有的理论借鉴,对其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亟待完成的必要事业。
面对前在的理论资源,习近平总书记以在“人类知识的总和”中“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理论大格局大气象”,提出了“生命共同体”的理念。这一理念强调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进行生产劳动、经济活动,也倡导人们自觉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态度约束自身行为、践行生态伦理,以个人行动为建设美丽中国、美丽世界作出应有贡献。因此,“生命共同体”既是对马克思主义“人化自然”观点的继承,同时也是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理念的继承,以契合之处为着力点和突破口、又以差异之处为相互补充。就此而言,“生命共同体”既是人与自然关系上的科学命题与价值指引,又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结果与生动示范。
(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