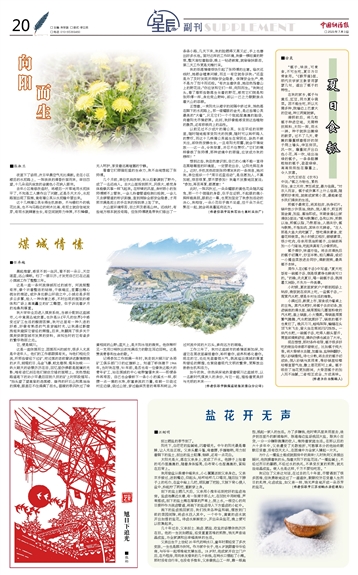“瓠子,味淡,可煮食,不可生吃,夏日为日常食用。”《群芳谱》里,明代农学家王象晋用寥寥几句,道出了瓠子的特性。
在我的家乡,瓠子与黄瓜、豇豆,同为夏令蔬菜。因不能生吃,所以无需多种,院墙边上巴掌大的空地,种三两窝就够。
清明前后,将几粒瓠子种进空地,无需特别照料,太阳一照,雨水一淋,种子就拱出嫩绿的新芽。过不了几天,青嫩的藤蔓顺着搭好的架子爬上墙头,伸至房顶。风一吹,藤蔓间开出白色小花,再一吹,结出油绿的瓠子。一条条胳膊粗细的瓠子,盈盈绿绿、高高低低挂在藤蔓上,令人欢喜。
元代王祯在《农书》中说:“瓠之为物也,累然而生,食之无穷,烹饪咸宜,最为佳蔬。”对农人而言,瓠子或许算不上什么佳蔬,随便煎炒煮炖,就做成家常小菜,最能彰显乡民们清淡的生活。
煎瓠子最常见,将其刨皮,洗净切片。锅中放少许菜油,烧热,倒入瓠子,煎至两面金黄,加盐、酱油即成。宋朝食谱《山家清供》里说:“瓠与麸薄切,各和以料,煎麸以油,煎瓠以脂,乃熬葱油,入酒共炒,瓠与麸熟,不惟如肉,其味亦无辨者。”古人那是大鱼大肉吃腻了,想吃清淡素食,变着花样做菜。我小时候正相反,顿顿素菜,很少吃肉,母亲用菜油煎瓠子,出锅前再加一小勺猪油,吃起来真有几分像煎肉。
瓠子清炒,味道亦佳。将去皮清洗后的瓠子切薄片,炒至半熟,拍几瓣蒜,或切一小撮韭菜放进去同炒,清新甜爽,最具瓠子本味。
周作人在《瓠子汤》中写道:“夏天吃饭有一碗瓠子汤,倒是很素净也鲜美可口的。”的确,炎炎夏日,喝一碗瓠子汤,既消暑又润肠,不失为一件美事。
小时候,夏夜里家家户户都到稻场上纳凉,晚饭就在凉床上吃,一盆瓠子汤,一筲箕汽水粑,便是乡村生活的缩影。
小满过后,新麦上市,面食成为餐桌上的主角。蒸汽水粑时,将瓠子去皮切条,放进锅底的清水里,锅周围贴几圈面粉做的汽水粑,盖上锅盖,小火慢蒸。等锅盖周围雾气腾腾,汽水粑就蒸好了,锅底的瓠子也煮烂了。晚风习习,蛙鸣阵阵,蝙蝠在头顶飞来飞去,萤火虫在草间闪闪烁烁。一块汽水粑,一碗瓠子汤,吃得人额头冒汗,胃里却清爽舒坦,燥热仿佛也减去了大半。
现在想想,那时条件有限,瓠子很多好吃的做法母亲都不曾做过,比如瓠子炖大骨。将大骨焯水去腥,加酱油、盐稍稍翻炒,倒入砂锅慢炖。待七分熟,将去皮的瓠子切成块,倒入砂锅与其同煮,等砂锅里咕嘟咕嘟直冒气泡,撒上葱花即可上桌。瓠子吸收了油花更加甜润,大骨因瓠子的加入而不油腻,二者相互成全,方成美味。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