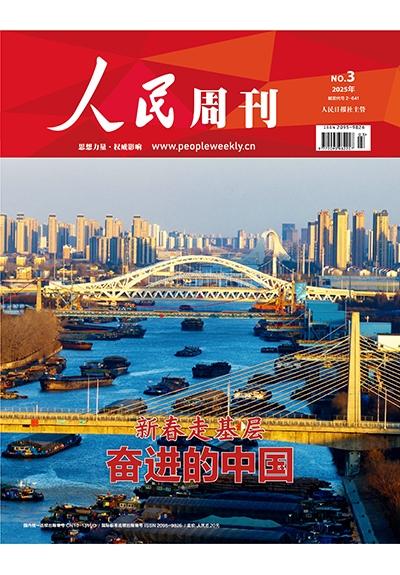继承与创新,我以为本来是没有矛盾的,只是对于继承的理解有偏、学习方法有偏,于是产生了矛盾。这好比吃东西,有的人属“热性”,不好吃鸡、喝牛奶。这是他本身的机能不适合,绝怪不得鸡和牛奶。善消化者,是没有矛盾的。所以前人早有“师心”与“师迹”的说法。只要我们理解和掌握传统的根本道理,取其精华,就可以学为我用,就能通而变。撇开传统、另起炉灶的说法,我看是学习上的笨汉,或者只说明他无知而且狂妄。“学然后知不足”,千百年来,我们的老祖宗难道没有为后代留下珍贵的遗产,没有值得研究、学习的吗?这个问题实在是显而易见的。
这里,我以为有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一是变与常,二是变好与变坏。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画从来是在变的,有继承,有多方面的吸收,只是有多少、快慢或者好坏的区别而已,就以山水画来说,从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至唐以来,所谓大小李,一变也;荆、关、董、巨,又一变也;李成、范宽,又一变也;刘、李、马、夏,又一变也;大痴、黄鹤,又一变也。明代的文、沈,基本上是继承。但如“浙派”及“野狐禅”吴小仙、张平山、倪端、徐端本等,都是在变,清初“四王”乃至戴熙,气息是旧,技法上还是有创造,如干笔技法,可说达到了极峰。至于石涛等以“怪”出名,怪在变也。干笔技法的流行,弊病也随着明显起来,于是又提倡湿笔,到了吴石仙,在生宣上打湿了画,这也是变。近代黄宾虹,面目又不同于古人。
所以,从历史上看,山水画一直在变,然而“万变不离其宗”。创造始终离不开“宗”,这就是中国画最根本的艺术规律,这就是“理”。“常理之不可失”,即是画画要讲物理、情理、画理。“法”在变,某些审美要求在变,一些根本的“理”还是没有变,或没有大变。科学与艺术是两回事,科学突飞猛进,并不意味着艺术在爬行。例如,画画讲立意、讲布局、用笔运墨、赋彩;用笔又讲圆、厚、沉着、凝练,或者生辣、流动、灵变等,板、刻、结、溷、滞、纤弱、躁气被认为不好,更不能飘、浮、滑、俗。用色要求清、和,明快而严肃,单纯而有变化等,把重浊、滞腻、火气、甜俗视为不好或者格调卑下。在布局上,三远结合,又有空白、虚实、宾主、繁简、疏密、隐现等的讲究。我想,这些审美要求不会因时代的前进而过时。有人说,“六法”的框框应该打破,怎么“打破”?难道画画可以不讲立意、不讲构图吗?总之,在观察方法和表现方法上、在审美要求上,中国画有自己独立的系统。形成中国画这种独特风貌的一些根本原则,又与文学、书法乃至音乐、戏剧紧密相连相通,极为高超,构成光辉的民族文化的精华。
有常又有变,有变又有常,这是一点。另外,“变”,有变好的,也有变坏的。晚清吴石仙打湿宣纸作画,确也是“变”,但这个“变”并不高明,因为缺少笔意,骨法不够,又单薄。黄宾虹运用浓、淡、破、积、焦、宿等墨法,浑厚华滋。二者不可相提并论。最强调“我有我法”的石涛,精品固然很多,有的用笔却显得放肆,信笔躁气。所以不能说凡变皆好。现在出版的某些山水作品,不大像中国画,倒近乎水粉、水彩、彩墨画,这个“变”好不好?变一定要有民族性,要在传统的基础上去创新。
谈到创新,又不能不涉及态度问题和对“新”的看法问题。
现在,可以说几乎没有人是不想创新的,但是有几种状况:有的脚踏实地,在坚实的传统基础上,吸收其他素养,努力反映时代精神,表现新的意境,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有的一面在生活和基本功上努力,努力追求新意,虽然还不成熟,每有一得之想,很值得我们学习。还有一种态度,却足以引起我们的警惕了。对于治学,古人说有两种态度,所谓“积学以成名”“速成以求售”,(“成名”的含义,这里不作分析与批判了)后者现在不是没有。企图以一朝一夕之力,凭他的小聪明,突变出自己的风格面貌以获利。书不读,传统不临习、不研究,却把自己那种“落笔无法”的东西视为最“新”。这种人只知道赶时髦,不晓得也不肯下硬功夫。说得过头一点,满口“创新”的人,往往会是学术上最不老实的人。中国画是讲究功力的,一条线,一个点,没有十年、几十年的功夫,很难达到某种高度。《石涛画语录》第一章就是“一画”,一生二生三,生亿万万,一是基础,一画所得的艰辛,没有下过苦功的人是无法体会的,因此只好靠搞“杂技”来出“效果”。美术界不能搞歪门邪道。不能笼统地说想“变”就变得好,不能笼统地说“创”的“精神”都应该肯定。胡来不是创作,更谈不上创新,冠以“创新”的美名,视听就被混淆了。
新,主要是意境的新,以及相应的笔墨的新。过去山水画的一变也,又一变也,主要是技法上的变,气息大同小异。现在,要表现新的时代风貌,也就要在传统的基础上创造新的表现手法。生活是源泉,传统是立足点。李可染三下江南,深入江浙、川、桂,在生活的基础上形成强烈的个人面貌;陆俨少经历了长江的艰险,古稀之年还饱看新安、雁荡、黄岳,创造出行云流水、大块水墨等前人未曾有过的技法,这就是我们极好的范例。总而言之,我们一定要踏踏实实在积累生活和积学传统两方面下功夫,水到方能渠成,侥幸之心是万不可有的。
(作者为中国美术学院教授、潘天寿基金会艺委会委员、李可染基金会艺委会委员,曾任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主任,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本文为新时代美术高峰课题组、中国画“两创”课题组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