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哪一个民族,都需要有那么一批人,在脚踏实地的前提下,时常仰望文化的星空,安心引领科技的远方。
两年前,一张“一个人的毕业照”,让北京大学2010级古生物专业学生薛逸凡为网友所熟知。如今,她的师弟安永睿也即将成为该专业本届唯一的毕业生。和管理学等热门专业相比,古生物专业“六代单传”,多少显得有些“高冷”。
高二时就立志学古生物的薛逸凡,从小就喜欢地理、化石的安永睿,也是如此,他们选择冷门专业,皆为强烈的兴趣使然。当许多同龄人还在盘算哪个专业有钱、有权、有稳定前景时,当一些媒体大举讨论什么专业最值得报考时,他们已然在自己喜欢的古生物学道路上精进,沉默却快乐,坚实而满足。
或许有人会问,每届至多只有一个学生,这样的专业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是不是对教育资源的浪费?仅从毕业后的直接回报来看,以古生物学专业为代表的诸多冷门学科,学习周期长,难以快速推出实用性成果,“性价比”可能远不及那些“显学”,因此也难免会被贴上“无用之学”的标签。但正如研究了一辈子东方学的季羡林先生所说:“学问不能拿有用无用来衡量。”当年牛顿研究万有引力、哥白尼研究天体运动、爱因斯坦研究相对论,如果只问有用无用,恐怕将会阻滞人类深入认识自然很长一段时间。“学问就是对未知世界、对自然界、对星空、对生态的尊重”,以学问为乐趣、为人类不断扩充知识边界的人,都值得敬佩。
“高冷”的知识,往往扮演着出其不意的重要角色。古生物学对于认知地球生命历史、探索生命演化规律、探寻化石能源等自然资源,甚至对探讨生态环境的治理,都有支撑作用。所以学生数量虽然“六代单传”,但学生可选择的发展方向不是“单传”,反而是多元。若抓住“六代单传”大做文章,继而以能否挣钱来评价这个冷门专业,显然贬低了专业的价值,更误读了这些学生的志向。
上大学的最大乐趣,在于能自由、欢快地在热爱的知识中遨游。刚刚逝世的杨绛先生早年在东吴大学读书时,父亲就鼓励她“喜欢什么学什么”。东吴大学没有她喜欢的文学系,于是读了政治系。她终究还是对政治学没有热情,课余最大的爱好就是在图书馆里乱翻书,偶尔读到希腊悲剧,大感兴趣。后来,她北上求学,确定以外国文学作为一生的研究领域,终成名家。
距离杨绛先生为兴趣而学,过去了80多年。反观今天,我们似乎还在经历一种为社会需求、他人眼光而学的阶段。“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句话耳熟能详,但“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就努力去学,并且一直坚持下去”,至今依然是不少人的遗憾。由此观之,薛逸凡们“六代单传”的坚守,无疑是这个时代宝贵的“稀缺资源”。它启示我们,不管专业是否冷僻,听从内心最真实的召唤,为心之所向而努力,才有可能活出人生的精彩。“每一样你喜欢的东西都是一道门,把门推开,就是一条特别悠长的路。”
“高冷”专业和“为稻粱谋”,本质上也并不是一对矛盾体。以长远的眼光来看,越是精于一业的人才,越会受到相关部门、公司企业的重视。基于良好的专业素养,扎实的科研态度,在今后的工作中,他们往往能发挥出与众不同的专业潜力,从而实现属于自己的出彩人生。那些看似寂寞、孤独的求学道路,其实远比一些人想象的壮美、宽阔。
在日前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重视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这些学科看上去同现实距离较远,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需要时也要拿得出来、用得上。”从某种意义上看,让“绝学”代有传承,也是我们对于人类、对于世界的贡献。无论哪一个民族,都需要有那么一批人,在脚踏实地的前提下,时常仰望文化的星空,安心引领科技的远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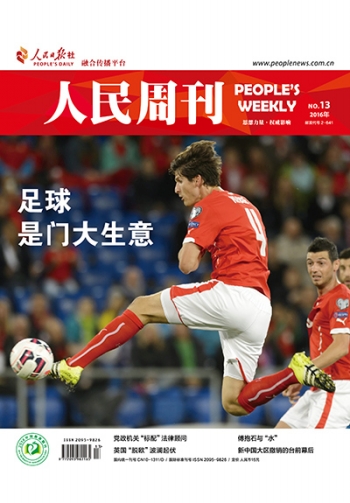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