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是文明的脐带,没有文化与历史的乡村是苍白的、漂泊的。
乍一翻开郭万新《吉庄纪事》的《引子》,冷不防,桑干河便披一身岁月尘埃,载满船钦慕目光,劈面而来——
桑干河,北方的河,北方的一条大河,裹挟了塞北西风的雄浑,记录着历史图腾的深刻印迹,古往今来奔流不息。
遥想三皇五帝时候,炎黄部落和蚩尤部落之间的涿鹿之战就发生在桑干河边,标志着华夏民族走过蛮荒,走入文明的起点;《水经注》中收入的一千二百五十二条河流中,桑干河又以恣肆不羁的个性,备受一代地理学家郦道元的推崇;当桑干河下游流经卢沟晓月,因为泛滥无常而获名无定河,直到康熙年间得到治理,被赐名永定河,堪称北京的母亲河;尤其是公元一九四八年,桑干河更是与丁玲的文学名著《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起,登临斯大林文学奖的荣耀殿堂……
这条承载着无数神奇的河流在山西省朔州市的神头镇开始澎湃着走向远方。对于神头,作者的笔饱蘸钦敬与追思,旁征博引,邀前人古人的诗句以铺色,掇优美的神话传说以添味,拈先贤尉迟恭的功勋为砖石……构筑起一座华美的舞台,为本书主角——神头镇的吉庄村倾力打造了一种浓墨重彩的氛围。
待铺垫已足,蓄势已成,吉庄村才踏着锵锵锣鼓,迎着千呼万唤,闪亮登场。
伫立于《吉庄纪事》里的吉庄,不是冰糖葫芦般的结绳记事,也不是单个人物的故事组合,更不是支离破碎的片段,既不沉静如石,亦不冷艳如冰,而是以岁月为经,以吉庄村的人和事为纬构成的一部质朴、厚重的村庄史;这部村庄史再延展弥散开来,成为一种宏大、绵远的中国乡村史。
吉庄史、乡村史的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姓名和一叠叠生机盎然的故事。雨果说:时代的每一个浪潮都在文化遗物上留下自己的冲积土,每一代都留下自己的一层,每一个人都填上自己的石块。吉庄如此,吉庄人如此,中国的所有乡村、所有在乡村中汲取生命滋养的人莫不如此。吉庄李姓的繁衍如大槐树一般枝繁叶茂,为吉庄增砖添瓦的同时,祖祖辈辈的李姓人仍以李氏的一条枝柯自视,不曾夜郎自大,更不曾数典忘祖。其心路历程如李树银老汉时常念叨的:“我的五个儿子,两个在包头,一个电厂,一个在县城,都上班了,剩下一个在村里也盖了新房。但我哪里也不去,谁家也不去,就在槐树院,哪儿也不去。”
连们院的连姓则代表着吉庄的文化高度,有意无意间,连姓族人在引导着吉庄靠近文明,熏陶着吉庄人沐浴文化之光。连步云老先生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儒家风范,一如连们院中的古老桑树,历经风雨,生机不改。
还有皮裤院的崇尚自由和幽默夸张,贾们院人们的浪子回头、农商并举……吉庄人如三大王庙里的各路神祇一样,来自五湖四海却英雄不问出身,思想兼容并包,五味杂陈而相得益彰。
吉庄从古代一路蹒跚而来,走过风雨飘摇的小农经济时期,走过在日寇铁蹄下的痛苦挣扎,走过耕者有其田、当家做主的苦尽甘来,昂然走进新时代,走进新生活的幸福;作家的心也一路溯流而上,直达历史的根部,然后携笔一路下行,将吉庄村史乃至乡村史的经纬格子用心填满,细大不捐。
贝奈戴托·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是的,历史与过往是根柢,是种子,现实与当下是梢杪,是果实。事实亦如此,不论是李氏祖先当年挈妇将雏背井离乡来到吉庄,贾氏先人离开熟悉的乡音乡情扎根于此,还是三大王庙的各路神仙能在同一屋檐下和平共处,历史似乎从开始已孕育出结局——勤劳、执着、融合,不是相互拆台,而是合力开垦造就和谐的土壤。
乡村是文明的脐带,没有文化与历史的乡村是苍白的、漂泊的。2013年底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在其报告中提出的“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至今仍令无数人动容和回味。乡愁,不应仅伤感在诗人的吟哦里,更不应飘渺于思乡者的喟叹遗憾里,而应具化于乡村的一缕炊烟、一抔泥土、一抹草色中。导演李军虎曾拍过纪录短片《父亲》,并拿了大奖。影片里,老韩为供儿子上大学,变卖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离开乡土到西安打工。为让儿子成功跳出农门,他竭尽所能。他随身装着的本子上记满了他的借款记录和对儿子的期望:“我儿胜利要在2013年前后,也就是父亲的60岁前后,让咱们全家到北京好好地玩几天,那时候咱们大家都很有钱……”家里的所有值钱物,恐怕其中也包括传统和乡愁,甚至包括自己的根,正因如此,老韩的心灵漂泊已成定局——这样的人又岂止老韩一个?在这方面,吉庄,吉庄人,应当庆幸——正因为有根,因为有史可依,心灵才不会是天空无根无性的云朵。
有专家指出,如果只是强调从乡民的感情与立场出发去体验乡村的生活,忘记了与来自大的文化传统的影响的互动,便无从洞察中国乡村社会的实质。这也正是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试图解决的问题。费孝通不孤立谈乡土或乡村,而是在“乡土”前加上“社会”二字,他说:搞清楚我所谓“乡土社会”这个概念,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具体的中国社会。在《乡土中国》里,他从乡村社区、文化传递、家族制度等方面去诠释乡土社会,这恐怕也是《乡土中国》一直不曾远离读者的主因。读罢《吉庄纪事》,不须掩卷冥思便会悟到,郭万新也试图从今古兼顾的维度,从纵横兼备的视角,尽量全方位、多元地为读者展现吉庄的历史,以期与读者的神思对接,使之形成一部宏大的中国乡村史;使吉庄与无数个乡村牵手,连接成一个真正凝聚着“乡愁”的“乡土社会”。
《吉庄纪事》是纪实文学。纪实的东西不好写,似乎深不得,也浅不得,要做到“不迁怒,不贰过”的冷静不易,要做到不粉饰、不阿谀的秉笔直书更难。但如果一味地“从心所欲,不逾矩”,则又似乎易流于平淡。记得美国诗人惠特曼对为他作传者的要求是:“你们要写老实话。无论怎样写,不要替我打扮,我的胡言乱语也要写进去。我恨许多传记,因为他们都不真实……”刘心武先生在《文学的腿功》中这样比较纪实小说与传统小说创作的迥异:“一般小说是去了解一百件事后,加以融会提炼,写出第一百零一件事来。纪实小说是在了解了一百件事后,从中选出一件最值得写的事来展现。如果在了解了一百件事后仍感到没有值得写的,那就再去了解,直到发现有一件值得移于纸上的事为止。”这里,刘先生所论虽是“纪实小说”,但一提到“纪实”二字,其重量便直逼心灵。由此亦可见纪实文学作家和纪实文学作品的可贵与值得钦佩。
自然,《吉庄纪事》并非完美无缺。比如,作者因为长时间走访村民和查阅资料,占有材料颇多,在写作中难免“舐犊情深”,难以取舍。或许,由于作者的目的只在于呈现、还原,故不曾着力于写作素材的遴选。或许正因如此,我们才能更长久地立于时空交界处,涵泳乡土之味,细细梳理乡愁入心入梦的苍凉与温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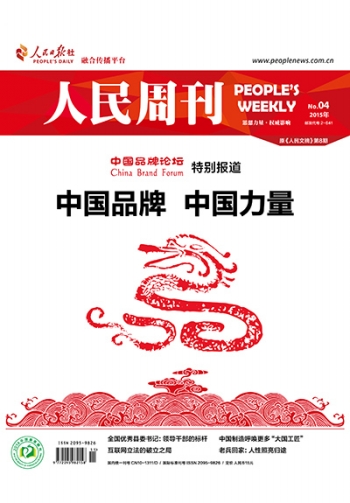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