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初,中共文献研究会刘少奇分会副会长、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二部副主任黄峥的两本著作《刘少奇冤案始末》、《刘少奇的最后岁月》再版,引起广泛关注。
为什么时至今日,刘少奇冤案还会引起人们的兴趣?
从申辩到沉默
让我们将历史翻回到40多年前。
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而那时的刘少奇,却对这次会议的情况一无所知。
在对刘少奇立案、审查、定案的整个过程中,没有人向他透露过有关专案的消息,更没有人听取过他的任何申诉。
在经历反复的侮辱、批斗及抄家后,刘少奇妻子王光美在1967年9月13日被正式逮捕,儿女们也被赶出家门。此后,中南海福禄居中的刘少奇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只有严密的监控如影随形。
刘少奇意识到,他的一切争辩都将无济于事。从此,他一句话也不说了,用沉默表示无声的抗议。而在此之前,为捍卫自己的政治生命,刘少奇曾几次三番口头争辩、书面申诉。但这一切均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伪证是如何制造的
囚禁、病危、反复抢救中的刘少奇自然很难知道,1968年10月后,他头上已被安了三顶帽子——“叛徒、内奸、工贼”,更无法知晓,这三顶帽子是如何炮制的。
按照黄峥讲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由于陆续有群众反映,党内也有很多人提出为刘少奇平反,最终由中纪委和中组部联合组成一个调查组,对刘少奇案进行复查。刘少奇420多卷档案,再加上王光美等人的案卷,共570卷档案。调查组看卷后根据提供的‘证据’再去调查。”黄峥记得,自己曾问当时参与复查的人,那么大的帽子,推翻有没有阻力?对方则说,没有。复查只用了半年时间。一箱箱材料很快都被否定。因为基本都是假的,是逼供的产物。
而这些伪证的出炉,都源自对刘少奇的一系列“专案调查”。
在对刘少奇进行专案审查前,1966年冬天,一个名为“王光美专案组”的机构成立。事后看,成立的依据,只是一张手写的、字迹潦草的“名单”。“它既没有标题,也没有日期,更没有注明是在什么会议上、由哪些人研究决定的。”黄峥说,这张手写“名单”中,江青的名字被圈掉,换成汪东兴,据当事人回忆,是江青自己提出的,但其实整个专案组一直处在江青、康生的操纵之下。前台的直接负责人则主要是谢富治。
1967年3月,随着“文革”的恶性发展,刘少奇问题升级,对他的审查随之开始。“最初,只是有人认为刘少奇在1927年有叛党嫌疑,于是在一次毛泽东、林彪及部分中央政治局常委等人参与的讨论会上提出由‘王光美专案小组’的办事机构‘调查研究’此事,并没有说要成立刘少奇专案组。但康生、江青等人在后来的实际操作中却设立了一个相当庞大的‘刘少奇专案组’。”黄峥说,或可证明江青、康生等人心虚的表现是,虽然专案审查刘少奇从1967年3月开始,5月加剧,但直到1968年4月中旬以前,关于刘少奇案情的各种请示报告和对外联系工作仍用“王光美专案组”名义,1968年4月下旬起才用“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名义。
至于专案组的工作方式,曾担任专案组负责人之一,后被江青批为“右倾”,关进秦城监狱5年的肖孟在1979年时这样回忆:“他们不断给专案施加压力,反右倾。在调查、看材料中,如实反映某些情况时,就以客观主义、扩散专案材料等罪名,停止专案人员工作,查封档案材料,有的人被赶出专案组,甚至关起来。搞专案的人思想负担很重,精神压力很大。在我被关进秦城监狱后,甚至有这种想法,宁肯坐牢,也比按那些人的旨意昧着良心办事为好,倒感觉自慰一些。”
肖孟所谓的“昧良心”,是指刑讯逼供,炮制伪证,以此证明在1925年、1927年、1929年刘少奇曾叛变革命,充当内奸、工贼。“在江青、康生看来,若要彻底打倒刘少奇只能从历史上找问题,说他是个叛徒,永世不得翻身。”黄峥说,“于是,他们千方百计,逼出证据。”
比如,为证明刘少奇于1929年在满州工作时叛变,专案组将刘少奇在满州时的部下孟用潜定为“隔离审查”的“重点突破”对象。肖孟当时参与了审讯孟用潜,按他事后回忆,“每次审讯,专案组几乎全体出动,七嘴八舌,拍桌子瞪眼睛,威胁恐吓,如‘交代不清,休想出去’、‘顽抗到底,死路一条’,还有指供、诱供情况。”
就这样,经过连续7天的日夜突击审讯,孟用潜作了违心的交代。但他事后多次口头和书面申诉,推翻假供,前后达20次,一再说明这些交代材料“都是编造的,并没有事实依据”,“写材料是在审讯小组帮助之下集体创作”。但这些申诉都被扣押和销毁了,有几次还强迫孟用潜本人当场撕掉,并一再警告他不许翻案,否则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像孟用潜这样,被株连进刘少奇案的人还有很多,其他受批斗、审查、隔离、关牛棚的人更是难以计数。
“人民误解你,那是最大的痛苦啊!”
刘少奇骨灰在河南,王光美是在丈夫去世多年后才知道的。
1969年10月,中国北部边疆局势紧张,战云聚集,毛泽东作出了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在这种背景下,中央决定将一些重要的审查对象分别转移外地。刘少奇首当其冲,被送往河南开封。
10月17日晚,刘少奇躺在担架上,在两名专案人员的押送下,被抬上飞机。因为走得匆忙,有关人员只给他套了一件上衣,裤子鞋袜都没有穿,只用被子一裹。
到开封不久,刘少奇身体状况急剧恶化,11月12日撒手人寰。13日午夜,刘少奇被秘密火化。此后多年,他的几个子女多方打听父亲的死因后得知,1969年11月13日深夜,河南开封的一个火葬场接到通知,说有一名“烈性传染病人”要半夜火化。火化单上,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死因:病死。家属签字处写着:刘原。
王光美说,刘少奇对“文革”的爆发没有思想准备。而让他真正清醒的,是毛泽东写的那篇《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尽管少奇同志思想上并没有想通,但他之后的检讨,就是努力按《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的口径写。毛主席也在少奇同志书面检讨上批示:‘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但中央文革在下发少奇同志检讨的时候,却有意去掉了主席的批示,并发动群众批判。”
王光美认为,“少奇对毛主席的热爱是真诚的,尽管形势这么险恶,他仍相信自己同主席的友谊。”而王光美自己,当年“更是盼望着主席早点为我们说句话”。
王光美还提到,刘少奇不止一次提过辞职的想法。“辞去一切职务,和妻子儿女回延安或老家种地,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而面对形形色色的批判,王光美记得,有一天刘少奇对她和孩子们说:“我过去常对你们讲,对一个人来说,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今天,我还得加一句话,就是对一个人来说,人民误解你,那是最大的痛苦啊!”
或许,让王光美刻骨铭心的,还是发生在1967年夏天时的画面:百万人“围攻中南海,揪斗刘少奇”后,满头华发的刘少奇对自己的未来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叮嘱子女无论今后生活如何艰难,“一定要活下去,在群众中活下去”。7月18日傍晚,夫妻二人在家等候造反派的揪斗,王光美预感到,“这回真的要跟你分别了!”
“倒像是等着上花轿的样子。”在这样严峻的关头,向来严肃的刘少奇反倒开了一个玩笑。
那天以后,夫妻二人被分别关押。“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是刘少奇与王光美分别时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1980年5月,王光美护送刘少奇骨灰从河南回家。“文革”时王光美曾问刘少奇,“为什么我们都被描绘得那么丑恶,简直成了罪犯,可彼此却没有怨言呢?”丈夫的话令她泪盈于睫,“因为相互信任。”多年后,王光美说自己“珍视他这句话的含义”。
摘自《小康》2012.3.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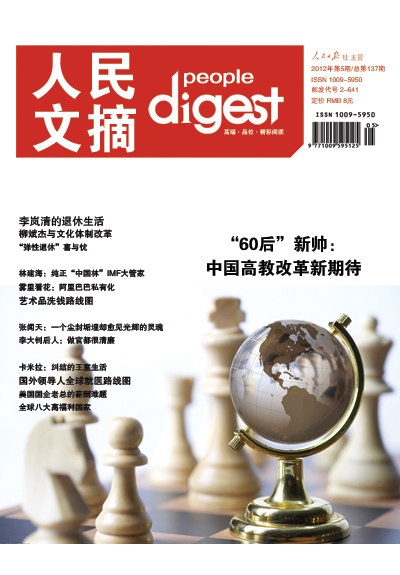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