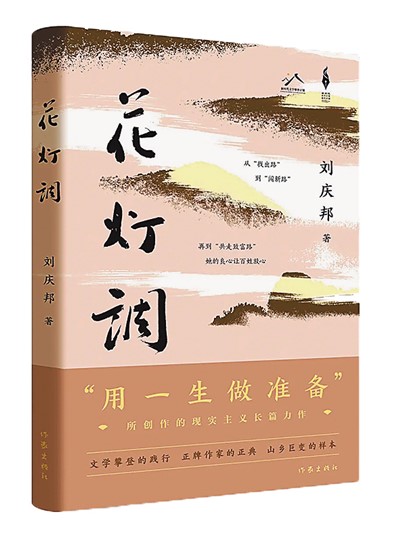新时代以来,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山乡巨变,堪称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一个历史性奇迹,矗立起一座永恒的丰碑。作为中国作家,我们有责任为这座丰碑“添砖加瓦”。作家的写作是手艺活儿,更是心意活儿,不是别人要我们写,而是我们按捺不住自己心潮澎湃的激情,自己要写。我写《花灯调》就是这样,不写就寝食难安,觉得对不起一个作家的使命和良心。
我1967年初中毕业后,回乡在生产队里当了3年挣工分的农民。1970年,我19岁,离开农村到煤矿,当上了一名矿工。1978年,我又从煤矿调到北京。虽说离开了农村,我几乎每年都回老家。母亲在世时,我回老家看望母亲。母亲在2003年去世后,因为大姐、二姐还在老家,我仍然每年都回去。一年回去两次,清明节一次,农历十月初一后一次。我虽然成了一个游子,但我的根还在农村,还和老家保持着骨肉相连的紧密关系,对农村过去和现在的变化也相对熟悉。在生产队时期,因为粮食产量低,交公粮多,分给社员的粮食很少,各家的粮食都不够吃。在穿衣方面,几乎人人穿的都是打补丁的衣服。更有甚者,打发闺女出嫁时,竟连一条新裤子都做不起,只能向别人暂借一条裤子给闺女穿。1975年夏季那场突如其来的大水,一天一夜之间把我的老家淹得房倒屋塌,变成一片泽国。我回老家看望母亲,母亲逃水灾跑到别处去了,村子里已渺无人烟,仿佛又回到了远古的鱼龙时代。
改革开放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内打响脱贫攻坚战之后,农民积累起一定的财富,农村的面貌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大地换了新颜。还拿我们村来说,差不多家家都盖起了宽敞明亮的楼房,我堂弟家盖到了4层。我们村的名字叫刘楼,一个“楼”字,代表着祖祖辈辈对居高条件的向往,代表着一个梦想。只有到了这个时代,才终于梦想成真,刘楼村才名副其实。穿衣早已不成问题,不论大人孩子,每个人的衣服都是单摞单,棉摞棉。吃饭的事更不用说。以前在我们老家,只有到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一顿白馍。现如今呢,每天吃的都是白面馍,想吃几个就吃几个。乡亲们感叹:我哩个乖乖吔,现在不是天天都在过年嘛!我大姐家、二姐家,还有二姐的大儿子家,都曾是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如今,他们都脱离了贫困,过上了丰衣足食的日子。这些都是我亲见亲闻的事实。我为这些事实所感动、所启发,很想写一部表现农村巨大变化的长篇小说,以见证时代奇迹,真诚地表达一个作家的理想和信仰。我大姐、二姐也对我说:你写过不少农村的事儿了,写的都是过去的事儿,现在的农村跟过去的农村不一样了,你写写现在的事儿呗。我说:我是想写,但写起来不容易,能不能写成很难说。
我的意思是,虽说有了写农村变化的态度和愿望,但不一定能落实到纸面上,变成一部长篇小说。写一部长篇需要扎扎实实的生活和大块大块的素材,而我每年回老家并没有长时间住下来,对农村的脱贫攻坚过程还不算熟稔。更重要的是,如何塑造好人物形象,是个难题。打个比方,主要人物是一部小说的纲,纲举才能目张。主要人物又好比是一棵树的骨干,只有骨干立起来了,才撑得起满树繁花。如果只是用小说图解政策,记录过程;只见物,不见人;只见客观,没有主观;只见变化,不倾注情感,不讲究细节、语言和艺术,那怎么写得出好小说?我知道,全国累计选派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奋斗在脱贫攻坚主战场。我想,最好是能找到一位驻村第一书记,以他或她为主要人物,这样方能把素材集中起来,统率起来。当我有幸遇到贵州遵义山区一位女性驻村第一书记时,心里一亮!好了,众里寻她千百度,她获得过“全国脱贫攻坚奖贡献奖”,不正是我要找的人吗?可以肯定地说,这个人物对小说的启动作用是决定性的,没有这个人物,就没有《花灯调》。
我所写的这个山村的原型,曾是贵州省的深度贫困村之一。我在这个村住了10多天,对该村的情况进行了了解。我得知,截至2015年,全村近5000人口,年人均纯收入才876元。山里往山外不通公路,连简单的沙石路都没有,只有一些乱石嶙峋的山间羊肠小道。整个山村几乎长期与外界处于隔绝状态,被人们称为“高山孤岛”,村里不少老人和孩子连汽车都没见过。村民养肥一头大猪,需请8个青壮男人分两班轮流抬,才能抬到山外卖掉。他们“刀耕火种”般种出来的蔬菜和水果,吃不完的因无处可卖,只能眼看着白白烂掉。村民要盖房,一些从山外购买的建筑材料,还得使用马匹驮运。常常是房子还没盖成,先把马累趴下了。除了不通路,村里还不通自来水,不通网络,不通高压电。村里有的小伙子外出打工谈了对象,女孩回来生下孩子后,实在不能忍受山村的极度贫困,就扔下孩子跑掉了。类似的情况不止一个,该村出现了十几个失去妈妈的留守儿童,让人痛心疾首。
2016年春天,遵义市纪委监委选派一位优秀女检察官,到这个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带领村民脱贫。在女书记的带领下,在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下,全体村民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村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交通、水利、电力、通讯,到教育、卫生、文化,各方面的条件都实现了巨大飞跃,堪称全国山乡巨变的一个缩影、一个典型。到2019年,全村年人均纯收入达到1.2万元。不少人家扒掉旧房,盖起别墅式的新楼房。春节期间,在全村院坝上停放的小轿车就有100多辆。“梧桐树”引来了“金凤凰”,村里的小伙子不愁找不到对象了。村民们把这些变化编成花灯调的唱词,广泛传唱,这也成了我小说名字的由来。
写《花灯调》之初,我就明确目标,下定决心,一定要把第一书记向家明的形象塑造成一个时代新人形象。可实话实说,我对何为时代新人并不很明确,不知道有哪些新特质。正是在与向家明原型的接触中,在人物形象塑造的探索中,我逐渐发现并认识到时代新人的特质,那就是,他们有坚定的信仰、不变的初心,有新的思想、新的担当、新的作为、新的创造、新的奉献。拿向家明来说,为了争取扶贫项目,为了说服村民参与修路,为了感激家人的支持,她多次失声痛哭,这是多么深厚的为民情怀。她身体患病,却瞒着领导、亲人、村民,坚持奋战在脱贫攻坚第一线,这需要多么顽强的意志和奉献精神。她曾3次差点把生命丢在山村,可谓九死一生,这又需要多么忘我的牺牲精神。新时代的新人形象不是一个概念,是通过具体行动在向家明身上完美体现出来的。
当然,向家明不是那种“高大全”式的人物,她也有七情六欲、儿女情长。她也想得到职务上的升迁,也想多挣工资。遇到不开心的事,她也跟丈夫使小性子。这些局限不但不会削弱向家明时代新人的形象,反而使其形象更真实、更立体,也更光彩照人。
除驻村第一书记向家明,在《花灯调》中,我还塑造了众多人物形象。像区委书记、镇委书记,还有高远村的老支书、村委会主任以及周志刚、刘丽、任欢欢等人物,我希望读者能从小说中读出他们的个性。我希望用这些人物群像,定格下时代的发展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