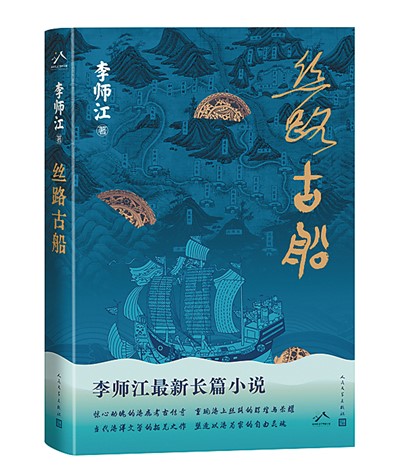李师江在新作《丝路古船》里,变成了一个老派匠人,老老实实地讲了一个好故事。作者将地方性知识与类型小说叙事技巧相结合,从福建渔民的打鱼技巧、当地习俗到方言土语,都有涉及。粗看流畅、精彩,像是一部扣人心弦的夺宝电影,细看会发现作者在结构上下了不少功夫。这部小说人物纷繁、故事复杂,但总体来说有两条线索:一是以文物贩子练丹青、海盗池木乡为代表的“盗窃线”,他们的目标是盗捞元代沉船里的珍贵青花瓷;二是以边防警察钟细兵、女警郑天天为代表的“追查线”,他们的工作是保护珍贵文物。把这两条线索明确下来,小说的基本骨架也就搭起来了。随后就是融入支线,丰富叙事。闽人陈秋生的际遇、遭遇海难的船仔父子、船仔与郑天天的微妙关系等,让一个简单的夺宝故事交织在历史和今天的复调中。
《丝路古船》以海上丝绸之路为背景,作者试图为这片独特的海洋空间融入世俗的烟火气息,还原与海为伴的人们顽强生活的故事。李师江在创作谈中写道:“(想要)塑造一个海岛上自由而固执的灵魂……那些漂在海上的,湿漉漉的灵魂,生于海岛又为海岛所困的,正是我想塑造的。”
小说中最值得琢磨的是船仔、郑天天、练丹青这三个人物。船仔4岁丧母,流落水上人家,他水性极好,向往自由,熟知海上世界的一切,却不习惯世俗社会的法则。与外界打交道,他感到本能的畏惧。相比之下,女警郑天天信奉法律和秩序,她的身份要求她恪守理性,但这个坚韧、聪慧的人物背后却埋藏着心理创伤。来自父亲和恋人的伤害,令她更加小心翼翼地处理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如果说船仔向往的是自由,郑天天向往的其实是安全,是自己可以掌控的生活秩序。这种性格上的根本差异注定了他们相处的结果。船仔是秩序和理性无法驯服的江湖之子,也代表着闽南本地人与海洋安宁共生的一种可能。作者对他的描写也在暗示他既是一个小说角色,又是闽东大地某种地域精神的化身。船仔大部分时间漂在海上,过着孤寂的生活,他曾一度与陆地上的众人接触,却被谎言所伤。他在寄给郑天天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岛屿与海洋,那是我的另一个父亲,我不会离开了。”
小说中最动人也最真挚的一笔,是船仔与郑天天在草屿岛上的相遇。当他们真正感知彼此,秩序的坚固围墙出现松动,善与恶、黑与白的界限也不再分明,人物的情感穿透宏大叙事,微妙而暧昧,直抵柔软的人心。当满天星河点缀大海,渔民思念着家的味道,恋人也在暗自领受惊心动魄之感。在那一刻,他们内心的冰河渐渐融化,对于温暖的渴望,打破了戒备的心理防线。他们走向彼此,实则也是通过彼此了解自己。本质上,这是一段自我疗愈、自我接受的旅程,它的重点不是恋人终成眷属的结局,而是一个人经历种种考验后,更加了解自己属于怎样的生活。于是,“皮肤里藏着阳光和海风”的船仔选择了大海,而郑天天在完成任务后,也继续在世俗生活中守护自己内心的秩序。
相比之下,铤而走险偷盗古物的练丹青代表了海洋文化的另一重特性,那就是冒险、逐利、实用主义。如果不急着用善恶标准去评判他的行为,我们不得不承认,海洋文化向外拓展的本质决定了人物对冒险的渴求。海洋文化对旧秩序和旧道德带来了冲击,同时又酝酿着新的机遇、新的创造力,比如地理大发现、全球贸易进程的开启等都与海洋文化密不可分。因此,练丹青可以视作海洋文化的另一重象征,与船仔进行对照,就会明白作者为什么要塑造这么一个人物。
近年来,南方边地写作日益受到关注,评论界有学者将其命名为“新南方写作”。诸如陈春成的瑰丽想象和对闽东山地的描绘,林棹对一只19世纪南方青蛙生命之旅的畅想,路魆的岭南志怪与变形记,索耳笔下焦灼的还乡叙事与岭南社会风貌,林森笔下的海南岛屿写作等,都展现出新一代南方写作的差异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师江的写作立足南洋,以古代丝绸之路作为历史资源,串联起边地渔民、商贾、小市民的生活,在历史与现实的互动中书写“海上丝路文学”,让新南方写作更具多样性。
从苦心经营的长篇小说《黄金海岸》,到这一部相对轻盈的《丝路古船》,都彰显出李师江明确的写作自觉,那就是打捞起东南沿海地区被遗忘和被边缘化的世俗生活,让海洋写作不再局限于纯文学的范畴,通过悬疑、夺宝、推理等写作技巧,在严肃写作和通俗笔法间找寻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