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从课本上读前辈作家笔下的广州,皆不出一个“花”字。
我们发现那里是花山,也是人海。在鲜花和绿叶堆成的一座座山下,奔流着汹涌的人群,我们走入春天的最深处了。(冰心《记广州花市》)
买了花的人把花树举在头上,把盆花托在肩上,那人流仿佛又变成了一道奇特的花流。南国的人们也真懂得欣赏这些春天的使者。(秦牧《花城》)
我因此对“花城”广州充满了向往。及长,多读了些书,略知了广州花市的来历。
花街芳踪古可寻
古来国中,洛阳看牡丹,成都曰蓉城,皆以花名世。而自海上丝绸之路开通,异邦珍品最早移入,广州即以草香花韵闻名,至百代罕有匹敌。由于岭南夏无酷暑,冬无寒冻,雨量充沛,土壤滋润,环境得天独厚,以至树木常青,繁花长盛。说什么岁枯月荣,广州花事无岁月,此花才谢,彼花已开;说什么伤春悲秋,广州花事无春秋,此叶方落,彼叶已绿。
花市者,广州俗称“花街”。钩沉史籍文献,追寻“花街”芳踪,已2000余年矣。
西汉陆贾使南越,叹广州皆“彩缕穿花”之人。南越王赵佗因思乡,令城内广植陆贾自西域带来的素馨。夏时盛开,满城如雪,馨香弥漫。女子以彩丝贯之,素馨与茉莉相间,以绕云髻,是曰“花梳”。素馨可提炼香油,以作面脂或润发,也可制龙涎香饼,韵味愈远。乞巧节,珠江素馨花艇游泛。千门万户,皆挂素馨灯,结为鸾凤诸形,或作流苏宝带。豪门饮宴酒酣,出素馨球以献客,客闻寒香,沉醉辄醒。挂复斗帐,能除夏炎,枕簟为之生凉。故此,粤以素馨为矜类之尤物,蔚然成风。
素馨以其洁白可人,备受青睐,名列花市首榜。以素馨花为主的广州花市,早在南宋就有记载。《岭外代答》(南宋·周去非)载,广州素馨花开时“旋掇花……以竹丝贯之,卖于市,一枝二文,竞买戴”,广州因称“天香茉莉素馨”。当年的珠江南岸,“平田弥望,皆种素馨”,(《广东新语》)不啻为大花园。农家多以种花、卖花为业,是故清诗人有诗“三十三乡人不少,相逢多半是花农”。
其实早在唐时,广州就有专门卖花的营生。唐末,广州近郊即现卖花的花墟。
明朝中期,常年花市形成。《南越笔记》中载:“广州有花渡,在五羊门南岸。广州花贩每分载素馨至城,从此登舟,故名花渡。”
花渡头,秋波桂楫木兰舟,红妆障日影悠悠。悠悠一水不可即,谁不怜花似颜色。钗头玉燕亦多情,不爱明(宝)珠爱素馨。君不见卖花儿女钱满袖,春风齐入五羊城。(清·方殿元《羊城花渡歌》)
载花船的招摇,卖花女的娇艳,尽在其中。
除夕花市渐成俗
明朝,广州种花已成专业,从江南逐步扩展到花地。清代沈复在《浮生六记》里专门写到“花地”:“对渡名花地,花木甚繁,广州卖花也。余以为无花不识,至此仅识十之六七,询其名有《群芳谱》所未载者,可见花地花事之盛。”每年农历正月初七,仕女结伴游花地,为当时习俗。平时花开季节,亦裙履连翩。俗谚“想死易过游花地”,“死”乃“挤死”之谓,是元宵灯会的写照。光绪年间,河南隔山名画家居巢、居廉兄弟,曾按廿四番风花信,写24种不同花的画册,使花地名花花容永驻。
乾隆年间,广州除夕花市渐为成熟,逐步扩展到香港和东南亚。咸丰、同治年间,有了除夕花市。
除夕是花市的高潮。《广州城坊志》记载了除夕花市的盛况:“每届年暮,广州城内双门底卖吊钟花与水仙花成市,如云如霞,大家小户,售供座几,以娱岁华。”至此,广州花市已由单一的素馨花变得更为多样,不但有吊钟花,还有水仙花。
上世纪20年代,广州大规模的除夕花市定型。
广州人对于花和花市可谓痴迷至极。即使是抗战时期,广州的除夕花市照常举办。敌机凌空呼啸,市民照常逛花市买花。
上世纪70年代初,花市规模逐年扩大。广州十大“除夕花市”,每天流量都达百万人次以上。
最是广州爱花人
广州花市是中国独一无二的民俗景观,也是世间规模浩大的美色集锦,作为一轴散发着浓郁岭南风情的文化长卷,成就了广州“花城”的美誉。
一年一度的迎春花市,是广州人的嘉年华。然而,客居广州十年,我一次也没有去过广州那些著名的花市。
因为没有必要。
我楼下的街道,每年除夕将近,便纷纷搭起一排排展卖鲜花鲜果及年宵用品的竹棚,四乡花农涌来,层层花架沿街伸展,宛如巨龙盘踞,望不到尽头。洛阳牡丹、漳州水仙、金边瑞香,欧洲薰衣草、泰国富贵掌、荷兰郁金香,茶花、芍药以及广府新年必备的金橘、桃花和水仙,乃至再普通不过的鸡冠花……林林总总,令人眼花缭乱。大街小巷,繁花漫漶,几被花海淹没。街道主要出入口立起巨大的牌坊,灯火辉煌、气势壮观。花市开张,人山人海,水泄不通。
古老而又青春的花市。灯色花光,春深如海。“人们选择和布置这么一个场面来作为迎春的高潮,真是匠心独运。”(秦牧《花城》)
不过,当年秦牧先生赞叹的“一日之间广州忽然变成了一座‘花城’”,今天恐怕已不是如此。即便不逢除夕花市,广州也是家家有花,户户多彩,一年四季花团似锦。
广州人喜花、养花、赏花,一如他们的喜食、懂食、善食。除了天宫的仙芝、龙宫的琼瑶或不可得,无所不可以入赏。门前屋后种花,堂上室内摆花,开业志庆送花篮,男婚女嫁坐花车,探亲访友捧花束……广州有最多的花店,拐弯抹角,触目可见;广州有最多的花景,远近高低,少有空白。豪门巨贾不惜千金唯求国色天香,寻常人家一钵金橘几株水仙清供岁朝。
“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张岱《陶庵梦忆》)以愚之见,鸟有鸟痴,鱼有鱼痴,石有石痴,木有木痴,广州多花痴。说花市是广州人的“匠心独运”,莫如说是他们的品性使然。
广州人的热爱生活,花是最靓的证明。花与广州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水乳交融。“讲意头”,成为独特的花语:桃花寓鸿运;柑橘示吉利;“发财树”“步步高”,其义自明;吊钟花“金钟一响,黄金万两”;标价数码多为“3”“8”“9”,谐音“生”“发”“久”,生猛、大发、长久;“行(hang)花街”即“行大运”。
“花城”是广州的精魄,“争似种花郎有幸,一生长伴美人魂”,贮满的是美色。“花市”是广州的字号,“筠篮卖入重城去,分作千家绣阁香”,交易的是美好。“花容”是广州的表情,“千叶芙蓉讵相似,百枝灯花复羞然”,展示的是永远的美丽。
(陈世旭,当代作家,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主要从事文学写作;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随笔集等多种作品出版,其中《小镇上的将军》《惊涛》《马车》《镇长之死》等曾获全国文学奖。)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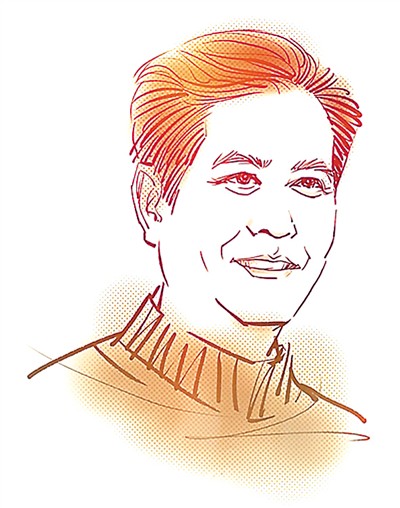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