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一则抗肿瘤药物“重出江湖”的消息在医药界引发震动——上海医药集团旗下的天普公司郑重宣布:启动安柯瑞??(重组人5型腺病毒注射液)的再上市计划。
重组人5型腺病毒注射液既是中国首个、也是全球第一个上市的溶瘤免疫治疗类抗肿瘤药物,开创了人类用病毒治疗肿瘤的先河。
更令人称奇的是,重组人5型腺病毒的发明人,同时还创造了另外两个“中国第一”:共同发明、领导开发了我国第一个具有全球知识产权的单克隆抗体类新药朗沐??(康柏西普眼用注射液)、第一个具有国际品牌的国产PD-1抑制剂达伯舒??(信迪利单抗注射液)。
这位目前为止我国唯一一位发明三个国家1类生物新药的科学家,就是中组部“千人计划”国家特聘专家、四川大学教授、中国免疫学会肿瘤免疫与肿瘤生物治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俞德超博士。
从放牛砍柴到研发生物药
“我出生在浙江省天台县的一个偏僻小山村,放牛砍柴是印象最深的童年记忆。”说起往事,俞德超很是感慨,“那时候村里的教育条件极为简陋,我的小学是在混合着5个年级学生的复式班里度过的,初高中阶段学校还常常缺任课老师。”
1982年,聪明好学的俞德超考入浙江林学院经济林专业,成为当地第一个走出深山的大学生。“说实话,当初自己也不知道真正的兴趣是什么。探索自己最想做什么,我花了很长时间。”俞德超笑着说。大学毕业后,他考取南京林业大学硕士生,攻读植物生理专业;1989年,他考上了中国科学院的博士生,攻读分子遗传学专业。“直到这时候,我才发现:研究分子生物学、做有用的东西,才是自己的兴趣所在。”
1993年,俞德超漂洋过海远赴美国加州大学博士后工作站,从事药物化学专业研究。当时,美国制药行业正处于从小分子化学药到大分子生物药的历史转折期,利用基因工程技术开发生物药方兴未艾。在博士后研究期间,俞德超围绕“在贾滴虫中建立基因表达系统”这一课题连续发表多篇论文,在美国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哈佛大学医学院向他发出了任教邀请。
“与单纯做科研相比,我更喜欢做成果转化,这样可以帮助更多的人。”1997年,俞德超放弃了哈佛大学的任教机会,进入美国Calydon生物制药公司从事生物药开发,并很快就从普通员工晋升到公司副总裁。此后,他又在美国多家知名生物制药公司担任研发要职,积累了丰富的生物制药研发与管理经验,成为美国业界知名的肿瘤治疗药物研发专家。
开创用病毒治疗肿瘤先河
“中国人常常用‘生于斯长于斯,歌哭于斯’来形容一个人和故土无法割舍的血脉联系。在异国他乡生活,对此更有体会。”在美国天天和新药打交道,他心里常常想:这个药美国有了、中国还没有;这个新药美国患者买得起,但大多数中国患者还掏不出这么多钱……“这样的想法日益增多,我就萌生了‘做中国自己的创新药’的念头。”
1997年,俞德超把自己发明的溶瘤病毒“重组人5型腺病毒”的相关技术转给了上海医药集团。
“溶瘤病毒的思路,就是‘以毒攻毒’。”俞德超解释说,简单地讲,就是利用肿瘤细胞与正常细胞的基因表达差异,用基因工程的方法,制备出专门针对肿瘤细胞的重组基因工程病毒。
俞德超说:“重组人5型腺病毒是一种致病力很低的普通感冒病毒,它只‘喜欢’肿瘤细胞,进入肿瘤细胞后能大量繁殖,迅速‘吃掉’肿瘤细胞;同时,它还能诱导产生针对肿瘤的免疫反应,进而把肿瘤溶解掉。”
上海医药经过进一步开发,研制出治疗鼻咽癌的重组人5型腺病毒注射液,并于2005年获准上市,成为全球第一个治疗肿瘤的溶瘤病毒新药,开创了利用病毒治疗肿瘤的先河。全球第二个溶瘤病毒药物TalimogeneLaherparepvec (简称T-VEC ,Imlygic? ),2015年10月才被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上市,比重组人5型腺病毒注射液晚了10年。
“现有研究表明,溶瘤病毒具有靶向性好、杀伤率高、副作用小的优势,是当今肿瘤免疫疗法的一个重要手段。”俞德超说,“更令人高兴的是,溶瘤病毒还可以与PD-1/PD-L1抑制剂联合用药,可以使对PD-1/PD-L1抑制剂不敏感的‘冷’肿瘤变成‘热’肿瘤,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因此,重组人5型腺病毒注射液的重新上市,不啻是肿瘤患者的一大福音。”
迫使进口药自降身价
单克隆抗体(俗称“单抗”)类新药是目前国际最具前景的创新药物,广泛应用于肿瘤、自身免疫疾病等重大疾病,疗效虽好,但价格非常昂贵。以治疗肺癌的单抗生物药为例,在美国,一位患者的年治疗费用是15万美元左右,约合100万元人民币,普通患者可望而不可即。
“开发出中国老百姓用得起的高质量生物药,让更多的患者享受到科技进步带来的健康成果!”2006年初,俞德超告别妻女,只身回国,加盟成都康弘药业集团,组建成都康弘生物团队,研发治疗老年黄斑变性和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致盲的单抗药物康柏西普。
老年黄斑变性和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被称为“致盲杀手”,是国际眼科界公认的最难治疗的眼病之一。在康柏西普诞生以前,跨国企业诺华研制的雷珠单抗独霸天下,以每支9800元的高价垄断中国市场。
“当时国内生物制药的基础几乎为零,我和团队在国内甚至找不到一家可以进行临床前研究的实验室。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坚持以国际标准扎实推进。”据俞德超介绍,经过多年艰苦攻关,康柏西普终于在2013年获准上市。
康柏西普是俞德超回国后领导开发的我国第一个具有全球知识产权的单抗新药,被评为中国“眼科学界最大科技突破”之一和“中国最具临床价值的创新药”,为无数老年黄斑变性和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致盲患者带来光明。
康柏西普上市后,药品“中国制造”打了一场漂亮的反击战。因疗效更好、价格更低,康柏西普销售份额很快后来居上,市场占有率超过50%。2016年7月,倍感压力的诺华在雷珠单抗还有10年专利期的情况下主动宣布降价,每支降价2600元,打破了国外专利药物在专利期内不降价的历史。俞德超由衷高兴:“国产药主导市场价格,受益的中国老百姓就更多了!”
2016年10月,康柏西普获得美国FDA批准,越过I、II期临床,直接进入美国Ⅲ期临床试验。这在美国也不多见,在中国制药史上更是头一回。
开创国产抗癌药品牌
单抗类药物具有很高的技术要求和研发壁垒,是代表全球制药最高水平的高端生物药,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垄断着全球98%以上的单抗药物。
要让更多中国生物药在国际市场拥有话语权,惠及更多中国老百姓!2011年底,俞德超移师苏州工业园区,创办信达生物制药(苏州)有限公司,聚焦研发高质量的单抗生物药。
历经7年多拼搏,俞德超共同发明并领导开发的信迪利单抗于2018年12月获准上市,成为中国首个具有国际品牌的国产PD-1单抗新药,拥有全球知识产权。
在信迪利单抗上市之前,我国先后批准了两个进口的PD-1类药物:默沙东的帕博利珠单抗(俗称“K药”)和百时美施贵宝的纳武单抗(俗称“O药”)。“K药”和“O药”是当前国际上最为著名的PD-1单抗药物,被业界誉为“抗癌神药”。
令人振奋的是,信迪利单抗的治疗效果并不亚于这两个进口药物。2019年第一期《柳叶刀·血液学》杂志,以封面文章的形式,刊发了由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石远凯教授牵头进行的信迪利单抗的临床研究结果——这是中国第一项荣登该杂志封面的科研成果。临床数据表明,采用信迪利单抗免疫治疗复发难治霍奇金淋巴瘤的客观缓解率高达85.4%,疾病控制率97.8%;77.6%的患者使用该药6个月后没有出现疾病进展,而“O药”、“K药”的同类数据分别为77%和69%。信迪利单抗为肿瘤患者提供了创新且高度有效的治疗模式,提升了患者用药可及性。
据了解,目前“K药”“O药”的年治疗费用均在50万元人民币左右。“为造福更多患者,信迪利单抗的价格将明显低于这两款进口药。”俞德超告诉记者。
除治疗淋巴瘤,信迪利单抗还在进行20多项临床试验,包括一线非鳞非小细胞肺癌、一线肺鳞癌、二线肺鳞癌、一线胃癌、一线肝癌和一、二线食管癌等,初步结果令人满意。在不久的将来,信迪利单抗有望造福更多肿瘤患者,缔造属于中国的“神药传奇”。
四“心得”制胜新药研发
新药开发可谓“九死一生”,难度之大超乎想象,发明一个上市新药已属不易,俞德超何以能“连中三元”呢?对此,俞德超表示:“我没有秘诀,只有几点心得”。
首先是创新。
“所谓新药,就是疗效不低于已有药物的创新性药物,必须以前沿性科学研究为基础。”俞德超认为自己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创新的敏感性,能从科学发现中觅得蛛丝马迹,进而研发优于已有药物的新药。
他举例说:康柏西普与诺华的雷珠单抗的靶点都是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但VEGF有多个成员,雷珠单抗只能阻断其中的一个成员,康柏西普可以阻断三个。它的治疗效果比雷珠单抗好,原因就在于此。
其次要有韧劲。
“开发新药在中国尤其难。”俞德超说,多因素导致中国开发新药涉及的人才、设备、工艺等非常薄弱,几乎是空白。侥幸的是他能坚持,不言放弃。
“就说康柏西普吧,截至去年上半年,它还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唯一一个单抗新药。”俞德超回忆说,2006年,他开始做康柏西普的时候,大家都以为是天方夜谭。从动物模型到临床医生、从临床前研究到临床试验,都是从零起步,就像在黑暗中摸索,用“千难万险”来形容一点都不夸张。“面对重重困难,要是意志不够坚定,不可能走到最后。”
第三是坚持国际标准。
“新药是用来治病救人、服务全球患者的,所以必须坚持世界普遍遵循的国际标准,一丝一毫都不能马虎。”俞德超讲了这样一件事:为实现国际化,信达从2012年开始寻求与国际制药巨头礼来合作。礼来的要求非常高,其标准比美国FDA的标准还要高。他们多次派人到苏州现场核查。本来信达在2014年就拿到了第一个项目(代号IBI301)的临床批件,马上可以做临床试验了。但礼来在核查时认为,信达的生产工艺和生产设施达不到全球质量标准,要求信达必须先整改生产工艺和质量标准、达到国际标准。
俞德超告诉记者,按照礼来的要求,生产工艺整改至少要花36-48个月——这就意味着IBI301的临床试验要延迟至少36个月。
“信达是一家没有任何销售收入、全靠市场融资维持的初创公司,每月的平均开支少说也得几千万元,推迟36个月意味着我们要多支出几亿元。为了生产出符合国际标准的药品,我们硬是咬紧牙关、加班加点,最终用18个月就完成了整改。”说到这儿,俞德超笑了。“回过头去看,这一步还是走对了。‘磨刀不误砍柴工’,包括信迪利单抗在内,我们的所有在研新药都能经受得起国际标准的考验。”俞德超骄傲地说。
第四是团队协作。
“做药是一个环环相扣的系统工程,不是单靠某一个人能完成的。”俞德超介绍说,发明一个新药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后面还包括:毒理、药理、药代动力学等临床前研究,工艺开发与验证,分析方法开发与验证,大规模临床研究,后续的规模化生产和商业化,而且每个环节都困难重重、每一步都不能出差错。“所以,开发新药就像一场接力赛,每一棒都需要不同专业的最优秀的人来完成,这都离不开系统集成和团队作战。”俞德超说,“在人才上信达可以说是不惜血本。除了自己培养,我们还陆续从全球吸引了近百位高级研发、管理人才,组建了国际一流的‘梦之队’。”
岁月催人老,两鬓发已白。回顾自己研发新药所经历的坎坷历程,俞德超并不后悔:“人来到这个世界,一定要有自己的使命,生命才有意义。开发出老百姓用得起的高质量生物药、让每一个人都能平等地享受到人类科技发展的健康成果,是我回国创业的初心。我有幸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今后将继续坚守初心,开发出更多、更好的药品,为国内外患者造福,不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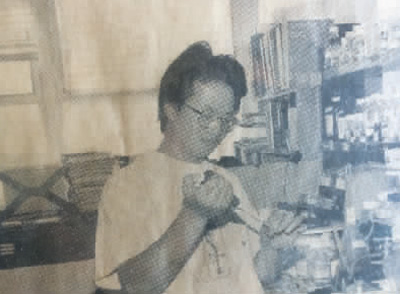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