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始于印书
1897年,夏瑞芳等几位年轻排字工决心自己当老板,于是筹资3750元在上海创办了小型印刷工场——商务印书馆(下简称“商务”)。顾名思义,是印刷书籍的地方。
复旦大学周振鹤教授考证,商务最开始并不以出版为主业。它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本馆专售大小新式活字铜模铅板,精印中西书籍、日期报章……”广学会的很多书是商务代印的,商务还代印创刊于杭州的《译林》,发刊词是林纾写的。
当时,清王朝风雨飘零,众多为中国寻找出路的知识精英目光投向西方,引入了各种先进技术、机械设备及思想主义,西学渐行。商务创始人敏锐意识到英语教材有市场,于是请人将印度英文教材加上译注,1898年出版了《华英初阶》,初印2000册,不到20天就销售一空。1925年出到第82版,换了封面又出到1938年,可谓第一桶金。当时杭州新办的求是书院用的是它,少年胡适初到上海,在梅溪学堂读的是它,梁漱溟在北京中西小学堂学的也是它。
1901年,商务改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增至5万元。夏瑞芳请翰林出身、因参与戊戌变法被革职的张元济入股,并负责编译工作。1902年,商务成立了编译所,大批知识分子进入商务,新的出版思路成型,商务完成了从印刷业到出版业的转型。
1904年是重要的转折年。商务耗费两年心血编纂出版的《最新国文教科书》,数月间风靡全国,此后陆续编印修身、算术、史地、英语等教科书,风行近10年,最终发行上千万册。辛亥革命后,商务推出65册的《共和国中小学教科书》,重印300多次,售出七八千万本,为清末民初的政治动员、思想启蒙和文化教育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周振鹤说,民国初年有一句话叫“今日之教育操于一二书商之手”,“一”就是商务,“二”就是商务、中华。可见当时商务在教育方面的势力如何之大。
商务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为宗旨,先后创办了《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小说月报》《少年杂志》等杂志,传播近代学术思想。
1914年,商务资本增至150万元,成为国内最大的集编辑、印刷、发行于一体的出版企业。
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张元济后代张人凤表示,商务从成立开始,就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己任,一开始就找对了办出版的方向。适应社会进步的需要,或者有的时候还领先于社会的潮流。
为中国看世界
自成立以来,商务担当起知识生产和文化传播的重要使命。它既致力于引进西方文化,普及现代知识,也致力于整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深度介入中国的政治、教育、出版和学术。
1929年,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第一集出版,收入图书1000种,作者有梁启超、王国维、吕思勉、傅斯年等大学者。丛书包括《国学基本丛书初集》《汉译世界名著初集》《百科小丛书》《新时代史地丛书》《工农小丛书》《国学小丛书》《商学小丛书》《算学小丛书》《医学小丛书》《体育小丛书》等,以低廉价格出售,使得各地公私团体或图书馆都有能力收藏一套基本丛书,进行系统的知识普及,嘉惠民众。
1915年,商务出版了《辞源》,这是我国第一部新式辞书。日本关西大学沈国威说:《辞源》的价值可能在于无源词,所收10万条词中有1万条没有书证,如西洋的人名、地名、机关名、事件名等专有名词,外语的音译词,科技词汇、术语等。这些词非常专业地解释了当时需要的术语知识问题,起到了传播新学、沟通新旧学桥梁的作用。
1917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的蒋梦麟回到上海,并进入商务,他向张元济提出编辑高等学术书籍的建议,被采纳。
1931年,《严译名著丛刊》8种风行于世,除赫胥黎的《天演论》外,还有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严译名《原富》)、约翰·穆勒的《逻辑体系》(严译名《名学》)和《论自由》(严译名《群己权界论》)、赫伯特·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严译名《群学肆言》)、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严译名《法意》)等,几乎每一本都影响巨大。
1939年,朱光潜翻译的黑格尔《美学》出版,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出版;1943年,钱穆的《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导论》出版,王力《中国现代语法》出版。1956年出版的《新华字典》,迄今已发行近6亿本。1978年,商务出版《现代汉语词典》,它是中国第一部规范性的语文词典,也是无数编辑的常任老师。
120年来,商务共出版5万余种图书,改革开放后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更是令读者感概:“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胡适当年曾经深有感触的说:“得着一个商务,比得着一个什么学校更重要!”
商务印书馆早期编辑寿笑天的后人袁明感慨,商务老一辈在他们那个年代为中国看世界。他们自觉地接受时代的提醒,有一种文化自信和底气,中西平衡,是旧学新知的平衡和完美结合。商务印书馆,不只是一家出版社。
低调的理想主义者
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说,做出版若不赚钱必定是短命的。历史上的商务印书馆首先是个成功的现代企业,既坚守自家立场,又身段柔软,随时准备吸纳人才和新鲜思路,其经营理念、组织架构以及管理方式均让人叹为观止。
前文提到的商务创始人夏瑞芳,兼销售、采购、取纸、收账于一身,善于识人,头脑灵敏,胆大心细,性情恳挚,富于冒险精神,是不可多得的人才,1914年被暗杀。
张元济放弃南洋公学校长之位来到一个小作坊,与夏瑞芳相约的条件就是“以扶助教育为己任”。1916年,张元济接任总经理,主持、督导商务近60年。他引进西学、介绍新知,精心选择、组织翻译了一大批外国学术和文学名著。他大力搜求古今图书,1926年“东方图书馆”对外开放,1929年藏书共达51.8万余册。“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这是张晚年所写的一副对联。张元济选择了以出版来推动教育,为中华民族的文明“续命”。
曾和张元济合编《最新初小国文教科书》的商务元老高梦旦,自觉商务出版物已落后于时代,而自己又不懂外文,1921年,赴北京邀请不满30岁的北大教授胡适主持商务编译。胡适推荐了老师王云五。高梦旦一个月后辞去所长职务,尽心辅佐王云五,还将自己的检字研究草稿交给王云五。王云五最终在1926年发明了四角号码检字法,并立即用于商务出版的字典编排。
王云五,一个读英语夜校出身的学徒工。17岁时以按揭方式买了套《大不列颠百科全书》,3年后付清书款时,他已将全书通读一遍。18岁任上海同文馆的讲师,成了胡适的老师。担任商务总经理后,他定下了“教育普及、学术独立”的出版方针,将文化与商业融合,主编了媲美小型图书馆的“万有文库”丛书,让商务赚了大钱。1932年日军轰炸商务印书馆,他写下“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当年8月1日,商务恢复印刷生产。1937年日军进犯上海,王云五将印务转移到香港、长沙。1941年,日军占领香港,上海、香港两地商务的财产尽失,王云五决定将总部迁至重庆。当时重庆分馆只剩13万法币,最多维持一个月,到抗战胜利时,商务账上已有数十亿法币现金。他重新确立总经理负责制,全面推行科学管理制度。实施大改革,9个专业部长换掉了7个,引进周建人、竺可桢、郑振铎、顾劼刚、叶圣陶等受五四运动影响的激进分子,后来都是学术界响当当的大人物。他又搞“科学管理法计划”,包括预算制、成本会计制、统计制、标准化与简单化、按件计酬制与售货量比较制,被全社视为公敌。这个曾经任政府财务部长、发行“金圆券”的“社会人”说:“我一生以出版为主,教学次之,公务、政务殆如客串。”
商务裁员之议为员工知悉,发行所共产党员廖陈云(即陈云)发起罢工,郑振铎为“罢工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之一,他的老丈人高梦旦为资方谈判代表之一。翁婿恪守“约法”,谈判桌上唇枪舌剑,会下相敬如常,如此处理公与私的关系,一时传为美谈。这种品格和风范,使得商务的工人能够成为延安印刷厂的厂长,使得商务无论多大的逆境都转危为安。
商务印书馆百年商务资源部主任张稷认为,有一种“商务印书馆情结”存在。比如后来出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的商务原总编辑陈翰伯说:“我不应该离开商务”。比如陈云,离开商务后很长一段时间,他每年到上海商务印书馆故地去看看,“我如果不到上海、不到商务印书馆,就没有我这一生。”
商务的魅力在于:一、深度参与中国现代化的全过程。二、它解决的问题具有根本性价值,是现代教育的最重要发端者、推动者。三、它在涉猎的所有领域中几乎都是冠军,展现了非凡的企业能力和事业高度。四、商务的历史体现了企业的大家风范和作为文化机构的风骨。
张稷认为商务印书馆具有非常强的乌托邦的性质,它的产生就是理想主义的产物,它和北大一样是戊戌变法的产物。“昌明教育,开启民智”就是张元济在戊戌变法中所做的,他把以教育救国这个灵魂移植给了商务,商务一直坚持了120年。
中国人民大学黄兴涛说,光将商务定位于“文化机关”远远不够,商务对现代思想文化启蒙的高度自觉,对教育现代化的重视和有效实践以及它对现代学术建设的不懈努力与担当,使它具有推动、激励、塑造、牵引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历史文化功能。商务可以也应该称作“中国现代文化的重要引擎”。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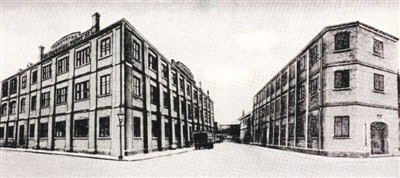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