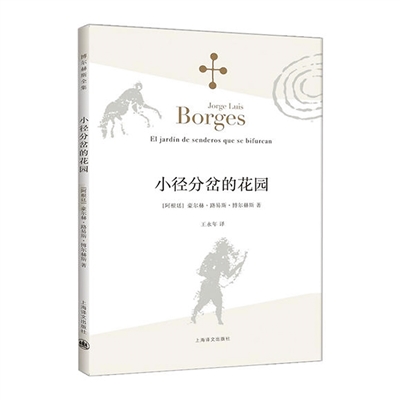1938年平安夜,阿根廷文学家豪尔赫·博尔赫斯撞伤了头,感染导致幻觉和高烧,他担心自己丧失创作才能,便决定检验一下——尝试写一个虚构故事,结果有了《〈吉诃德〉的作者皮埃尔·梅纳尔》,文中列举了虚构的小说家梅纳尔的所有作品并加以分析。这个多少有些欺骗和调侃读者性质的故事获得了成功,也开启了博尔赫斯短篇小说的创作生涯。一系列虚实相间、结构精巧、情节科幻和充满哲学思考的作品,让他位列20世纪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
“我首先是个梦想家,然后才是个作家”
读博尔赫斯的小说,就像玩一场智力游戏——如果一个人记忆力惊人,脑中充满古往今来所有事物的所有细节,会感到幸福还是痛苦?要是人的命运全靠抽彩票决定,一切皆是偶然,社会将如何运转?原本分处两个时代、两个城市的老年博尔赫斯和青年博尔赫斯,竟然坐在了同一条长椅上,这是一场梦吗,又会是谁的梦?……进入这些用文字构建的迷宫,你必须集中精神,展开想象,才跟得上作者狡黠的思路。
迷宫,是博尔赫斯钟爱的意象。他构建的迷宫是海岸高地上的大宅子,密布着通道;是永生者之城,有着盘综错杂的宫殿;是通天图书馆,由一个接一个的六边形回廊组成,无穷无尽;甚至是无形的,在其名篇《小径分岔的花园》(右下图)里,主人公找到了祖先设计的迷宫——一本小说,小说里,相互靠拢、交错或永不干扰的时间,构成了包含所有可能性的网络,时间不断分岔,通向无限的未来。
然而不管笔下的迷宫如何多变,博尔赫斯心中真正的迷宫只有一座,“世界本来就是迷宫,没有必要再建一座。”一切离奇叙述的外衣之下,是创作者对哲学的向往。对博尔赫斯来说,哲学是记录印度人、中国人、希腊人以及一切让人困惑的历史。而他要做的,就是记录下困惑,他的一次次思维实验,关于宇宙,关于生命,关于时间和空间,无限和永恒。“我首先是个梦想家,然后才是个作家。”
故事的主题多少有些形而上,却并非不可亲近。博尔赫斯搭建迷宫,也关心迷宫中的人。他说任何命运,不论如何漫长复杂,实际上只反映于一个瞬间:人们大彻大悟自己究竟是谁的瞬间。所以在他的故事里,可以看到怯懦之人终于决定撕下自己伪装出的英雄面具,看到嫉恨对手之人在对手毁灭后怅然若失,看到设下圈套之人惊觉最后步入圈套的是自己,看到一个人成为他自己的死敌。走进博尔赫斯思维乐园的人,不仅可以体会到智力活动带来的巨大而深层的快乐,也会在某一瞬间被击中,看到同样在世界迷宫中摸索的自己。
“我总是把天堂想象成图书馆的模样”
1955年成为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馆长时,56岁的博尔赫斯已经看不清书上的字了。眼疾是家族遗传,他的父亲、祖母和曾祖父去世时都是双目失明。博尔赫斯从小视力就不好,后来的失明如同夏日徐徐降临的黄昏,黑色和红色先消失,接着蓝色和绿色渐渐褪成棕色,最后黄色也弃他而去,他被留在一团雾气中。“上帝同时给我书籍和黑暗,这可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他在《关于天赐的诗》中这样感慨自己的命运。
当夜幕终于降临,博尔赫斯不得不与阅读告别。告别是苦涩的,因为阅读于他是“不亚于周游世界或坠入情网的体验”,是他回忆往昔时的人生坐标——童年是堪比图书馆的父亲的书房,是精灵、先知和海盗的故事,是百科全书里动物和金字塔的版画;15岁,是欧洲旅行,是待在旅馆里沉迷于弥尔顿的作品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早年生活,是每天早上在书店里消磨好几个小时。“我总是把天堂想象成图书馆的模样”成为他最广为流传的名言。
失明后的博尔赫斯常常做噩梦,梦见文字活了起来,他想读书而不得。但他并没有因眼疾而远离书籍,他继续买书,请别人读书给他听,头脑中依然充满各种引文,可以随口背出西班牙语、英语、古英语、拉丁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和古北欧语的诗句,可以自如引述古希腊学说、中国老庄哲学、北欧史诗、各国文学经典、宗教典籍……仰慕者将他的讲座以及与他的对谈记录下来,集结成书。评论家甚至开始称颂他发展出的口头文学,“他的听众无处不在。这个失明的人依凭拐杖缓步行走,似乎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不过一旦开口说话,就无疑是他那个时代的发言人”。
长久的黑暗也赋予博尔赫斯更多时间想象,当他在头脑中构思润色好一首诗或一个故事,就口述出来,由他人记录。厄运、不幸、挫折、耻辱、失败,都成为他写作的滋养。“我生命的每一时刻都像黏土,要由我来塑造,要由我来赋之以形态,把它炼成诗歌。”
“我有许多家乡”
诚然,作为一位阿根廷作家,南美元素在博尔赫斯的作品中并不鲜见,他出版的第一本诗集是关于故乡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激情》,南美大陆的历史风云,粗犷血性的高乔人也时而见诸笔端。
有人说博尔赫斯是“全球化的”阿根廷人。博尔赫斯有着多元的文化基因和人生历程。他的家族出过诗人,也出过在潘帕斯草原上骑马冲锋的军人。他的祖母来自英国,他从小在英语和西班牙语环境中长大,15岁随家人旅居欧洲,在瑞士日内瓦接受教育,阅读大量东西方经典,学习多国语言,直到22岁重返故乡。彼时的阿根廷尚处繁华年代,大量欧洲新移民涌入,文化活动欣欣向荣。当一些南美作家困惑于“我是谁”时,博尔赫斯反而认为杂糅的历史背景是一种优势,因为不会被任何一种本地传统所束缚。“我有许多家乡。”他说,他希望世界是一个整体,人人都是世界公民。
热情赞颂世界上一切美好的博尔赫斯,似乎注定要在想象中完成与世界的接触,开始是通过阅读想象,后来是在玛丽亚·儿玉的描述中想象。儿玉是博尔赫斯晚年的助手和伴侣,他们一起游历世界。博尔赫斯虽然看不见,但旅行热情不减。在美国加州,他兴致勃勃乘热气球飞越纳帕谷,感叹完全不同于乘坐飞机的真正飞翔之感;在埃及,他抓起一把沙子,撒在稍远处,低声说“我正在改变撒哈拉沙漠”;在冰岛雷克雅未克的旅馆里,他张开双臂拥抱一根巨大的圆柱,体会着领悟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幸福感。
而在所有城市中,日内瓦对博尔赫斯而言格外不同。这个引领他在年少时进入更广阔天地的地方,被他称为“最适于幸福的城市”。他说,“回忆中的一切,包括不幸,都是美好的”,自己总要回归日内瓦,也许是在肉体死亡以后。后来,这一许诺提前实现。1985年11月,被诊断出患有癌症的博尔赫斯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前往欧洲,到达日内瓦时,他选择留下。次年6月,博尔赫斯去世,并安葬于日内瓦,墓碑上,刻着古英语和古北欧语的引文。
版式设计:蔡华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