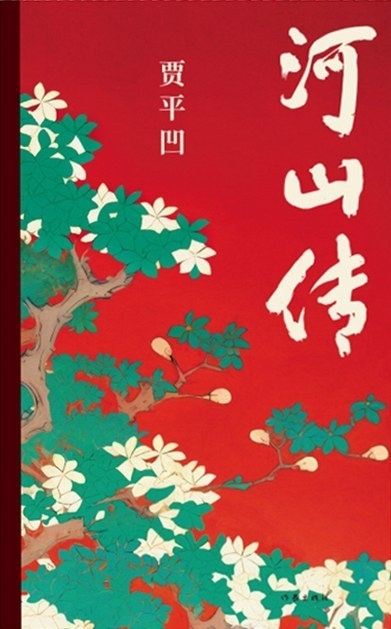读完贾平凹的长篇新作《河山传》,我竟忘了小说是以一则流言开篇。事实上,流言并非以讹传讹,作者通过对洗河、罗山、梅青、呈红等人物命运的描摹和大量细节的呈现,为流言安装了骨架,增添了血肉,讲述了“故事里的事”,再现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民营企业家及其后代等人物群体的生活轨迹和精神走向。
作者在后记里这样写道:“因出生于乡下,就关心着从乡下到城市的农民工,这种关心竟然几十年了,才明白自己还不是城市人,最起码不纯粹。”出于作家对乡下人的身份认同,小说首先呈现的面貌便是一部农民工进城的变迁史,尤其展现了在转型期内,农民工在用工方式及心理层面的变化。在洗河爹的年代里,“即便在建筑工地上搬砖铲沙和水泥,一天管待吃喝还能落下十元”。然而,到了洗河这一代,他们“并不愿意沿街吆喝着收集废品,也拒绝到建筑工地上搬砖、铲泥子、卸水泥袋子”,而是通过个人的天赋和眼光,在机缘巧合之下,结识了民营企业老板罗山,成为城市发展过渡期的农民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洗河的后辈们则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的务工形式。作者在文本中设定了一个始终关注着农民工命运的作家角色文丑良,通过他的描写展现了当下新一代进城农民工的群像。
文学不仅要反映社会面貌的变迁,更为重要的在于对人生意义的深思。洗河爹作为崖底村第一代进城的农民工代表,其终极目的无外乎农村人必须要干的三件事:盖房子,给儿子娶媳妇,为父母送终。而洗河这一代,则开始以新城里人的姿态,直接参与改革浪潮中的风云际会。洗河机灵、忠诚、情商在线,逐渐赢得信任,成为了老板的得力干将。在灯红酒绿、酒池肉林中,洗河始终保持着善良的底色,没有被物欲横流的现实完全同化,他真诚地帮助老乡,真心地爱着梅青。尽管有时他也会控制不住地赌钱,却在每次赌输时都给老家汇去一笔钱,用以弥补内心的愧疚。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农民一直都是作家倾力关注的对象。鲁迅笔下的闰土、祥林嫂等农民形象,具有着丰富的意涵,他们对自身命运的蒙昧既是作家批判的对象,同时也承载着作家深切的同情;沈从文一直以“乡下人”自居,他笔下的湘西农村充满着原始的生命力和纯粹的情感;老舍笔下的经典形象祥子,也是城市里的外乡人,他毕生愿望就是能拥有一辆自己的车,却始终无法实现。到了新时期文学,高晓声的《陈焕生上城》写出了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农民的精神和心理变化。梁晓声在短篇小说《西郊一条街》里,通过户籍制度展现了城乡居民因身份不同所带来的生活上的差异。新世纪以来,以陈应松、刘庆邦等为代表作家的“底层写作”直接把农民工等群体作为表现对象,书写他们的生存困境。
贾平凹通过《河山传》完成了对农民工进城史的勾勒,小说在传统现实主义叙事的框架下,不仅具有浓郁的西北地域色彩,同时也兼具着一定的传奇性。更为难得的是,小说还揭示了潜藏在表象之下人类命运的偶然与无常。洗河的名字源自一次涨水,他事业的转折在于和罗山的偶遇,而罗山的死更是一场意外。
值得深思的是,作家设定罗山在即将完成市内最后一处城中村改造前不幸身亡,或许正是出于其对乡村文明的深情回望。小说取名“河山传”,即为“洗河与罗山”们立传,他们是城镇化进程中处在转型期的典型人物,他们的命运遭际与时代变迁紧密相连。作者在后记里说:“如果五十年,甚至百余年后还有人读,他们会怎么读,读得懂还是读不懂,能理解能会心还是看作笑话,视为废物呢?”我想,这恰恰说明作品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下农民工群体的生活变迁史与心灵史,不仅为当下读者带来情感的共鸣,也用文学的表达方式为后世提供了了解我们所处时代的小说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