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于2011 年底出版了新书《城市的胜利》,引起了从《经济学人》到《纽约时报》等严肃国际媒体的广泛注意。如今,距离此书2011年出版已三年有余,但其影响力依然未减。他在书中提出的众多关于城市发展的问题和观点,对于今天的中国正适宜。为此,小编将其中关于城市人群的观点进行了梳理。
人口密集
创造更多财富
城市是人员和公司之间物理距离的消失。它们代表了接近性、人口密度和亲近性。它们使得我们能够在一起工作和娱乐,它们的成功取决于实地交流的需要。
在20世纪中期,交通方式的进步,削弱了把工厂设置在人口密集的城市地区的好处,许多城市因此出现了衰落,如纽约。在最近30年里,由于技术的进步,更加适合于人们在近距离接触中产生的知识得到了更多的回报,有些城市出现了复兴,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城市。
在美国,在大城市的大都会区工作的工人的收入比不在大都会区工作的工人高出了30%。这些高出的工资被较高的生活成本所抵消,但这并不能改变高工资体现高生产效率的事实。公司之所以能够承受设在城市所带来的更高的人力和土地成本,唯一的理由是城市能够带来足以抵消这些成本的生产效率优势。
生活在居民人口超过100万的大都会区里的美国人比那些生活在规模较小的都会区里的美国人的生产效率平均高出50%以上。即使我们考虑到工人的文化程度、工作经验和行业等因素,这种关系也是一样的。甚至在我们把工人的智商考虑在内时,情况仍是如此。在其他富裕国家,城市和农村地区的收入差距也同样巨大,在较为贫穷的国家,这一差距甚至更为明显。
城市创造共同辉煌的能力并不新鲜。多个世纪以来,创新总是来自于集中在城市街道两侧的人际交流。
在布鲁内莱斯基解决了线性透视法的几何问题之后,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天才开始爆发。他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了他的好朋友多纳泰罗,后者首创了透视法在浅浮雕中的应用。他们的朋友马萨乔后来将这一创新带入了绘画领域。
佛罗伦萨的艺术创新是城市聚居带来的十分宝贵的副产品;这座城市的财富来自更为平凡的追求:金融业和服装业。
但是,今天的班加罗尔、纽约和伦敦所依赖的完全是它们的创新能力。工程师、设计师和交易商之间的知识传播与绘画大师之间的理念传承是相通的,城市的人口密度长期以来一直是这一进程的核心。
底特律败于
失去创新联系
底特律本身曾经是一只嗡嗡作响的蜂箱,它接纳了许多规模不大但相互关联的发明家。但是,福特的伟大构想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摧毁了这座古老而又富有创新精神的城市。
底特律在20世纪的繁荣给各个工厂带来了数十万文化素质不高的工人,这些工厂成了独立于这座城市和整个世界的堡垒。当产业多元化、企业家精神和教育引发创新的时候,底特律模式却导致了城市的衰落。可以说,这座工业城市的时代结束了,至少在西方国家是这样的。
城市不等于建筑
城市等于居民
许多来自遭遇困境的城市的官员错误地认为,通过实施一些大型的建设项目——一个新的体育馆或轻轨系统,一个会议中心或者一个住宅项目,他们就可以领导他们的城市重现昔日的辉煌。毋庸讳言,任何公共政策都无法阻挡城市变革的潮汐力。我们绝不能忽视生活在铁锈地带的贫困人们的需要,但公共政策应该帮助贫困的人们,而非贫困的地区。
开发新的地产项目可能会为一座日益衰退的城市涂上一层亮色,但无法解决其深层次的问题。城市日益衰退的标志是它们拥有相对于其经济实力来说过多的住宅和基础设施。鉴于供应过剩而需求不足,利用公共资金建设新的项目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以开发建设为中心的城市振兴计划是非常愚蠢的,它提示我们:城市不等于建筑,城市等于居民。
在卡特里娜飓风之后,重建的拥护者希望投入数千亿美元来重建新奥尔良。但是,如果将2,000亿美元分配给在这里居住的人们,他们每人将获得40万美元,足以支持他们迁移到其他城市,或接受教育,或购买更好的住所。甚至早在洪灾之前,新奥尔良人已经做了一项很平凡的工作,即关爱那里的贫困人口。当需要大量金钱来帮助新奥尔良的孩子们接受教育的时候,投入巨资来建设这座城市的基础设施真的很明智吗?新奥尔良的伟大之处一直在于它的人民,而不在于它的建筑。认真地考虑联邦政府的开支怎样才能更好地造福卡特里娜飓风的幸存者难道不是更有意义吗?哪怕是让他们迁移到其他地区。
总之,市政府的职责不是为根本无法弥补成本的建筑或铁路项目提供资金,而是关爱它们的居民。一个能够为这座城市里的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以便他们能够在地球的另一端找到机会的市长是成功的,即使这座城市的规模正在不断地缩小。
贫困并非都是坏事
底特律及那些与其相似的城市中存在的难以摆脱的贫困是城市的不幸,但城市的贫困并非都是坏事。显然,在一位参观者见到加尔各答的贫民窟之后,他可能会赞同甘地的意见——质疑大规模的城市化是否明智。但是,城市的贫困也有很多值得肯定的地方。不是城市让人们变得贫困;只是它们吸引了贫困人口。弱势人群流向里约热内卢、鹿特丹等城市证明了城市的优势,而非弱势。
城市的结构可以几个世纪保持不变,但城市人口是流动的。1/4以上的曼哈顿居民五年之前并不住在那里。贫困人口不断地来到纽约、圣保罗和孟买,其目的是寻求某种更好的东西,这是一种值得欣慰的城市生活的写照。
城市贫困与否,不应该基于城市的富裕作出判断,而应该基于农村的贫困作出判断。与一片繁华的芝加哥市郊相比,里约热内卢的贫民区可能看起来十分寒酸,但是,里约热内卢的贫困人口比例远远低于巴西西北部的农村地区。贫困人口没有办法迅速地富裕起来,但他们可以在城市和农村之间作出选择,其中许多人明智地选择了城市。
富裕人口和贫困人口涌入城市,使得城市地区充满了活力,但是贫困人口集中所带来的成本是难以避免的。接近性为理念和商品的交流提供了便利,但它同时也方便了细菌的传播和钱包的盗窃。全球所有较为古老的城市都已经遇到了城市生活的痼疾:疾病、犯罪、拥挤。这些问题从未因为消极地接受现状或愚蠢地依赖自由市场而得到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在21世纪可能会重复欧洲和美国城市的巨大变化,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推动全球的城市化。
建筑保护需
付出巨大代价
城市规划大师简·雅各布斯认为,越是古老和低矮的建筑就会越便宜。因此,她错误地相信,限制高度和保护原有建筑将会确保价格的可承受性。事实并非如此,价格的决定因素是供给和需求。当一座城市的需求上升时,价格就会上升,除非建造更多的住宅。当城市限制新的建设项目时,它们肯定会变得更加昂贵。
保护并非总是错的——我们的城市中的确有许多值得保护的东西——但保护总是要付出代价的。看一下巴黎那种井然有序的优雅吧。在巴黎,干净整洁而又富有魅力的林荫大道笔直而宽阔,与两旁建于19 世纪的建筑相得益彰。我们可以欣赏到巴黎的名胜古迹,因为它们没有受到周围建筑物的遮挡。这种景观得以保留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巴黎的任何建设项目必须通过一种始终把保护工作放在第一位的拜占庭程序。限制新的建设项目并非总是错的,尤其是在拥有建筑遗产的城市里,但这也导致现在只有富裕人士才住得起巴黎。我们不要忘记,巴黎曾经因为接纳落魄的艺术家而闻名。
同巴黎一样,伦敦对19 世纪的建筑也有很高的忠诚度。威尔士亲王本人曾坚决反对建造高大而现代的建筑,以免损害圣保罗大教堂的独特景观。英国似乎已经把他们对于高度的厌恶输出给了印度。
居住在城里比
在郊区更环保
交通技术总是对城市的形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汽车城市,城市是水平式的向外延伸,政府鼓励人们迁往城市的边缘。然而,以汽车为基础的生活方式给整个地球带来了巨大的环境成本。环境真正的朋友是曼哈顿以及伦敦和上海的市中心,而非郊区。在几乎完整地于城市中生活了37 年之后,我又不计后果地体验了郊区的生活,最后痛苦地发现:与居住在城市里的人口相比,居住在树木和草地周围的大自然爱好者们消耗了更多的能源。
很少有什么标语像“思想全球化,行动本土化”这一环境口号那样愚蠢。有效的环境保护主义需要世界的视野和全球的行动,而非狭隘地旁观自己的邻居单枪匹马地试图阻挡建筑工人。我们必须认识到,虽然我们试图通过阻止新的建筑而使得我们的邻居变得更加绿色,但通过推动某些地区开发更不符合环境友好标准的新项目,我们同样可以很轻易地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灰色。
有效的环境保护主义是指把建筑物建造在对生态造成的损害最小的地方。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对为了建造高层建筑而拆除城市里的低层建筑保持更高的容忍度,同时对反对可以减少碳排放的城市发展模式的活动分子保持更低的容忍度。政府应该鼓励人们在中等规模的城市高楼里居住,而非引导人们购买大型的郊区豪宅。如果这种想法成了我们当前时代的主流,那么为这种想法建造合适的住宅将会决定我们共同的命运。
(Edward Glaeser系当代顶尖经济学家、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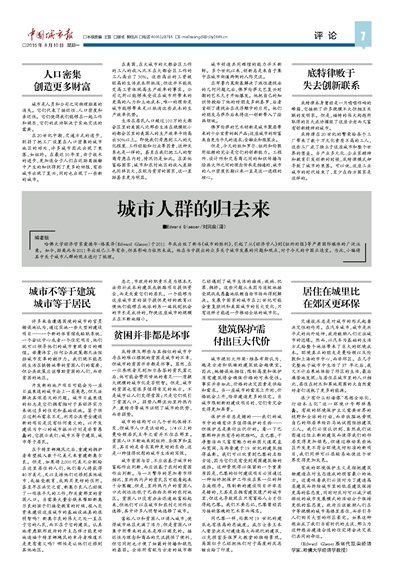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