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人齐欣:采访与写作
记者:齐老师,您关注和研究文化遗产8年了,作为媒体人的工作、生活也慢慢地发生了变化,现在您既是报纸的主编,又是大学的导师,还是各种民间社团组织的推动者或参与者。
齐欣:总的来说,在本职工作之外,我的生活由三部分构成,行走、写作和讲课。行走的时候,记者和研究者的身份不停转换,现在我还承担了许多文化遗产传播方面的课题;另外就是在学校里授课和带实习生。
你看我办公室里这两辆自行车,可不是展品,我家里还有一辆公路车,杭州还有一辆在那边用的车。我曾是单位里第一个买私家车的人,而现在几乎一年都不开一次车了。变化就来自于倾力做文化遗产传播。比如为了现在在做的一个课题《如何规划一条 “遗产小道”——以蜀道为例》,我花了很多时间去考察。在哪一段路骑什么车,我都是认真研究过的。
由记者向研究者的转变,使得我自己达到了一个自由的状态,这自由来自于自信:媒体人既可以用笔去描绘他人,我们也可以在采访时铺陈自己的观点。当然,这得益于人民日报这个严格又宽松的环境,得益于我这28年来在这个平台内的积累和训练——坚持到一线采访,掌握第一手资料。
至今,我都不敢认为自己是个学者。但这么多年做下来,我有一些心得:媒体人能干比写稿多得多的事儿,对于文化遗产传播的研究者来说,目前最应该做的,就是静下心来,去爬爬“如何有效传播文化遗产”这个最难上的“长坡”。别的都能慢慢来,唯独这个领域非常紧迫不能等——等研究明白了,这个事就没了。
记者:大运河为世人所知,常常仅因为它的名字;而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发的文章《大运河究竟有多长?》,却为我们呈现出了大运河古往今来、从南到北的一幅幅历史风情画,让我们看到一条有血有肉、沧桑饱满的大运河。我觉得这是媒体人在遗产保护中的重要作用之一。
齐欣:在文化遗产领域,这么多年来,我们充其量是做到了“宣传”,而非“传播”,这两者是大不同的。如何让人来关注,如何发挥受众的力量,这体现着媒体的能力,也是媒体的责任。
其实我本意并不是成为今天这样跨多领域的“四不像”角色。起因在于,如果媒体人开始对一件事深究又从学术上得不到现成答案的时候,他会突然发现,自己站在了一条路的最前端。这时,媒体的能力和责任都有可能转化为动力。
记者:文化遗产说起来很热,但提到保护却少有人能做些深入的探索。是什么机缘促使您关注文化遗产保护这个领域呢?
齐欣:做新闻的人会有很多的机遇。表面上的偶然其实积累了相当多的必然因素。对“文物”领域我其实并不生疏——我的母亲做了一辈子的文物征集保管工作;我少年时代大部分的假期都是在国家博物馆的院子里度过的。1985年我进入人民日报的时候就分工报道国家文物局,自此从未离开太远。
2005年,我开始做罗哲文专家的助手。当时的想法非常简单,就想怎么样把他的一生总结一下。那时候他已经80多岁了,他跟我讲:“齐欣,其实你应该发挥你的长处,现在我们在宣传上是缺人的。” 但随后,我们将研究的目标,由“宣传”改向了“传播”。
刚刚过去的20年间,中国从文物保护到文化遗产保护,大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远溯至梁思成时代,是由“古董”到“文物”观念的转变;在罗哲文时代,开始了从“文物”到“文化遗产”观念的转变。到了我们现在,则面临由专业保护向全社会力量参与的转变。但这一领域既缺少足量的理论论述,也缺少方法。我们一直在努力,虽然越做越难,但越做越觉得有意义。
记者:“文化遗产”这个概念是外来的,它刚进来的时候媒体没把它当成一个多重要的事儿,但其实它与媒体有着不解之缘。可以说媒体的专业素养决定着保护的分量和保护的成败。
齐欣:可以说,文化遗产传播的特点决定了媒体对于文化遗产报道的功能和作用:第一是要真实,这个真实不是事实的真实,而是其报道的对象、事件的本质是真实的;第二是要完整。“真实性”和“完整性”是文化遗产自身的概念,不是媒体的属性,但媒体报道的内容要坚持文化遗产的这个核心属性。
仅以这一条来衡量,我们以往做过的许多文化遗产节目就需要改写甚至推倒不算——因为我们常常不知不觉地传播了“假古董”。例如蜀道上的剑门关。我们看到媒体的大量报道,这本身没有错。但在我们全新规划中的“遗产小道”体验路线中,反而将其列为:“强烈不推荐”的“浪费时间和精力”项目。为啥?因为它不符合真实完整的文化遗产属性。
这个例子,其实是一种慢慢演化的文化遗产传播趋势:媒体开始基于真实完整性进行判断,并利用传播资源影响公众。这样的例子会越来越多。
学者齐欣:研究与授课
记者:齐老师,说了半天,回到定义上来,究竟什么是文化遗产传播?
齐欣:仅仅是两年前,我们还简单地认为,文化遗产传播不过是“以文化遗产为传播内容的信息活动”。直到现在,仍有许多传媒同行认为,文化遗产传播的应用范围是小众的,所以难以想象或者说根本不需要去搭建文化遗产传播的体系。但是如果你花上一年时间来跟随体验一些文化遗产保护的具体实践,你就会改变看法。
我认为,文化遗产传播的定义应该包括如下内容:首先,它是指文化遗产价值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过程;第二,这种信息的流动模型是反复进行并呈螺旋式上升的;第三,文化遗产传播效果是文化遗产价值的组成部分。
提出上述判断的基础,是基于社会力量已经全面成为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参与者。这就要求我们研究的传播主体,由原来瞄向传统主体比如新闻媒体,开始换了个角度,按照个体、群体和团体进行审视;同时,关注的传播介质也更加广义,比如,原来我们研究传播效果,就是去看报纸、电视,顶多加上网站。但现在,“遗产小道”这种体验线路和自媒体,都反而成为优先研究的传播方法。
记者:这些年来,人们对“文化遗产”的认识是不断变化的。应该说,媒体和研究人员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齐欣:文化遗产使得人们的视野和研究范围都在不断拓展,最重要的观念转变有两个:一个由文物保护视野转变到文化遗产传承视野,这就意味着由“个人或者国家拥有”可转变到“全人类共有”;二是保护范围由关注文物本身,向关注保护风貌转变,这远远超出了一个文物保护职能部门的权责范围。
这时,媒体就具有了双重价值:一是反复唤起受众的关注;二是媒体自身也成为社会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记者:那么,如何做好一档文化遗产传播的节目?或者说应该如何判定一家媒体是否合乎文化遗产传播标准呢?
齐欣:文化遗产传播的节目会越来越多,它的“兄弟姐妹”比如环保传播和健康传播,都走在了前面。我去判断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摸索总结出了文化遗产传播的如下特点,然后逐条对照就是了。这些特点包括:真实和完整性、持续性、同步性;如果传播者都做到了,那还可以再从“社会力量”的角度,深入计算其独立性、主动性和互动性的水平。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给各地的媒体做公益性的培训,让更多的媒体人具备和提高文化遗产传播的水平。
记者:在传播方法上您最近有什么新的研究?
齐欣:做传播很有意思,不光有理论,还要有实践。我会让学生去做很多的功课,比如蜀道、茶马古道以及古村落研究,但看上去比较零散,力量也很弱很分散,我每个月的工资基本上都花在上面了(笑)。有好多学生就问我:老师你为什么要挑选这个项目不做那个更有意思的呢?其实,我们每个试验背后都有总结或者印证方法的目的。
比如,我们在文化遗产传播中,提供了一个“双重认同方法”,我们就通过在杭州做大运河“遗产小道”的示范课题,去印证,如何让远方慕名而来的人,不仅能看到景色,还能感慨大运河的文化遗产价值,从而增加停留的时间。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同学承担了“文化遗产视角下的厦门”的实践课题,挑选了厦大、环岛路、第八菜市场等地点。同学们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厦大还有文化遗产?其实这是一个媒体报道中普遍性的疑问——都说文化遗产就在我们身边,哪儿呢?于是,我们就通过厦大的实践课题提供了另一个“价值成熟度方法”。 引导公众尤其是媒体,认识到文化遗产是活着的和生长的,只是目前“还没有达到佳酿的度数”,但它的基因就已经应该受到保护而不是损害了。
“价值成熟度方法”,对各地的近现代遗产、工业遗产乃至农业遗产价值传播,都有广阔的应用空间。
志愿者齐欣:传承与传播
记者:文化遗产传播是一个大概念,如何通过媒体的传播,让更多的公众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的队伍中来,而不仅仅是政府和专家的任务,这也是您现在努力的方向。
齐欣:是的。回过头来看,文化遗产传播是各种公益传播中最难做、最需要“爬坡”的。我们看环保的传播、医药的传播,受众已经非常容易接受了。这种受众的热情,对文化遗产传播者来说,还是一个日夜都渴望的梦想。真实完整的价值与受众之间尚有很大落差。所以,一个文化遗产传播者面临的压力处境,我称之为“前有鸿沟,后有洪水”。一方面要解决点击率、收视率这些难题,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放弃真实完整的核心宗旨;更重要的是,在快速城镇化的社会发展格局下,等到全民的素质水平都上来了,那个文化遗产就没了。
记者:齐老师,是什么一直在“发动”着您,让您愿意去分享和奉献,去做很多人看来于己无关的事情?
齐欣:表面上无关,其实每一次拆,都和传播不到位有关。我去看没有开发的一些古镇,发现大声疾呼要保护古镇的,和拆了自己家的古建房屋贴上瓷砖的常常是同一个人。为啥,我们还没有真正把文化遗产的价值当宝贝,更不知道哪些环境是可以变的,哪些基因是不能拆掉或者作假的。同时,我们也没有能够持续地尽到监督责任。
对于保护文化遗产来说,我一直坚信,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团火;关键是,要有让火焰产生正能量的方法。
有许多人,都在努力去寻找;我,不过就是其中的一个行者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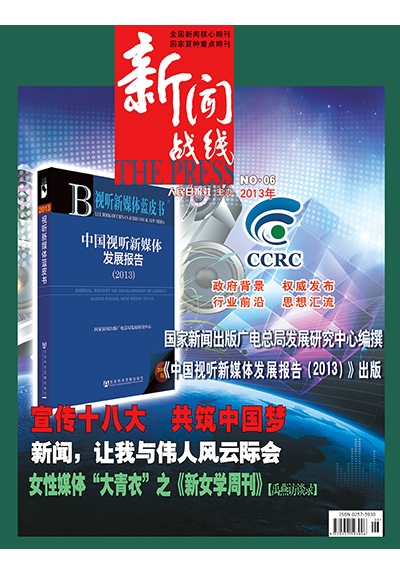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