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女学周刊》新在哪里?
——我希望《新女学周刊》具有“大青衣”的气质,外表优雅大气,内心丰厚沉静,既“悦目”也“赏心”。
记者:禹老师,您主编的《新女学周刊》是中国妇女报的一大亮点,其中既有政策研究、调查报告,也提供丰富的知识、观点,可谓开卷有益。同时,周刊的文章、报道也对决策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是我们慕名来采访您的原因。
禹燕:谢谢你们的关注。《新女学周刊》是中国妇女报去年创办的,当时我们报社新上任的总编辑孙钱斌希望本报更具思想力,更有影响力,使这份中国唯一的女性主流大报更好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我过去在这方面有所研究,所以就担纲主编,做起来了。其实当时压力蛮大的,也花费了蛮多心血。不过正如你们所言,周刊在女学研究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也引起了知识女性的共鸣和妇女工作者的关注。另外,先后推出的《中国女教师发展报告》、《缩小男女工资差距的立法构想》、《关注中国女性人口状况》、《西藏妇女口述实录》等,也得到了有关决策层的关注和重视。
记者:看得出来您的良苦用心。现在的女性媒体比较缺乏有理性、有深度、有力量的声音,这是否也促使您想办好《新女学周刊》?
禹燕:我觉得女性媒体可以类比戏曲中的几种行当:青衣、花旦、刀马旦。我们大量的女性媒体相当于花旦,打扮得很漂亮,活泼可爱,如红娘一样乖巧体贴,专注于生活服务;还有的媒体就像刀马旦一样,为弱势女性提供情感慰藉和法律帮助,这类媒体运作好的就具有侠义之气,运作不好的就以女性受伤害、被侮辱的故事吸引受众;还有一类就像青衣,外表端庄大方,有一种“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内涵,应该看到,一些女性媒体正在努力成为内外兼修的青衣。
《新女学周刊》虽然只是中国妇女报的一个周刊,但我们希望她成为传媒“青衣”,让她外观看起来大气而舒服,不会让人敬而远之,但内在的东西也有底蕴。
记者:人们提到《新女学周刊》,大概都会问:“女学”是指什么?“新”又新在哪里?请您给我们“科普”一下。
禹燕:“新女学”是我们为《新女学周刊》专设的命名。其实,“女学”在中国是一个传统概念,既泛指旧时的女子教育,也特指近代而兴的女子学校,而当“女学”与“新”字相遇后便有了崭新内涵。可以说,“新女学”是与性别相关的学术研究、知识传播与社会实践的集合,是女性/性别研究在中国的本土化表述。因此,“新女学”既携带着女性解放的理想基因,也秉承着女性主义的学术气质,还夹带着中国文化的悠远乡音。它不是对西方女性主义的简单传导,也不仅是少数学者的冥思独白;它致力于性别研究的中国化,它不但要推动性别平等进入决策主流,也要推进两性和谐融入公众生活。
为使新女学“新”,我们力求做到理论上的前沿性、观点上的新锐性、态度上的包容性、表达上的策略性。另外,就是培养新人,给年轻人机会。我们有个栏目就叫《新锐T台》,给在读的硕士生、博士生一个表达平台,而他们青春的智慧也给我带来成就感。
记者:学术问题出现在大众报纸上,而且稿件或访谈对象主要来自科研院所、专业院校,有可能会让人感觉比较“阳春白雪”,那么,您在小众话题与大众媒体之间如何平衡呢?
禹燕: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好。一张报纸,一份周刊,怎么样做更切合报纸和读者的需要?当时我们也确实费了很多心力。两个版的周刊,肯定不能面面俱到,所以只能尽可能在影响到决策层的话题上做到最大化。
我们的定位有三个主要方面:一是为女性/性别研究者服务,二是为妇女工作服务,为有关决策者提供分析与决策依据,三是为有性别平等理想的读者服务。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只讲纯粹的理论,我们有两个版面,一版是注重于理论的《知?道》,传播女学的知识和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另一版《行?范》主要是关于性别平等的实践性探索,包括在推进性别平等中一些有价值的范例。理论这部分更多是面向决策层和学界,目的是增加对决策层的影响力和专业影响力,实践这部分更多的是面向行动者,更大众一些。我们试图把大众化的传播和对决策层的影响结合起来。
例如我们有一期对黄菡的访谈,因为她是公众人物,既有新闻热点,也有公众关注度。很多人对中国妇女报、对《新女学周刊》不一定感兴趣,但是黄菡可能就会吸引大家的关注。她对我们记者设计的问题回答得也不错,有角度有深度,传达出了一种性别平等的价值观,会在青年中产生影响力。另外,我们对一些热点话题也都展开讨论,如有一个话题为“可恶的丈母娘”,分析在家庭伦理剧中为何丈母娘的形象总是很可怕,涉及传统文化对女性的偏见、伦理价值的性别冲突等等,这样就可以吸引普通受众来看。
性别视角与学术的新闻化传播
——每个人都需要一个思考问题的方法、工具:你怎么看人,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你利用这个工具就知道如何分析、解读新闻事件。
记者:作为一个非学术类报纸,《新女学周刊》的稿件来源却多来自科研院所和专业院校,这让我们很是好奇。
禹燕:回想一下《新女学周刊》一年多来的编刊历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突破难点的过程。我们不是学术核心刊物,在学界影响力很小,约稿时专家学者积极性不高。我们只能尽心竭力,以推动性别平等和女学研究的热忱去感召作者,以真诚沟通和对稿件的精心编辑去打动作者,以选题设计的专业性去获得专家的认同。作为理论周刊的编辑,首先要有专业性,这样你才能理解并尊重作者的思想,并让你的思想也得到尊重。
文章发表以后引起的反响,让有的学者非常感慨:搞了多年研究,写了那么多论文,但社会影响却不大。但是通过新闻传媒的推介,却能引起决策层和大众的关注,他们觉得自己的研究有了现实价值,由此对传媒也更有亲近感了。
记者:您的职业理想是做“学者型编辑”、办“有思想的媒体”。把学术问题用新闻的方式传播出去,既需要不惧市场的勇气又需要大胆创新的思路,可否把您的心得和我们分享一下?
禹燕:说起如何推动学术的新闻化传播,我们也只是在以下方面努力尝试。
首先是抓重要的时间节点,通过主题性策划,体现理论的时效性。比如我们在教师节做的《中国女教师发展报告》、在重阳节做的《性别视角下的养老制度变革》等等。其次,是抓现实热点,推动学者为改变现实而思考,体现学术研究的社会干预性,比如“建言公共政策系列”推出的《关于缩短男女职工收入差距的立法构想》、《让女性原始创新融入农业科技创新主流》等建议,不仅接地气,也都得到不同层级决策部门的重视。还有就是抓理论研究的前瞻性,体现理论传播的新闻敏锐性,比如我们关于女性与税收政策改革等文章就具有开创价值。
记者:把“女性/性别”作为一个切入点去看新闻事件,这是一个新鲜的角度,能看到不同的呈现。
禹燕:对。每个人都需要一个思考问题的方法、工具:你怎么看人,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你利用这个工具就知道如何分析、解读新闻事件。比如美国校园枪击案,别人看这件事,会从很直观的角度去看,但是我们请的专家是从“母婴关系”的角度——凶手与他母亲之间的关系入手分析,这就是亮点。这位作者之前研究过母婴关系,她把过去研究过的东西,跟这个新闻一嫁接,一个很好的分析就出现了。我们很多专家跟编辑之间,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沟通——他们通过看你怎么编,就知道该怎么写。有的专家越写越好,原来写的东西可能学理性很强,但是渐渐地,就会把这些新闻点也勾描得特别好。
最近我们推出了一个“反暴力”的系列讨论,其中一篇文章谈到“足球需要女性主义”,讲的是加拿大、尼泊尔等国如何利用足球的公平游戏规则教育青少年参与反暴力,非常有新意,也有新闻点。我们就把标题改为《反思并重塑男性气质 让“足球”加盟反暴力》, 这篇文章引起不少男性的兴趣。
女性解放与个体幸福感
——妇女解放的最终价值就是使个体更有幸福感。我提倡一种包容的态度。女性应该怎样做女人,要看“这个”女人愿意做什么,尊重每一个女人自己的选择。
记者:据我们所知,您20多年前就已经是研究女性主义的“小名人”,现在也还在从事与之相关的工作,您当初是如何与女性主义结缘的呢?
禹燕:我当初的理想实际上是当个“红学家”,去中国艺术研究院下面的红楼梦研究所。结果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以后,却被分配到出版社当编辑。离学者梦有点远,多少心有不甘。后来赶上了上世纪80年代末女性学在中国兴起的机缘,我自己呢,从小比较要强,可能也有一些女性主义的“慧根”吧,就写了《女性人类学》这本书,当时算是这个领域的“开创之作”。写完这本书之后,因为种种原因我游离在女性主义研究圈子之外。主编《新女学周刊》让我回归女性/性别研究,我感谢妇女报给这个平台。我们的黄海群社长、孙钱斌总编辑都是有性别平等理想的人,他们支持我用对学术的理解,对社会需求的理解,对新闻的理解,来推动学术的新闻化传播,让学术更鲜活,更有社会价值,为思想者搭建推动社会变革的桥梁。
记者:您说得对。理论不能束之高阁,只有落到实处,才有现实意义。有了这么多年的女性主义研究的积淀,我们想知道,在您的观念当中,女性在社会中应该充当什么样的角色呢?
禹燕:我觉得女性文化和男性文化的一大区别在于,男性文化是强调群体价值观的,女性文化强调个体价值观。女性应该扮演什么角色,要看“这个”女人愿意做什么,社会不要对她强求。我觉得有些女人,她愿意承担公共身份,愿意做更多公共领域的事情,在事业上奋发有为,社会要认可她的价值。有的女人,愿意相夫教子,她若觉得这是她的人生理想和幸福所在,社会也应该尊重她的选择。社会应该尊重个体价值。我认为,妇女解放的最终价值就是使个体更有幸福感。
有人会疑惑,女性回归家庭是否是妇女运动的倒退?其实,国外的实践表明,一些回归家庭的女性,如果受过很好的教育,一旦履行了家庭的阶段性责任之后,就会成为公民社会很重要的力量,参与公共事务。国外很多社会运动都是由家庭主妇发起和推动的。经过家庭生活的沉淀之后,她们看世界的方式会不一样,对人和人、人和社会关系的理解会不一样。所以,我提倡一种包容的态度。
记者:现在中国女性地位有很大提高,特别是近些年,甚至有那么点矫枉过正。比如“妻管严”现象,比如相亲节目中流行的“女选男”,再比如女孩喜欢“灰太狼式好老公”……您怎么看待这些现象?
禹燕:电视相亲节目中流行的“女选男”模式,可以说是编导者为迎合当代年轻女性的择偶愿望而做的选择,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女性自主意识的增强。但仔细观察也会发现,在“女选男”的表象下,根深蒂固的择偶观、男强女弱的性别观仍时有表现。在我看来,电视相亲节目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有时它张扬着女性的权利,有时又以弱化甚至伤害女性自尊为噱头,依然摆脱不了男性主导的观念惯性,需要加以适度引导,使这个平台能传达更多正面的性别价值观。
人们常说的“妻管严”现象,只是反映了个别家庭对夫妻关系的选择,就整个社会而言其实并不具有普遍性。有相关调查显示,在家庭消费上,虽然夫妻可以共同商议,但购买大宗商品的决定权往往在丈夫手里,另外,在家务劳动时间上女性也普遍多于男性。我想,女孩之所以喜欢找“灰太狼式好老公”,一方面是她们的自我意识在增强,另一方面还是因为“灰太狼式好老公”太少,“他”只是儿童动画片中虚构的角色。
记者:您如何评价一百多年前兴起的国际妇女解放运动?如何评价中国“五四”以来的妇女解放?中国有个口号是“妇女能顶半边天”,这个调门应该说是很高了,但实际上问题解决得怎么样呢?
禹燕:这是一个宏大而深邃的问题,我谈点个人的理解吧。一般来说,国际妇女解放运动经历了三次浪潮,发端于19世纪后半叶的第一次浪潮主要是为妇女争取选举权、教育权、就业权。第二次浪潮20世纪60~70年代兴起于美国,并波及各主要发达国家,主要内容是批判以父权制为核心的不平等的社会权力结构,推动女性走向公共领域,强调消解男女差别。第三次浪潮从20世纪80~ 90年代开始并一直持续到现在。概括地讲,女性解放运动经历了从争取女性权利,到批判男性权力,再到反对二元对立、认同性别差异、寻求性别融合的历程。女性解放运动既是一种社会运动,也是一种理论思潮,对推动社会变革、推进社会公正以及变革传统知识体系都起到了历史性的作用。
中国“五四”以来的女性解放运动既有男性思想家和革命家的倡导,也有觉醒的知识女性的参与和推动,和西方女性的独立奋斗有很大区别,所以有学者以“与男共舞”来概括,这一特点也决定了中国女性解放在思想与路径上的独特性。当时提出的许多思想、目标现在仍然具有特殊价值,值得深入挖掘,所以《新女学周刊》专设了《女史重建》专栏来回顾历史并向先驱们致敬。
“妇女能顶半边天”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口号。应该看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妇女解放确实取得了许多值得称道的成就,但是,也不必讳言,我国的妇女还面临不少问题。女性在很多领域获取资源、机会、保障的能力与水平都低于男性,女性、女童受暴力侵害的事件也时有发生。因此,要真正贯彻男女平等这个基本国策,需要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向互动中协力推进。其中,立法的完善是前提,执法的到位是保障,社会观念的变革是基础。
记者:您似乎更倾向两性之间的一种温和合作的精神,而非性别之间的对抗与竞争。
禹燕:我理解的女性主义既是一种思想方式,也是一种生活态度。性别平等与社会公正是它的核心价值。性别平等不仅是男女平等,不仅关注女性权益,也关注男性权益,还要关注其他性别少数群体的权益。作为一个女性媒体人,我希望能借助中国妇女报这个平台,以理性、包容的态度把性别平等的理念传达出去,得到更多人的关注。
今年三八节,我们报社还联合中央主要新闻单位负责人共同发出了《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媒体倡议书》,号召媒体做性别平等的传播者、守望者、践行者,就是希望媒体能在这方面做得更多,不只是女性媒体,而是所有的媒体人,都能参与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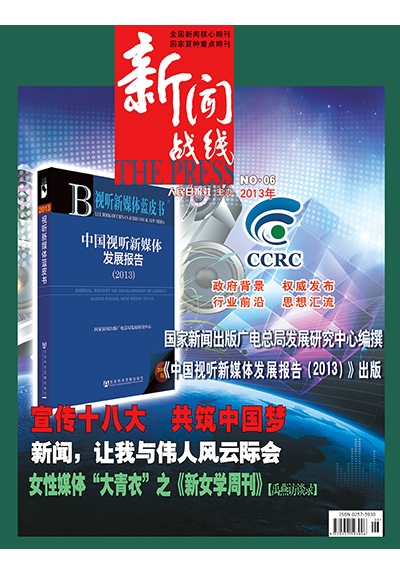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