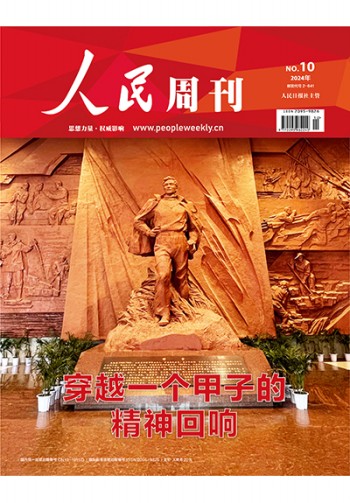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让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形势的崩塌与政治秩序的动荡,迫使中华民族在绝境中寻求出路。
杜亚泉文化观的理论阐释
杜亚泉审时度势,开启了对东西方文化的探索,重新思考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建设与发展的新道路。
(一)从全盘否定到有机调和
清末,封建统治颓势难掩,举国上下都迫切寻找新的出路。鸦片战争之后,封建地主阶级开始接纳并吸收西方的制度、文化,西学成为人们竞相学习、推崇的对象。但随着一战的爆发,西方文明的弊端日渐显露。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深刻描述了欧战后城市和乡村的疮痍满目,曾经西方人引以为傲的富足生活也在顷刻间化为废墟。
1916年,杜亚泉在《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中将东西方文明概括为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他认为,固然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均不圆满,但东方固有文化仍然具有无法替代的优越性,故而应将西方文化融合到传统文化中,用传统文化来调和西方文化,也用西方文化来补充、巩固传统文化,使其成为具有普适性的人类共有的精神力量。
1917年,杜亚泉在《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中表示,一战的爆发揭露了西方文明发展性与延续性上远不如传统文明更加系统、完整的弊端;也揭示了西方文明的问题远远大于东方文明,中华民族逐渐发掘到西方物质文明的迷惑性与虚幻性,从而更能体悟东方文明的纯粹与中正。之于都不完美的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杜亚泉认为,要“以科学的手段,实现吾人经济的目的。以力行的精神,实现吾人理性的道德”,最大化地利用、吸收西方文明的积极之处,同时也最大化地保留、传承东方传统文明的根基与精华。
(二)从“静”与“动”到新文明
新文化运动时期,革命派和守旧派的论战为“中体”的未来提供了新思路。杜亚泉在《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中提道:“平情而论,则东西洋之现代生活,皆不能认为圆满的生活;即东西洋之现代文明,皆不能许为模范的文明。而新文明之发生,亦因人心之觉悟,有迫不及待之势。”他认为,东西方的现代生活皆不完美,战后新文明的产生是不可阻挡的必然趋势,也是全人类的诉求与愿望。一个社会只有当经济与道德均发达,才能被称为文明。文明时不时的“生病”是人类必然会经历的,如今的东西方社会正经历着“病”的侵袭。而对社会“病”的治疗,是不分民族、国家与人种的,是全人类共同的任务与事业。
1918年,杜亚泉在《迷乱之现代人心》中鲜明指出了中国社会精神生活的空虚与无序:“决不能希望于自外输入之西洋文明,而当希望于己国固有之文明,此为吾人所深信不疑者。盖产生西洋文明之西洋人,方自陷于混乱矛盾之中,而亟亟有待于救济。”针对如何拯救迷乱的现象,杜亚泉表示,只有中国的固有文明才能救中国,也只有以中国固有文明为基础形成的新文明才能拯救西方于水火。
杜亚泉的文化调和论肯定了中国固有文化的地位与价值,理性看待其弊端,积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乐于创造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的适应时代与全人类的新文明,极大地体现了东方思想家所特有的中庸思想与宽广胸怀,彰显中华民族经历了几千年的沉淀所蕴含的深厚包容性与适应性,为新时代建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方法论。
文化主体性视域下杜亚泉文化观的时代价值
巩固文化主体性推动着新时代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积极维护自身文化的独立性、主导性与发展性,为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的思想交汇中独立自主地融合与发展开辟道路。杜亚泉积极推动着东西文明的融合与调和,对如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接续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
(一)促进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助力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文化主体性的建设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时代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充分挖掘各国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各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至于如何真正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杜亚泉文化观给予了充分的回答。
五四运动时期,杜亚泉清楚地剖析了东西方文化差异的现象与根源,提出文明的调和势不可挡,西洋社会输入资本,我国提供劳动,对于两边社会都有益处。在文化调和的同时,西洋动的文明的弊端要靠中国固有的静的文明来救急,而中国固有的静的文明,则因系代表多数人之文明,而具有无比优越的价值,所以勿须效法西洋动的文明,西方文明反而需要东方文明的调和。
我们想要巩固好文化主体性,就需要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中华民族最坚韧的民族信仰与文化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想要在新时代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就需要融入新的时代要求与先进理论。杜亚泉调和思想始终坚持中华文化的主体性,以固有的文化为思想载体,也汲取着各国优秀文化与思想,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在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同时,也为世界人民提供健康的、普世的精神力量。
(二)激发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要努力从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形成和积累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和智慧,延续文化基因,萃取思想精华,展现精神魅力。要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把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一起来,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想要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就需要传承好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就需要树立正确的文化观,激发中华民族文化自信。
杜亚泉文化观为激发中华民族文化自信提供了积极的解决思路。在《再论新旧思想之冲突》中,杜亚泉主张新旧思想要根据时势的变化而变化,当时代成为新旧的标志时,主张创造未来文明的即为新,主张固守中国习惯的即为旧。我们不能全盘摒弃固有的文化,而是要学会将“中庸”的态度融合到文化的发展当中。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提供深厚的思想底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有鉴别地对待、有扬弃地继承。杜亚泉的文化观兼顾了文化认同的维系与文化自觉的培养,对中华民族在信息繁多的新时代保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认同与积极践行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要真正激发中华民族文化自信,让文化的种子生长在每一位中国人民的心中,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对杜亚泉文化观不足之处的再审视
杜亚泉文化观既是新文化时期中华民族面对西方思潮时坚守东方文化阵地的坚强支柱,也是新时代推进中华文化转型与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有力指导。但他的论述与调和思想的实践路径仍旧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杜亚泉过分强调了文化的作用,一定的文化由一定的经济、政治所决定。而杜亚泉则忽视了东西方之间科技水平的巨大差距等具体实际,而是将东西文化孤立在社会具体实际之外进行分析。另外,在中华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过程中,对于何者为精华、何者为糟粕的定义略显模糊,观点有些脱离当时的中国国情与身处的时代背景。杜亚泉文化观在新文化时期的局限性,是他在论战中败下阵来的根本原因。
巩固文化主体性、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推动文化的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重要任务。在这一根本目的基础上,一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乃至全人类的优秀文化成果,都能够被吸纳、改造和扬弃,成为新时代中华文明体系中的精华。正如此,让杜亚泉文化观得以在新时代再一次展露出其科学性与实践性,推动新时代中华民族现代文化的接续发展。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