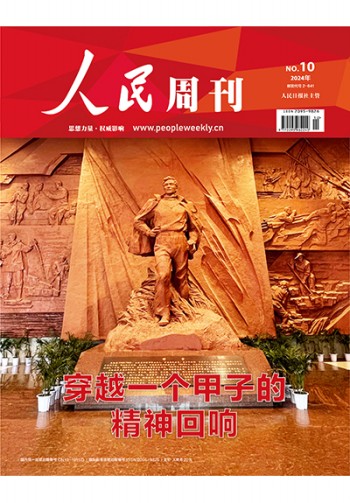五四运动前后的东西文化论战,明线是论“东西”文化,但暗藏一条论“到底什么是真正历史观”的暗线。这条暗线在局势混乱之时,甚至决定着明线主题的变化。本文尝试从五四运动之前进化论历史观的传入开始,探究在面对东西方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中国知识分子持有怎样不同的历史观,如何在时代中作出自己的选择,兼论正确的、科学的历史观对我们把握历史发展规律、迎合历史发展大势的重要作用。
历史观何以用作研究角度?
历史观是指人们对人类社会历史问题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虽然在具体提法上还有待商榷,但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时代主题是救亡图强已经基本成为学界共识。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向外寻找救国良方,对西学进步性的肯定是五四东西文化论战的重要背景。在希望学习西方文化改良本国境况的强烈愿望下,进化论的“物竞天择”概念很有解释力。为了能被“天择”,唯有努力追赶西方。儒家传统文化是古代中国的核心意识形态,从进化与退化的逻辑上细看,儒家有一种鲜明的崇古复古观念。近代后进化论历史观传入中国后,中国知识分子先是尝试用“天理”历史观对其进行改造与融合,但“改良派”“革命派”的出现表示,儒家历史哲学因盛赞三代之治的理想社会,而形成的退化论与循环论“三代”历史观在日新月异的新时代必须要面对来自进化论历史观的直接进攻了。这就是历史观角度考察五四文化论战的背景。
五四时期历史观如何影响学者观点?
以杜亚泉等人为代表的持传统儒家历史观的知识分子,面对一连串战争的失败,虽然已经无法否认西方文化所具有的某种优越性,但在历史观层级上决不能承认中国文化的“陈旧”,否则在“新”与“旧”的单向逻辑中,就完全无法与进化论历史观持有者抗衡。因此,他们否定“新”与“旧”的文化二元对立结构,一方面将文化的时代性抹去,另一方面着重寻找西方文化的“落后性”。他们使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这对在价值上区别并不明显的概念来解释东西文化。五四论战时期,杜亚泉将其引申为“静”和“动”两类文化,东西方文明“乃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虽然持儒家传统历史观者通常也对西方物质文化表达一定程度的肯定,但其历史观决定了他们认为统整一切的标准——“精神”标准。在复古观念的影响下,他们在提到精神世界的理论基础时,常常断在诸子时代,最多提及汉儒,很少探讨之后的中国古代思想文化。
与传统儒家历史观的解构相反,进化论历史观的信奉者依照进化论历史观暗含的“新旧”与“优劣”价值判断,不遗余力地链接“新旧”与“东西”。陈独秀在论战初期就大胆提出“新旧”设想,将“生物进化论”列为“欧罗巴真正近世文明”的三大特点之一,认为“代表东洋文明者,曰印度,曰中国……其质量举未能脱古代文明之窠臼,名为近世,其实犹古之遗也”。对于“新”的赞赏和推崇也毫不吝啬,“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李大钊也提出关注“历史的法则”,“康德之流已既想望凯蒲拉儿、奈端其人者诞生于史学界,而期其发现一种历史的法则,如引力法则者然”。瞿秋白同样关注文化的时代性,他指出:“东西文化的差异其实不过是时间上的……”可见虽然基本原理和理论方法还不尽完善,但东方文化为旧,且不受人意志转移地要让位于“新”的思想,已经成为想要对抗儒家传统历史观的新派知识分子群体的某种共识。
历史观角度考察为何重要?
(一)探寻文化调和派的思想本质
有观点认为,“杜亚泉、章士钊、李大钊、高一涵等人皆为英伦自由主义的信奉者和调和主义的倡导者”。但假如以历史观考察之,早期李大钊虽然萌生过与章士钊等人相似的调和观点与立场,但随着其进化论历史观的成熟、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确立,他的调和思想逐渐与持传统历史观的章士钊等人渐行渐远。他虽然承认中西文化有调和的可能,但却是站在“新文化”这一时间维度去谈的。在阐明自己调和观的《辟伪调和》一文中,他直接提出自己立论的根基“是义也,斯宾塞、穆勒、莫烈、古里夫森诸君信之……愚亦笃信之而不疑”。他还说“宇宙进化的大陆,只是一个健行不息的长流,只有前进,没有反顾;只有开新,没有复旧……物质上、道德上,均没有复旧的道理!”可见,在“新旧”问题上,李大钊作为一个进化论史观、未来唯物史观的坚定信仰者,他的立场是毫不含糊的,那就是抵制“复古主义”思潮以及一切装点这股思潮的虚假“调和”,敦促中国的知识分子与年轻人利用好一切现有思想资源,站到新文化、新道路上来。
(二)理解“现代性弊病”显现时的思想分流
五四时期,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入侵,一些现代性弊端如背信弃义、物欲横流也在中国凸显出来。无论当时的学者是否能意识到这种“现代性”,这种社会发展“弊端”在不同的史观视角下呈现出了不同的形态。文化保守派认为,这种弊病令他们恐惧,预示着进化论的终结,而进化论历史观支持者则转而投向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进化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等新思潮。当时的五四学者中少见“后现代主义”立场,要不左转走向社会主义,要不右转走向保守主义。有观点认为,唯一站在后现代立场上的是国学大师梁漱溟。上述思想分流的出现与历史观的作用密不可分。持进化论史观者依照进化的视角向未来寻找解决办法,而在退化论或是循环论历史观的视角下,保守主义者就只能回到历史中、传统中去寻找答案。在这一时期,实用派进化论史观者相对失声,理性派进化论者和传统文化派同时高歌猛进。而梁漱溟将西方化的世界历史视作是第一个纪元,东方化的世界历史纪元反而是未来的纪元。秉持“新旧”但是调换“东西”的倒转进化论,本质还是以“现代”为本位考察未来,因此不惧怕面对“现代”的真实问题。
东西文化论战中历史观抉择有何当代启示?
(一)始终坚持唯物史观的正确立场
唯有坚持唯物史观正确的、科学的立场才不会迷失在时代洪流中,把握住历史发展的规律和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顺势而为、奋发有为。“持什么样的历史观,就决定了什么样的道路选择,唯物史观是我们共产党人认识把握历史的根本方法。”在唯物史观视角下,“新”与“旧”的关系是明确的,“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
(二)充分认识文化考察的复杂性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进化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但马克思强调在考察这种变革时,需要注意有两种变革: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和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意识形态的变革。因此,各民族各地的经济基础变革具有多样性,由其决定的上层建筑因而出现复杂的双重多样性。要想树立正确的文化观,必须从上层建筑的双重多样性入手,细致地辨别“传统文化”与“落后性质的文化”。
(三)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以更好建设社会主义为标准
面对浩如烟海的传统文化资源库,判断其是否“优秀”,要看其能否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是否符合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能否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习近平文化思想“七个着力”重要要求亦将“加强党的领导”“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排在前列。因此,面对风云变化的时代现实,我们首先要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寻找精神力量,这样才能走向历史正确的一边。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