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有两种:一种是官藏,一种是私藏。与官藏受皇命不同,文人“藏君子之书”是一种自发自觉的文化活动。文人士大夫穷一生之力,耽耽简编,艰险不避,用情于书,几成痴迷,孜孜追求精神生活的体悟和内心修养的悠逸。如果说文人士大夫读书著书抱有求取功名之心的话,那么,访书聚书赏书更多体现的是一种趣味、格调和境界,彰显了文人士大夫藏书生活的文雅气质和审美追求。
访书——
“但愿得者如我辈,即非我有亦可喜”
以书会友,访书即是访友。文人为访求好书而自甘清苦,纵使散尽千金,却怡然自乐,其趣味高雅。
聚书缘自爱书。爱书是文人与生俱来的基因,这种基因根植于对知识的顶礼膜拜。“读未曾见之书,历未曾到之山水,如获至宝,尝异味,一段奇快,难以语人”(谢肇淛《五杂俎》)。也有异于常人的“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晚唐皮日休诗云:“惟书有色,艳于西子;惟文有华,秀于百卉”(《六箴·目箴》)。更重要的是,书还是文人安身立命之所,是思想的源头活水。宋代朱熹诗云:“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月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观书有感》)。生活中只要有了书,哪怕“木落水尽千崖枯”,也能“迥然吾亦见真吾”(翁森《四时读书乐》)。
因爱书而访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董其昌《画禅室随笔》)是文人的治学箴言,一则有“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下》)的古训,须“行万里路”来验证“读万卷书”的真理性。二则不行万里路,读不到万卷书。访书不易,甚至不亚于取经。其实,唐僧取经也是一种访书。明代胡应麟爱书访书,遍游吴齐鲁赵卫各地,“穷搜委巷,广乞名流,录之故家,求诸绝域,中间解衣缩食,衡虑困心,体腹筋骨靡不所惫”(《经籍会通》),访书之艰辛自不待言,文人乐此不疲。他们流连“槐市”,或与书友雍容揖让,侃侃訚訚,或侧身书铺,不问寒暑,沉迷其中。宋代郑樵访书10年,“闻人家有书,直造其门求读,不问其容否,读已则罢”(《夹漈遗稿》)。清代袁枚亦爱书如命,“每过书肆中,两脚先立定。苦无买书钱,梦中犹买归”(《对叹书》)。
访可爱者聚之。纵使访书过程艰辛,但文人并不贸然行事,总要依照自己的眼光与喜好来取舍一番,甚为挑剔。“藏书者贵宋刻,大都书写肥瘦有则,佳者有欧、柳笔法。纸质匀洁,墨色清纯,为可爱者”(张应文《清閟藏》)。越是“可爱者”,聚书的代价越是不菲,遇希贵者甚至得割爱让出田庄美妾。据吴翌凤记载,“嘉靖中,华亭朱吉士大韶性好藏书,尤爱宋时镂版,访得吴门故家有宋椠袁宏《后汉纪》,系陆放翁、刘须溪、谢叠山三先生手评,饰以古锦玉签。遂以一美婢易之,盖非此不能得也”(《逊志堂杂抄》)。如此书痴,真让人哭笑不得。
聚书——
“读书得此护持,万卷尽生欢喜”
访得可爱书,需有雅室居。或楼或室,文人聚书旨在构建一个独特的心灵空间,任天地岁月悠悠,其格调高贵。
斋号之雅。文人藏书之所并无定规,可筑楼于山间水滨,可取一室隐于市井郊野,斯是陋室一间,亦要出尘清雅。东晋陶潜辞官归隐“归去来馆”,写下千古名篇《归去来辞》。清代范钦建“天一阁”,藏书甲于两浙,黄宗羲、全祖望皆为其作记。晚清曾国藩有“富厚堂”,又称“八本堂”,自取家训以记之。不仅室名斋号有雅称,文人也因藏书得美名。唐代李泌家中藏书汗牛充栋,被誉为“书城”,后汉曹平积石为仓以藏书,号曰“曹氏书仓”,五代孟景翌出门藏书跟随,终日手不释卷,谓之“书窟”,不一而足。如细细玩味,又别有一番风味。
藏室之雅。清代郑板桥书斋有联云:“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文人藏室“绝俗之趣”,宜小宜香宜雅。小能聚气,不热不寒,连乾隆帝三希堂也不过八平方米而已。香即芸香、檀香和茶香,书中所夹芸草有异香,可避蠹驱虫,“故藏书台亦称芸台”(徐坚《初学记》)。檀香可宁神,令人思绪悠远,南宋陆游《即事》云:“语君白日飞升法,正在焚香听雨中。”茶香可静气,煮雪烹茶恬淡至极。如仿倪瓒之清閟阁,“古鼎法书,名琴奇画,陈列左右”(《明史》本传),刹那间,一股古雅深邃、静逸无边的书香气息就能扑面而来。
诗印之雅。文人喜吟诗,每有所得,或抒藏书之情,或言藏书之志,留下了许多藏书诗,也留下了许多文坛美谈。最著名者莫过于唐代韩愈赠予邺侯李泌的《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云:“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皆牙签,新若手未触。”这就是典故“邺架之藏”的出处。如果看到谁家前门高悬“邺架留芳”牌匾,则基本可以判定,主家是个读书人,且姓李无误了。除了藏书诗,文人还善刻藏书印,一枚枚小小的方印,或宣示藏书主人,如田吴炤之“荆州田氏藏书之印”;或抒发藏书之情,如陈简应之“精校善本,得者珍之”印;或表达藏书之趣,如李馥之“曾在李鹿山处”印等。这些印章篆刻精美,印泥鲜艳夺目,使人赏心悦目,既流露出文人的爱书之情,又表达了文人的读书之乐,还体现了文人某种豁达与通透。
赏书——
“书味在胸中,甘于饮陈酒”
不为功利赏闲书,每有会意则欣然忘食。文人在赏书读书中,追求人生真味,陶然自得,其境界高远。
藏书非为读。文人藏书何其多,岂能遍阅?不为读,仍藏之,何故?有三功也。一曰校书之功。书在传抄、刻印、排印时,错误在所难免,如不及时校勘,其害深也。二曰治书之功。北魏李业兴“爱好坟籍,鸠集不已,手自补治,躬加题帖,其家所有,垂将万卷”(《魏书·李业兴传》)。三曰抄书之功。南宋尤袤“每公退,则闭户谢客,日影记手抄若干古书”。明代叶盛“服官数十年,未尝一日辍书。虽持节边檄,必携抄胥自随。每抄一书成,辄用官印识于卷端。其风流好事如此”(钱大昕《听雨轩集跋》)。正是文人忘我的校书、治书和抄书,为后世留下了无价的精神宝矿,如今的古籍善本就有其不可磨灭的功绩。
书非借不读。家有藏书万千,可自嗜、可借观、可共赏。比如说明代越琦美,“性嗜典籍,所裒聚凡数万卷,绝不以借人”(龚立本《烟艇永怀》)。不外借,无非担心一旦丢失便不可再得,“仅有单行之本,烬后不复见于人间”(曹溶《绛云楼书目题词》)。对于不外借者,人们应当抱以理解和同情。当然,借观是值得鼓励的。文人与书为友,亦能因书得友,“幸而遇赏音者,知蓄之珍之”(曹溶《流通古书约》)。借人典籍者,也当须精心呵护,如遇缺坏则为之补治。晋人范蔚“家世好学,有书七千余卷,远近来读者恒有百余人,蔚为办衣食”(《晋书·范平传》)。这种风范值得后人好好学习,因为藏书不只为情趣,不用不借不考,就如“守书奴”无异,行之不远矣。
清淡好读书。“读书之乐何处寻,数点梅花天地心”(翁森《四时读书乐》)。文人自视清高,一种难能可贵的清高,只有这种清高,能令其于物欲横流中洁身自好,超凡脱俗。或坐或立于书斋别院,“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尤袤《遂初堂书目序》)。人生最惬意、最纯粹的时光,莫过于这种自在随性、自由遐思的读书时光。于文人而言,一旦步入书斋,拿起书来赏玩也是一种心灵慰藉。陆游诗云:“剩喜今朝寂无事,焚香闲看玉溪诗”(《假中闭户终日偶得绝句》)。净手焚香,品茗听音,在暖阳正好的芸窗下,静坐清读,这是一桩多么有仪式感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说,文人因拥有了聚书之乐,而拥有了门槛最低却是世间最美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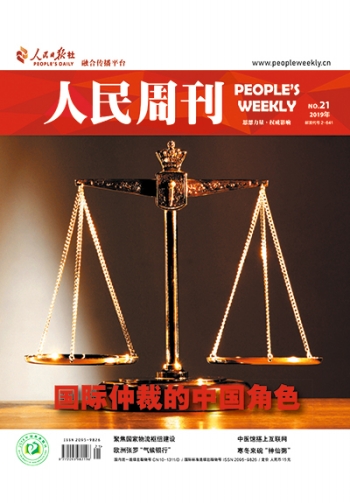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