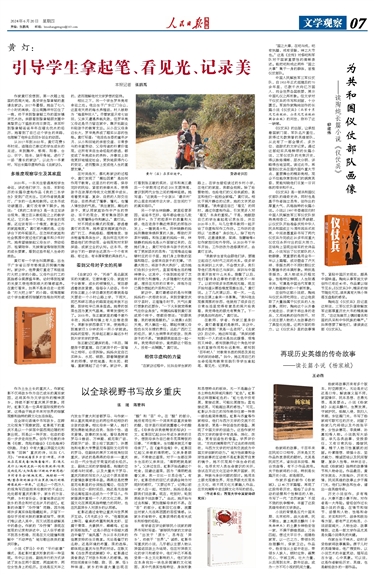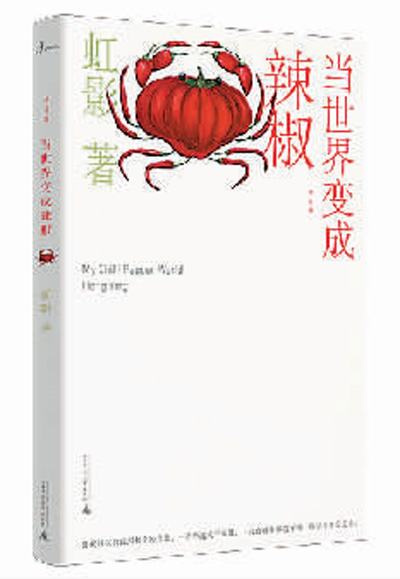作为土生土长的重庆人,作家虹影不仅将故乡作为自己成长的真实家园,还将其作为文学创作的精神原乡,持续不断对重庆展开想象。同时,虹影又是一位具有国际视野的作家,这得益于她多年来对世界的细腻观察和独特的跨文化生活体验。
在全球化语境中书写故乡,在跨文化视角下观察家园,虹影笔下的重庆不是以一个深居中国西南边陲的形象出现,而是以一种开放、包容的姿态一步步走向世界。创作于伦敦的诗集《伦敦,危险的幽会》《白色海岸》《快跑,月食》中有大量以异国文化和视角“回眸”重庆的诗,比如《八月》:“四姐说着家乡方言/种葱,不停地在花园走着/她隔着墙问:家/英文是什么/她的皮肤一到伦敦就痒/伦敦没雨没风/太阳高挂/不断地中断思想/乡村音乐会/被她发现,她轻轻一叫唤/整条街的猫全闪出黑夜/她们的眼睛像我的一样亮。”这是以一个西方人的视角写四姐刚来伦敦时的不适应,处处都有重庆的影子,家乡的方言、气候、乡村音乐会,含蓄地表达出对故乡的思念和对过去岁月的追忆。虹影的诗属于“冷抒情”范畴,因为她将许多真实体验隐藏起来,只留下一些似乎没有关联的意象或细节,使我们难以进入其中,而又试图去破解其中的悬念。作家的“冷抒情”表现在客观的记录和讲述中,让人似乎感受不到思乡愁绪,而是在文化碰撞和理解中“不动声色”地勾勒出淡淡的重庆印象。
小说《罗马》中的“平行叙事”模式,是虹影对重庆形象的另一种呈现。书中以主线、副线并行的方式讲述了发生在两个国度、两座城市、两位女性身上的经历。主线是五天半之内发生于意大利首都罗马、与作家一样从重庆南岸走出的两位年纪相仿的女孩的故事。相比母亲一辈人,她们更加勇敢地表达自我、张扬个性、追求爱情。故事的发生地,看似是拥有罗马斗兽场、万神殿、威尼斯广场、西班牙广场、君士坦丁凯旋门、许愿池和电影大亨费里尼等国际文化符号的罗马,但副线的展开又将视角拉回重庆,讲述的是燕燕的母亲——重庆60后一代女性近乎荒蛮的成长经历。主、副线之间的穿插错落,构建的空间感与时间感,以及大量关于罗马、重庆风物的写实介入让这个原本简单的爱情故事变得丰盈。燕燕总是把费里尼电影里的台词挂在嘴边,但在罗马生活过一段时间后,她还是无法接受远离祖国永远成为一个罗马人。作家强调并重视一个人的文化之根,异国文化在展现其独特魅力的同时,也在巩固异乡人对原乡的认同感。
虹影还通过食物让重庆与世界展开互动。《月光武士》中,“他看到桌上鲜花、餐桌的布置和刺身龙虾、豆腐干青菜、夫妻肺片、棒棒鸡、红油折耳根泡菜。”这是小明在卡菲娅大酒店中餐厅“渝凤凰”为从日本归来的佳惠安排的生日晚宴。无论是餐厅的名称,还是环境的布置、菜的选择,都体现出重庆与世界的对话。在散文集《当世界变成辣椒》中,虹影通过美食表达了对故乡和亲人的感情。她把世间美食分为酸、甜、苦、辣、怪5种味道,家乡的味道大量出现在“酸”和“苦”中。在“酸”的部分,她没有用任何一个词来形容重庆食物的酸,但字里行间却流露着心中的酸涩。《母亲告诉我做稀饭的秘诀》一文,虹影回忆起2006年返乡奔丧的日子,想到母亲为自己做冬苋菜稀饭的旧事,“不肯醒来,生怕醒来就见不着母亲了”。在《童年佳肴》中,虹影回忆起父亲做的清明粑。父亲身患眼疾,不常做这道菜,对于一生都在异乡生活的父亲来说,“清明粑就是家乡”。父亲过世后,虹影开始逃避这个吃食,回避这道菜,因为“清明粑连着父亲,我一日比一日思念他”。有时,虹影悲伤的回忆式语调会转为对现时的感叹,“又要过年了,记得以前一家人在一起,吃饭时,妈妈总是会跟我们说故事。现在,吃饭时,轮到我给孩子说故事了。”由此,她开始与过去和解,更加理解母亲的不易。在“苦”的部分,虹影回忆往事,流露出对家人无法再团圆的苦涩情感。从家乡的食物中,虹影获得的是有关成长和珍惜的经验。
有学者在评论新移民小说家的跨界书写时写道:“新移民作家的文学创作“出发于‘原乡’,思考在‘异乡’,终极于‘世界’。”诚然,虹影书写重庆的小说,几乎都以主要人物从异国返回故土为结局,但在对异质文化的学习和感受中,他们早已不再是受单一本土文化影响的人,他们的存在本身宛如一块色彩斑斓的文化地图,其中代表其性格特征、身体形象和思想特点的板块,无一不是融合了本土特色和异域风情的“虹色”。虹影是这样理解虹色的:“虹七色中没有黑,紫接近黑,可能比黑理性;蓝也接近黑,可能超出黑的感性。”可见,虹影认为自己的写作绝非任意一种单一颜色能简单概括。虹影与苏童等作家相似,他们与西方文学的交流不仅是接受,更是一种创造性的借鉴,展现了中国文学的创造力。这些作家对西方文学的接受中有选择、消化、改造,更有创造性的借鉴。学界评价说,“双向的阐释取代了过去的单向吸收,与西方文学的对话和交流成为中国文学创新的动力。”地方性叙事和全球性叙事的互动绝不是虹影孤芳自赏的镜子,她不仅观照个体生命的成长,也寻求对人类生命意识的关怀,尝试在双边文化互动中展开国家、民族、种族与身份问题的探讨。她用本土眼光观察世界,用世界眼光反观本土文化,将不同文化元素融入作品,在双向阐释中走在跨文化书写的前沿。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