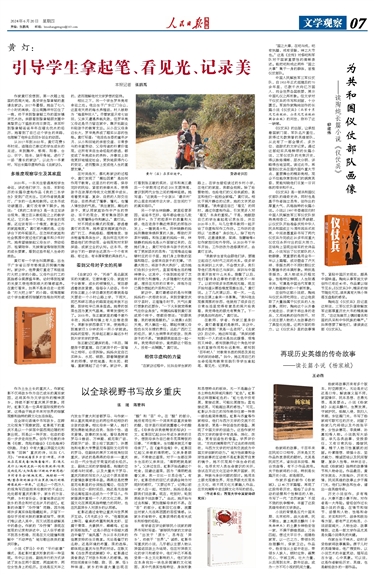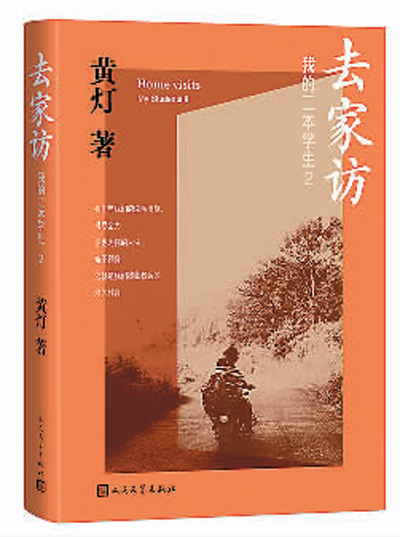作家黄灯没想到,第一次踏上祖国的西南大地,是受学生黎章韬的邀请去家访。2017年暑假,她坐了七八个小时的高铁,在云南腾冲市区住了一晚,终于来到黎章韬工作的固东镇宗艺木坊。亲眼看到黎章韬朋友圈中高黎贡山下盛放的向日葵花,亲耳听到黎章韬爸爸早年在缅北伐木的经历,她看到了自己这个学生的来路,也理解了他毕业后回乡创业的动因。
从2017年到2022年,黄灯花费5年时间,追随自己教过的学生成长的足迹,来到腾冲、郁南、阳春、台山、怀宁、陆丰、饶平等地,进行了一场“漫长的家访”,以此为一手素材,写出长篇非虚构作品《去家访》。
多维度观察学生及其家庭
2020年,一本关注普通高校学生命运,讲述他们学习、生活、求职经历的长篇非虚构作品《我的二本学生》受到广泛关注。它的作者就是黄灯,广东的一名高校教师。这本书成功破圈后,黄灯没有停下脚步。她说:“《我的二本学生》是一本立足讲台视角,建立在从教经验之上的教学札记,它只是一个方面。对学生的观察,还应该有另一个维度,教室之外的家庭维度。”黄灯感兴趣的是,这些讲台下的年轻面孔,在怎样的家庭和社会氛围中度过他们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她希望链接起父母生计、劳动经历、祖辈陪伴、兄妹情谊等细致而微的成长要素,看到这些年轻人生命的底色。
黄灯有一个学生叫莫源盛,出生于广东省云浮市郁南县历洞镇内翰村。家访中,他带黄灯重走了和姐姐打火把上学的小路。父母外出打工的孤独感令莫源盛早熟,幼时得到祖辈的关爱又使他得到极大的情感滋养。在黄灯看来,如果不是亲自走一走那条“打火把上学”的小路,很难理解这个学生敏感而细腻的性格如何形成的,进而理解他对文学梦想的坚持。
相比之下,另一个学生罗早亮有幸运之处。他出生于广东江门台山,这里有天然的海水养殖场,村人被称为“海里种田人”。尽管家里只有七亩田,父亲又遭遇养蚝失败,但罗早亮父母还是尽力留在家中,靠开拓副业补贴孩子的教育支出。从小在父母身边长大,罗早亮养成了踏实从容的性格。黄灯写道:“他活色生香的童年岁月、从小和田地的亲密交道、日常参与的丰富劳动、父母传递的朴素价值观,这所有来自生命经验的渗透,都变成了早亮成长的养料,并事实上助他更好地锚定社会,更快地获得内心的安定,进而整体上变成他人生的重要支撑。”
在对吴浩天、蔡礼彬家访的过程中,黄灯发现了“潮汕因素”是如何作用于教育。这里古朴的村落、保存完好的民俗、紧密的亲缘关系,使得孩子在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中成长,有着更丰富、复杂、自然的人际交往机会,自然养成了懂事、懂礼,也懂人情世故的气质。“我注意到,潮汕的孩子,更认同家庭协作中产生的劳动、实干的观念,更有集体团队意识,也更懂得合作和谦让。”黄灯说。
对不同成长模式的观察,渗透着黄灯的思考,她希望发掘家庭作坊、进厂打工、养蚝修船、摆摊售卖、宰杀牲畜等具体生计,是如何在无形中塑造他们的劳动观、金钱观和对求职深造、成家立业的认知。这本书,使讲台下的一群学生还原为一个个有来路、有过去、有丰厚背景的具体的人。
看到父母对子女的托举
《去家访》中,“托举”是名副其实的关键词,它意味着父母、家庭对子女教育、成长的倾情投入,背后渗透着浓浓爱意,每每令人动容。书中的张正敏上小学后最发愁的事就是每天要走一个小时山路上学,下雨天,泥巴和碎石混合的路面走起来拔不出脚,到学校早已浑身湿透。她带的饭菜也因为夏天气温高,常常发馊吃不了。2005年,张正敏家里的橘子意外丰收,妈妈得知镇上有人出售老房子,果断东拼西凑买下来,使她得以到离家仅5分钟的另一所小学就读。妈妈的坚韧,托举起正敏从偏远乡村到大学求学的梦想。
张正敏记忆最深的是,7年后,隔壁房子要重建,自己家房子的一面墙与之相邻,必须拆除。妈妈决定自己买砖头、水泥、钢筋,跟着隔壁家请来的师傅,学挖地基、和水泥、砌墙,重新建起了这个家。家访中,黄灯看到张正敏的奖状、证书和高三最后一个学期用过的近200支圆珠笔,意识到两代女性之间的精神延续。她写道:“这就是一个女孩从‘最农村’的山里走向城市念大学,在世间打下的真实烙印。”
另一个学生林晓静,家里经营茶园,爸爸手艺好,每年都会做出几批好茶叶。为了把控茶叶的质量和火候,他在老房子靠近烤茶机的那张沙发上,一睡就是9年。而林晓静的妈妈则靠做珠绣积累的人脉,帮助打开茶叶销路。和张正敏的妈妈一样,林晓静的妈妈也是从外面嫁过来的,在她们身上,黄灯对母亲与孩子的关系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在艰难适应偏僻村庄的日子里,她们身上弥散的坚强和隐忍,全部来自孩子的支撑。‘尽最大努力,将孩子养大养好’,成为她们告别少女时代,直面艰难生活的精神律令。这其中,个体到底经受了怎样的努力和磨难,大多随着时光的流逝,湮没在无穷的日常中,淬炼为自己偶尔想起的片段和记忆。”
家访中,黄灯最感动的是与何健妈妈的一次彻夜长谈。来到安徽安庆怀宁县时,正值隆冬时节,天气比黄灯想象的还要冷,“一下火车就觉得寒气往你全身泼”。何健妈妈看到黄灯冻成那个样子,想都没想说:“你跟我睡,我的被窝是暖的。”从凌晨3点到天亮,两人躺在一起,聊起何健父母担负长兄长嫂的责任,远赴广西打工的经历,家人生病带来的变故,抚养孩子的不易。“就像跟我姐姐在一起一样。我觉得好奇妙,竟然跟这个陌生人,没有一点隔膜。”黄灯说。
相信非虚构的力量
“在家访过程中,比如去学生家的路上,在学生曾经读过的乡村小学,在他们的家里,我都会拍照。除了给景物拍,也给他们的父母亲戚拍,甚至和他们一起拍全家福。”黄灯说。相比于照片静态的记录,她的文字灵动而厚重。“我希望在自己‘看见’的同时,通过非虚构作品,引发更多人对‘看见’本身的重视。”于是,她鼓励自己的学生拿起笔记录生活,并在2020年3月,与几位青年教师一起开设了非虚构写作工作坊。工作坊的老师以“志愿者”身份加入,除了校内导师,还邀请袁凌、梁鸿、张慧瑜等6位作家担任校外导师。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工作坊改为选修课形式,由黄灯主讲。
“我教学生首先会跟他们讲,要建立起自己与时代之间的关系。很多学生来深圳上大学,不会想太多,我引导他们思考自己与深圳、深圳与中国改革开放有什么关系。提醒了以后,他们看待身边事物的眼光就不一样了。以前对很多东西熟视无睹,现在开始知道从哪些维度观察生活。”黄灯说。上了几次课以后,有一天,一名学生在课上拿来一本影集。“我叫他去观察周围的东西,他就拍了很多自己日常生活里觉得有意思的照片给我看,我觉得他的眼光有聚焦了。下一步就是如何选材。”黄灯说。
在教师、学者、作家三重身份中,黄灯最看重的是教师。采访中,她多次提到“我是一名老师”。《去家访》后记中,她这样写道,“我深刻感知到一个人的成长是如此缓慢、艰难而又神奇,感知到教师这个角色对学生的直接作用和长远影响,感知到‘百年树人’对教育本质的洞悉及其包孕的深刻命题。”如今,她正用自己的生命经验和教育实践引导学生拿起笔、看见光、记录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