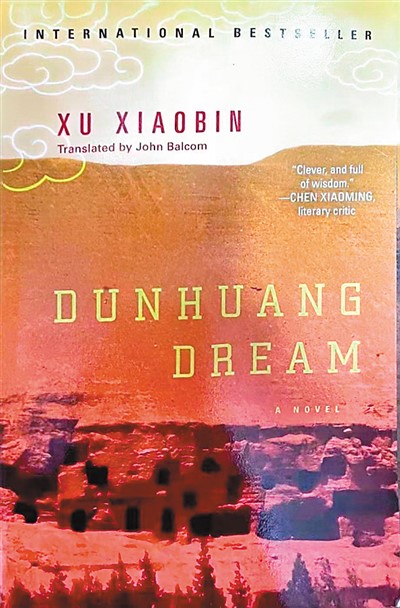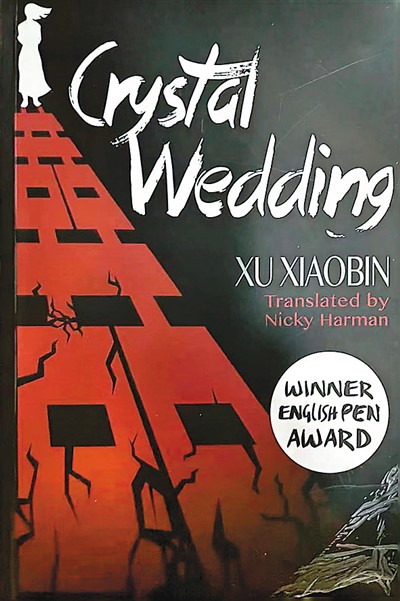《蒲地蓝》是我的一个新短篇,首发于《作家》杂志今年第6期,《小说选刊》第8期选载。小说重点讲述了一位老人无意中发现美味牛肉面的故事,这引发了英国纸托邦翻译团队的兴趣。团队很快进行了翻译,并做成专题网页。翻译梅根和我用双语朗读了小说中吃牛肉面的桥段,出乎意料地受到东西方很多读者的喜爱。他们对中国的牛肉面大感兴趣,都跑出去找这样的牛肉面,国内“80后”和“90后”年轻人纷纷留言:“听得我都流口水了。”通过文学作品传递中国文化,实在是一件自然而美妙的事。
我的作品海外出版发行始于上世纪90年代。2009年算是一个突破,世界著名出版公司西蒙与舒斯特预付了8万美元,签约了《羽蛇》和《敦煌遗梦》两书。之后,《羽蛇》又签了几个语种,如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挪威语等,日本也翻译了《蓝毗尼城》《银盾》等四五个中短篇小说。之后,希腊翻译了我的部分中篇小说,英国的巴来斯蒂亚出版公司通过英国翻译家尼基·哈曼联系上我,出版了我的部分作品。
除了作品走出国门,我自己也经常到海外与外国读者进行面对面交流。1996年,我应杨百翰大学之邀赴美讲学,当时在科罗拉多大学任教的葛浩文(翻译过莫言作品)同时向我发出邀请,我做了题为《中国女性文学的呼喊与细语》的演讲。可能也是借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召开、女性文学热的东风,讲座出乎意料地受欢迎。老葛当时正在翻译王朔的《玩的就是心跳》,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每天都要问我很多问题。我的回答极其耐心,比若干年后人家翻译我的小说还耐心。但同时我心里也在想,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实在太大了!大到难以想象。有时甚至需要翻译重新改写,才能保证母国的读者看得懂。
幸好,有这么一群人,用自己的行动搭建文化交流的桥梁。
最令我动容和不能忘记的,是《羽蛇》的翻译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Gibbon),他的中文名是霍华。
我和他远隔浩瀚的太平洋,从未谋面,但似乎又离得很近。我的《羽蛇》,他似乎十分懂得。特别是懂得主人公的孤独,她的寂寞,她的神性,甚至她潜伏得很深的善良。因为霍华,也是这样一个人。
霍华是加拿大翻译家,曾经在中国生活居住了很长时间,在外语学院教过书,也在《中国日报》工作过,翻译了大量文学作品,对中国文学有着赤诚的热爱。他的祖先,便是大名鼎鼎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他一生中翻译的最后一部小说,便是我的《羽蛇》。
2005年初,霍华已经73岁,此前已宣布不再接新的翻译任务,但读了《羽蛇》(200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之后,决定破例。2005年岁末,我终于与霍华通上电话,在电话中我感觉到他的幽默与坦诚。他说:“我这个老外也觉得你的中文水平很高。”但是他紧接着说到了翻译此书的难度,他说有些地方几乎是不可译的。紧接着发来的邮件中,他说要在翻译前再精读一遍。他极其认真的态度让我肃然起敬。
我们开始邮件往来,他有时叫我大斌,有时叫我小大斌或者大小斌,有时自称白酒翁,有时又自称长臂猿,非常有趣。他说非常喜欢这部书,但也坦率表示,译书速度会非常慢。如果我嫌慢的话可以找别人,不用考虑他的感受。我十分坚定地表示,再慢也没关系,我会等待。就这样,在2007年4月,他终于译完了《羽蛇》的前三章。而西蒙与舒斯特出版公司正是在看了这前三章之后,才决定跟我签约的。
2009年,《羽蛇》英文版全球发行,长着双翅的《羽蛇》飞向了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在国内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文艺报》也在头版登了这个消息,我准备做完手头的事,尽快去跟这位老翻译家见面。
霍华有每天游泳的习惯,他幽默、纯真,但内心孤独,略微自闭。他渐渐老去,靠酒和安眠药打发他发达而已无力表达的智慧。没想到,2011年夏末秋初的一个早上,他迎着东方出现的曙色,只身游向大海,再没有返回人间。而恰恰是那年,我已买好了去加拿大的机票,准备看他。消息传来,真是无比悲伤。幸好此前我专门到云南腾冲为他买了一副翡翠挂件,表达了我一点点心意。俗话说:黄金有价玉无价,我与霍华的友情是无价的!
另一位令我无比感念的翻译家,是英国女翻译家尼基·哈曼。她很早就看中了我的小说,正是由于她的推荐,我才得以在巴来斯蒂亚出版公司出版新书和中短篇小说集。新作《蒲地蓝》的翻译,也是由于她的推荐。
记得2016年伦敦书展,中国出版集团展位最上方是“感知中国”4个白底红字,下面赫然挂着汤显祖和莎士比亚两位先贤的巨幅画像。当地时间下午4时45分是我新版英文书的发布会,我回忆了一下1996年第一次到海外讲女性文学,正好是20年!发布会最后,我引用获诺奖的英国作家威廉·高登的一段话,大意是:“无论你给一个女人什么,你都会得到她更多的回报,你给她一座房子,她给你一个家;你给她一堆食材,她给你一顿美餐;你给她一个微笑,她给你整个的心!”我接着说:“如果是这样,希望你们给我信任,你们会发现我的书给予读者的是十二万分的诚意!”
所有在座的人都留了下来。读者们纷纷购书,有两位印度读者给我的印象很深,他们的打扮像是印度的瑜伽行者,其中一位对我说,喜欢我的声音,像唱歌一样。另一位说,我说话像念诗,尽管不懂汉语,但似乎能听得懂我的意思。这当然令我开心,没人不喜欢赞美。他俩说了又说,万分真诚,以至于耽误了不少签名的时间。他们走后许久,尼基等人才反应过来:“为什么不和他们谈谈印度语的版权呢?”
第四天,赴著名的利兹大学演讲。校方负责人是弗朗西斯和莎朗。弗朗西斯的眼睛是蓝灰色的,很美,而莎朗更是个典型的英国美女,两位都是研究《聊斋志异》的专家。下午3时开讲,下面坐了不少人,且有书店老板现场卖书。在弗朗西斯主持下,演讲从一开始便成为问答式,很新颖,我准备的稿子一点没用上,反而舒服。譬如一开始的问题:“你为什么要写作?”就足够我讲半天的。演讲进行了两个小时,我以一首美国女诗人艾德里安娜·里奇的诗作为结束语,掌声热烈。
书店老板说这是书卖得最好的一次。我暗自庆幸:总算对得起大家的辛苦了。弗朗西斯和莎朗也都认为是讲得最有趣的一次,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像听故事似的,竟然忘了拍照!很多读者喜欢我的那句话:“时间把历史变成了童话。”是呀!我在黑龙江的那些青春岁月,如今在年轻人这里不都变成了有趣的故事吗?
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步伐越来越快,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值得庆幸的事。希望我的小说再次跨越太平洋,拥有更多读者。也希望有更多优秀的作品能充分展示自身的魅力,引读者进入文学殿堂。走进来,走出去,“环球同此凉热”!
(作者系作家、编剧,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