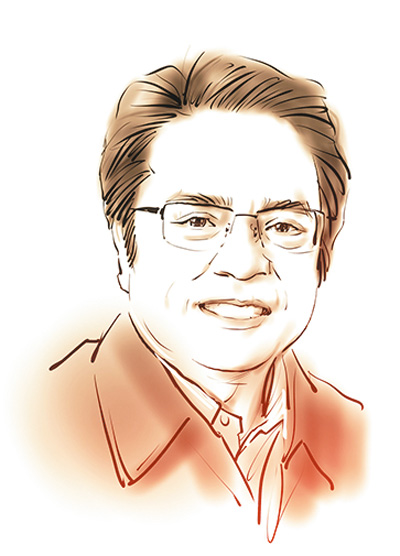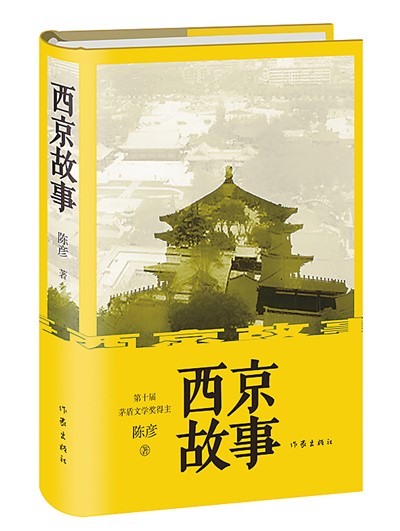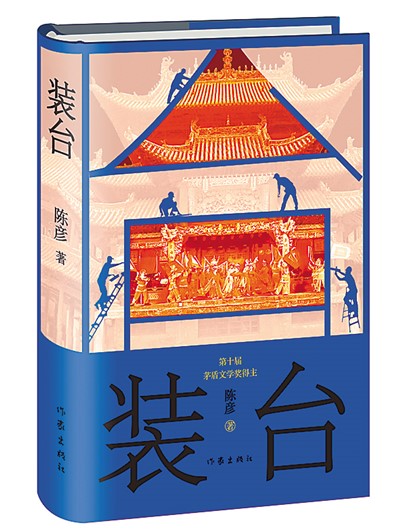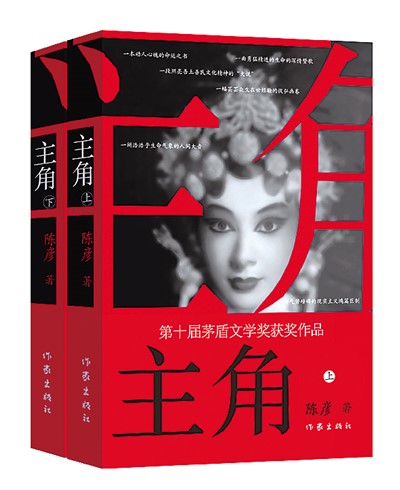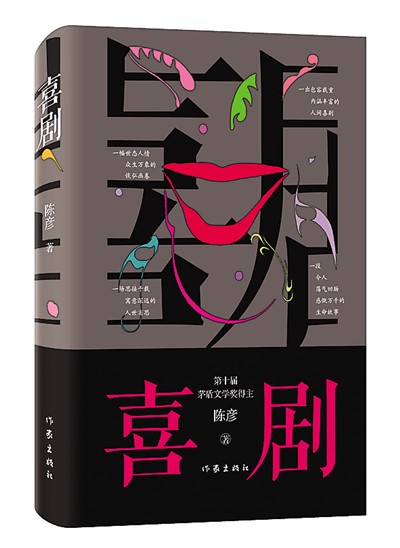长篇新作《星空与半棵树》的初稿,是我在写完《西京故事》后拉拉杂杂写下的,因为很多事情还需要拉开时间距离再看看,就放下了。之后又接连写了被称为“舞台三部曲”的《装台》《主角》《喜剧》。有人希望我沿着这个路子继续写下去,也有人说应该转转舵。我倒没过多考虑与“舞台”的关联度,因为舞台永远是一个平台,无非是提供人表演的场所,至于把人物放到哪里去表演,那要看你对哪个场所更熟悉。一个不熟悉的场域,会让我那些急着施展拳脚的人物缩手缩脚,并吃尽暗亏。尽管如此,在《星空与半棵树》的改写中,我还是在人物的表演舞台上做了延展与调适。
这里拉开的是一个从乡村到小镇,再到县城、省城、京城的宽阔舞台,人物也是三教九流、五行八作、高高低低。而抽丝剥茧,故事的缘起和一个基层干部的几句话有关。我在省城工作时,他来看我,跟我讲了一件小事:两家人因为地畔子上一棵树的产权问题没有解决好,结果事情越卷越大,积怨越来越深。他说只要基层干部有一句话,也许早就解决了,可偏偏没人说,大概都觉得事情太小吧。那时我并没在意,后来调到北京又从这位朋友口中听到几个故事,脑子里就有一些形象挥之不去了,与我所熟悉的这几十年漫长的历史画卷发生了勾连。而这幅画卷恰与我当初写的那部小说初稿暗合,我就把它翻出来重读。一点一滴,从儿时由偏僻乡村对星空的深邃记忆,到山乡的河山、村落、宅院、人物等摧枯拉朽般地改头换面,再到铁路、高速路、高铁对物理空间的陡然拉近,以至城乡边界的显性模糊与隐性加深……我开始了一种混沌的过往盘点与整合记录。
小说的名字“星空与半棵树”有两部分,先说“星空”。我对山村最深刻的记忆就是星空。在稍高一点的地方,就觉得星空像一顶筒状的帽子,戴在我们头上,边沿耷拉到山脚下。我记得上小学时有一位老师是主张我们多看星星月亮的。他说,晚上回去记得数数星星,别老用眼睛盯着脚下有没有分分钱。在课堂上,他又会讲到围绕太阳系旋转的九大行星,因为那时冥王星这颗不够尺寸的矮行星还没被踢出去。我相信老师让大家多看月亮、数星星、别老盯着脚下分分钱的幽默提点,一定会让同学们记忆深刻。后来进县城工作,星星还是那个星星,但至多抬头看看月亮,因为生活逼得你还真需要时时盯着脚下的分分钱了。再进了省城,连看月亮都少了。星空,就逐渐成了一种存在的概念。
就在这时,我突然又被专题片里画面优美、奥妙无穷的太空所吸引,阅读兴趣随之转移,从卡尔萨根的《宇宙》、霍金的《时间简史》、布莱森的《万物简史》等书中,甚至得到了比一些社会学家纵论社会演进规律更深刻的洞见。他们将人类的生死存亡、宗教、哲学、历史、科学、经济、技术、战争、病毒、进化,统摄在天体的照妖镜下,一一辨析着我们认识自己、改造世界的可行性。随着网络阅读的勃兴,我停掉了订阅的其他刊物,却始终保留着《天文爱好者》杂志,甚至还买了一台天文望远镜,不时向天空扫射一二。再回到乡村,我想拜访那位让我们数星星的老师,可人已作古,就想在小说中复活他的形象。因为乡村总有那么一些人,让我们拥有看到深广与辽阔的胸襟和眼神。他手提的老马灯,有时真能照亮一个山村。小说的一个特殊人物——民办教师草泽明就出场了。他有两个学生,其中一个,就是背着一部上大学时购买的漆皮斑驳的二手望远镜,一次次奔波在路上的安北斗。他老想仰望星空,可脚下要处理的却偏偏是半棵树的事。
再说“半棵树”。对星空而言,太阳系在银河的恒星系统中,有数千亿个。而银河系在宇宙的星盘上,也有万亿个以上。连庞大的银河系都只是宇宙的一粒尘埃,何况地球上的半棵树。可在这半棵树的主人温如风看来,它却有关尊严、权利、面子、里子,一个男人甚至一个人的一切。因此,他屡屡踏上讨要公道之路,甚至耽误了志在仰望星空的安北斗。安北斗由无奈、讨厌、气愤、恼恨,到理解、同情、不平、介入,他越来越感到自己是干了一件有价值的事,与天文爱好者梦寐以求的小行星发现之旅殊途同归了。理想信念,看似高蹈出尘、超然绝俗,但最终落到俗世层面上,落到一名基层公务员安北斗身上,就具体到了帮村民温如风争取那半棵树的权利上。
生活与小说,在我看来,有时就是一棵树的状态。根系越庞大,主干越粗壮,旁枝越纷扰,叶茎越繁复,就越耐看、越有意味。小说只是对生活之树做一种精心的爬梳与打理。把你知道的有趣世事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讲出来。其实还是戏剧家李渔“立主脑、剪头绪”的问题。只是小说的“主脑”和“头绪”更加丰沛斑驳,因为有可以“拉平撴展”的长度自由。而自由恰恰又需要一种更大的限制,只“拉平撴展”肯定乱糟无序。一个村子本来就是一棵不小的大树,厘清头绪实在是一件难事,何况我还想由村子连带到镇上,再由镇上带到县上、省城、京城,有时就觉得这故事特别不好讲。但小说最终仍是对一个村镇的山川物理、鸟虫花草、人情风貌、生老病死的铺陈,就有了一个看待整体的落脚点。
我所经历的半世沧桑,在历史长河中,只是一个小单元。但这注定是一个重要单元——历史不可能忽略这十几亿人的生命共进。透过一个村镇去仰观俯察,其中的摸爬滚打、拼死拼活、山崩地坼、反复试错,都具有了一个时代演进史上的独特意义。我们的所有行动都是一个过程,当我们恨着大山的贫瘠、闭塞,认认真真折腾几番后,才逐渐读懂了人与自然生态之间和光同尘的重要。星空与大地,自古以来就是人类认识与把握生存命运的关键点,无论怎样潮起潮涌,最终还会落在敬畏、适洽、呵护与共生上。
归根结底,小说是写人的艺术。人是最复杂、微妙、多变的,我们阅不尽、品不够,其价值、尊严、智慧、力量之综合,体现了人的高贵性。而善良与恶行、淳厚与奸诈、正大与宵小、爱怜与仇恨、守常与贪婪,交汇出人的百态千面,这是作家无法穷尽的世相。由一个或几个人到一群人的命运,再自然地牵连出现实的、时代的、历史的命运,虽然故事各不相同,打开的世界存在巨大差异,但出发点和落脚点,仍在一个个具体可感的人身上。鲁迅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越来越体会到这句话对于文学的意义。当我们感觉不到远方所发生的故事与我们作为人的牵绊时,说明我们正在麻木或堕落,文学也变得无意义。
小说当然也要探索新的艺术技巧和表达方式,需要不断地求新变异,但最重要的仍然是对人,对由人牵连出的广阔时代、现实和历史的打理记录。文学是关于人的一系列行为的系统性安排,人的行为的变数,决定着小说的前进方向,任何技术,都只是人的行为的拐杖。当拐杖影响了人的行为时,哪怕这个拐杖再漂亮,再精美,大概都得忍痛割爱。这部小说里有一个特殊的角色——猫头鹰,他比我说得多,比《喜剧》里那条柯基犬说得也多。它不时对人类的过错絮叨个没完,有时对自己也十分不满。但愿这只猫头鹰不是某种后现代技法的刻意,而是一个创新的艺术形象。希望人类有更多的它或他存在,赐予我们从更广阔的星空来打量现实、省察生活的能力,增强自己更高层次的觉悟。
(作者系中国作协副主席,茅盾文学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