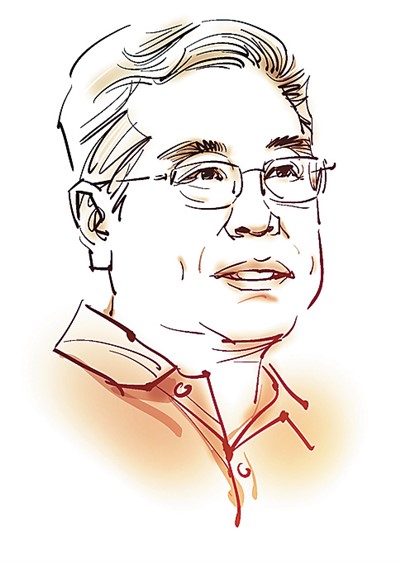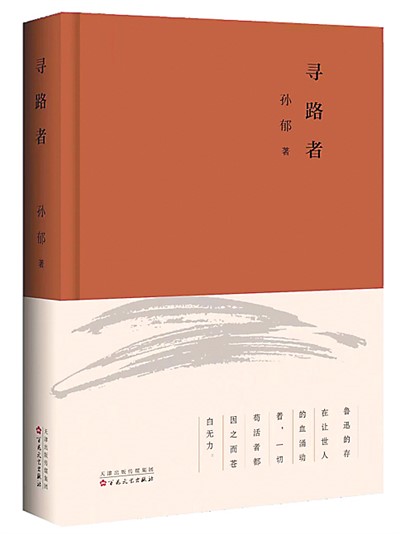青年时代,我徘徊于学问与创作之间。
上世纪80年代,我与许多人一样,如饥似渴恶补知识,读过西洋诗学理论,看过古代文章,可就是不能融入其中。因为一些问题意识无法在那些表达方式里呈现,辞章逻辑被什么限定了,结果是表达生硬,思维缺乏伸展的空间。
后来到鲁迅博物馆工作,进入一个特殊的环境,慢慢地,我的思想与审美观发生了改变。
博物馆注重对旧物的陈列,还原场景,再现历史。这个过程自然有思想的投射,但因为以史料为主体,精神是敞开的,不同遗物折射的故事不同,告诉我们的是有宽度的空间。这给我很大的触动,隐隐意识到,比起教条的表达,从基本资料出发的思考与书写,意义更大。之前,自己在概念游戏中待得过久了。
我所在的办公楼旁有许多藏书,让我颇感兴趣的是《新青年》《小说月报》《语丝》《莽原》《新月》等原刊。最有意思的是看到了作家原稿,从旧的纸张间嗅出前人的气息。接触这些旧刊时,会发现那个时代的精神缠绕着多样形态,知识人在困境中,各自走了自己的路。他们之间冲突有之,对话亦多,重要的思想闪动,照出存在的多种样式。而我们的文学史与现代史对于彼时社会的描述,大抵遗漏了什么。
偶尔也参与文物搜藏、征集,见到了过去没有接触的旧物。比如,曾与林辰先生接触过,看过他的藏书,被许多版本所吸引,才知道做学问最基本的准备是什么。林先生去世后,我与朋友清理他捐赠的书目,翻看一些未见过的刊物,对于过去的文化行迹自然多了心得。他的文章好,与懂得历史文献有关,古文功底非我们这代人所能企及。曹聚仁先生称赞他的厚重,大概就是指文献的功底。我从他的文字中才知道,学问的文学化表达,要有多方面修养。做到此点,要下许多气力。
研究室有位江小蕙老师,是鲁迅朋友江绍原先生的女儿,她退休后给博物馆捐赠了大量信札。看到鲁迅、蔡元培、胡适、刘半农、钱玄同等人的墨宝,似乎感受到那些人互往时的片影,我与几个同事从中理出了些有趣的学术线索。最大的启发是,彼时的学人,样子不一,率性之中,有着传统文人的一面。这些人新旧交错,学问与趣味也有脱俗之美。他们何以丰富了现代学术,其间的蛛丝马迹,亦可视为一种注解。
真正触动我的是,在博物馆接触的一批文章家。那时候我参与《鲁迅研究动态》编辑工作,负责编辑业务的老师大概受民国杂志的影响,趣味驳杂,不仅有论文,也设随笔、考据和译文板块,能看到老一代作家楼适夷、黄源、梅志的短文,许多都值得反复咀嚼,还有一些现代文学研究专家的文章,像唐弢的学术随笔、林辰的考据短札、姜德明的书话,都很有意思。在我看来,他们的书写,延续了鲁迅那个时代的遗风,在领悟社会与解析思想时,保持了汉语的温度。
看这些人的文章,震动之余,也反问过自己,为什么我们不会那样表达?后来又认识了汪曾祺、张中行等前辈,才慢慢知道汉语的多种路径。
从材料出发,思考现代文学的来龙去脉,是博物馆系统和非学院派作家的一种本领,五四遗风有魅力的地方,大概也包括这些。
许多年间,五四那代人一直吸引着我,研究新文化社团的思想,用去了我许多时光。不过,因为基础较薄,阅历有限,对于那代人的理解有着诸多障碍,最初几年一直不敢下笔,思想与材料尚无法形成一种对应关系。
这本《寻路者》的主要文章,是友人催促的结果。有一次遇见时任《十月》主编的王占军先生,他请我开一个专栏,谈谈五四那代人。我知道这是对于我的信任,便随口答应了。后来才知道,要处理的难点比想象要多,于是一写就是两年,大致留下了当年思考的旧迹。那时候白天忙于行政杂事,晚上伏案写作,却并不觉得疲劳。以感性的方式面对史料,能够发现诗意的存在。五四那代人,有真纯之气,驻足那些旧迹时,不仅有思想的洗礼,也受到了美的灵光的冲击。
那代人的不同道路,对于后来人的影响至今未消。我发现,将这些前辈看成“寻路者”也许更符合实际,因为他们都是不同路径的开辟者。鲁迅的抵抗之影、陈独秀的孤傲之气、老舍的京味之音,还有巴金的超俗之韵,撕裂了旧的词语之衣,古老的汉语涌出了新浪。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春水的涌动,所至之处,绿色泛波,花香飘动。面对这些遗产,有时无法抑制自己的激动。
写新旧之际的文化人与社会思潮,有不同的办法,我希望能够将彼时的学术趣味进行文学化的表达。张中行先生在《负暄琐话》中就是这样处理记忆的,不过他是对亲历岁月的反观,有温度与爱憎。我们追踪那段历史,总还有隔膜的地方,倘不是深潜在资料里,贴近文本来描述旧影,总还是隔靴搔痒。避免这种局限,就不得不放弃以往的写作方式,调整叙述语态。而寻找一种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也正是确立自己思维方式的一种跋涉。我们说写作不都能看作是一种游戏,也有这方面的因素。
比如写未名社的那一篇,事先看了一些材料。鲁迅为韦素园写的碑文,也在博物馆的资料室里。看那些同人们办的杂志,刊发的多是俄国文学的译文,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安德莱夫,文字都有些苦涩,思想性的部分透出译者的追求。比如李霁野所译《文学与革命》,是鲁迅催促而成的,几位青年不幸因之入狱。那时的文学活动,并非都是闲适的产物,他们还是怀揣着梦想的。我们的老馆长李何林先生是未名社后期人员,他偶尔和人谈起青年时代,一方面是革命,一方面是文学,生命呈现着燃烧之状。李先生一生追随鲁迅思想,与时风一直有着距离。馆里的老同志受到的影响很大,以致单位的风气仿佛也散出未名社的一些味道。
五四之后新知识人,有许多是精神的冒险者和引领者。我在描述巴金的时候,重点谈及他精神品位中圣洁的形影,从巴金纪念馆得到的图片与手稿复印品中,可体味到他纯然的一面。他在鲁迅启示下的寻梦之旅,对于世俗化的读书人无疑是一种拷问,描述这样的作家,也是一次自我教育。虽然巴金的矛盾与缺陷影响了他的深度,但那种不断与灰暗决裂的跋涉,也正是世俗之人最缺少的勇气。
人的一生,走路的方式无非两种:一是沿着前人铺成的路而行,不需要思考,传统的士大夫是这样;一是在没有路的地方走路,或遇到丛葬,或碰见沟壑,这需要探索精神和毅力,五四那代知识人,有许多是这样的状态。现在回望这些寻路者,描述他们,许多时光深处的遗存,只变成了几许片影。满足于片影的捕捉是不够的,微茫之间,亦有非同寻常之意。细细体察,那些片影下是无数坚毅的足迹,它们述所由来,道其所往,是一条迷人的精神之图。坦率说,写透前辈的形影,并不容易,要悟懂他们,也许需要用一辈子的时间。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