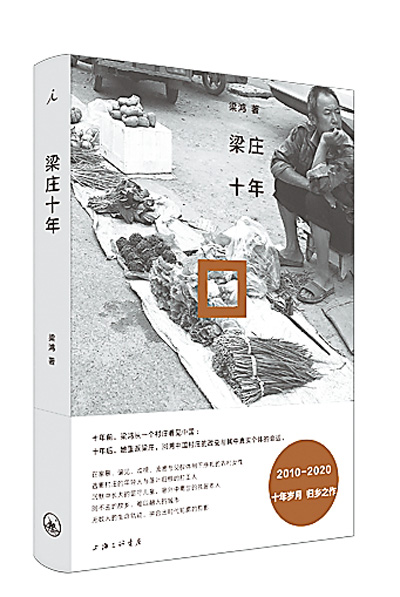《梁庄十年》是作家梁鸿继《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后的第三部梁庄故事。“在梁庄”“出梁庄”是以梁庄为原点的空间转移,“梁庄十年”则打开时间之维,重在记录“变动中的感觉”。作者以梁庄与梁庄人十年来的现实遭际与命运浮沉,勾勒出中国当代村庄与时代共振的轨迹。
《中国在梁庄》与《出梁庄记》均彰显出梁鸿强烈的问题意识与介入现实的有力姿态,她以“参观者”“访问者”的身份出入梁庄,运用学者的理解与视野观察梁庄人的生存境遇,并借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物故事叩问反思关乎社会、国家、历史命运的深层结构性问题,其中不乏充满人文关怀的自省意识。一般而言,先在的主题预设既是理解描写对象的线索,也有可能限制读者的阐释空间。因此,梁鸿在后续的《出梁庄记》中避免预设判断,而是“从人物的行动、语言和故事中寻找他的结构和逻辑”。她不是轻率地站在道德与公理的制高点上发出谴责,而是试图努力看见、理解梁庄人“心里面的深流”,揭示现实的复杂性。
与《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不同,新作《梁庄十年》在创作上的变化,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呈现出结构与情感的“内化”。具体表现为在书写对象上由事件化转向日常化,作家的写作意识从外部旁观化为内在沉浸。全书共5个章节,分别从房屋、女性、土地、回乡和生死角度观照梁庄人。梁鸿延续了将叙述者“我”的所见所闻与梁庄人的自述记录相结合的形式,但“我”时常退场、隐于幕后,取而代之的是基于合理想象的文学性描写,赋予文本更强的故事性与可读性——这从“福伯有福气”“五奶奶上街去理发”等平实而有童话意味的小节标题中便可窥见一二。
与前作相比,《梁庄十年》显得更“轻”,“轻”既指字数所标识的篇幅体量,也与基调的“沉重”相对。梁鸿适当收敛理性启蒙式的批判锋芒,转而关注梁庄个体的生存境遇与生命体验,呈现出对乡村伦理人情的回归与认同。这并非简单的倒退,而是建立在深刻反思基础上的回撤——回撤到“人”的存在本身。最具代表性的是第二章“芝麻粒儿大的命”,梁鸿第一次将凝视的目光转向梁庄长期缺乏关注的女性群体上。她将象征一个人主体身份的名字还给失落在时间深处的梁庄女孩们,并设法与分别近30年的燕子、春静、小玉重聚,倾听她们真实的往事与心路历程,“让她们重新在梁庄的土地上生活,尽情欢笑,尽情玩耍”。
末章“生死之谜”是有意味的收束,关怀“人的消失”这一终极问题。“门开着开着就不开了”,既指涉破败不堪却“毫无意义地上着锁”的老屋之门,也隐喻不经意间戛然而止的岁月与生死之门。梁鸿写下逝者的名字,逐一交代他们的生平:清立、梁清发、梁清朝、梁万生、梁兴隆……直到最后,梁鸿的父亲,梁光正。作者以文字为媒介,以纸张为载体,为远去的乡人们在纸上立起一座座小小的碑。“这时,纪念才真正开始。遗忘也真正开始。”
最后一节“少年阳阳”写“我”和村人坐在五奶奶的院子门口聊天,秋风卷起金黄的落叶,“我”视野中的公路、蓝天、麦秸垛乃至文哥家的破三轮车,在金色的光与叶笼罩下如梦似幻——“我”第一次意识到梁庄竟如此美丽。诚如梁鸿自言:“我和梁庄的关系变成了一个人和自己家庭的关系。”这一“觉”,用了十年光阴。十年间,梁庄的人来来去去,离乡或返归、逝世或成长、失落或重聚,每个个体的经历都是梁鸿“长河式的记录”中真实的浪花,梁鸿与这些浪花的遭逢,也构成了她审视、清理自我生命的契机。
《梁庄十年》以“我”和“少年阳阳”分别“往前走”的场景作结,留下近于“光明的尾巴”,其中隐含着梁鸿的生命哲学:“生活如此古老又新鲜,永恒存在,又永恒流逝。但并不悲伤,甚至有莫名的希望所在。”梁庄系列未完待续,但已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梁庄传”,熔铸了梁鸿对梁庄这片故土的眷恋、深情、反思与悲悯。下一部梁庄书写何时问世?我们和梁鸿一样,“几乎等不及时间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