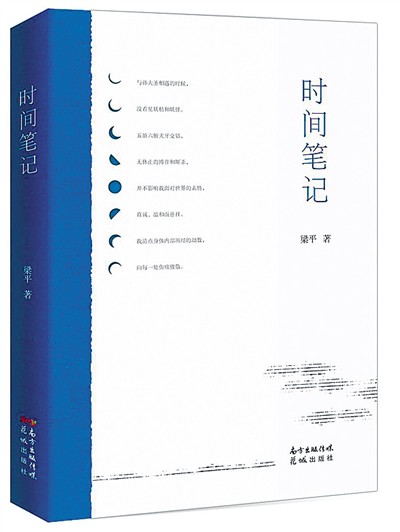梁平将他的最新诗集命名为《时间笔记》,这最为直接而显豁地印证了诗歌的记录和记忆功能。他在诗集中所呈现的“诗歌记忆”不单是关于日常经验的,而是综合性地融合了生存经验、现实经验、地方经验以及个人化历史想象力参与之后的文化经验。
这本诗集中有一首诗名为《时间上的米沃什》,“时间在他的笔记里/惶恐、困惑、悲伤和虚无/每一个时刻都有斧凿的痕迹。”具体到梁平近期的写作,我们同样可以把这些“时间之诗”称之为“时间上的梁平”。当诗人自觉地把时间意识放置在诗歌的首要位置,这就说明他的“中年经验”和人生阅历已经足够厚实了,眼界也更为开阔,包容异质的消化能力和精神意志力也更强,“耳顺能够接纳各种声音/从低音炮到海豚音/从阳春白雪到下里巴人/甚至花腔,民谣,摇滚,嘻哈/皆可入心入耳。”(《耳顺》)与此同时,这也是喧嚣红尘和现实泥淖之中的自我辨认、检视和清点、省思的时刻,正视时间、世界与人相遇的得失,正视一个人的欲念和整个世相的浮华万端,这是卸下面具直面本心和原生的一刻,“我是在熬过许多暗夜之后/读懂了时间。星星、睡莲、夜来香/它们还在幻觉里争风吃醋。”(《欲望》)
当时间一次次来到心头和纸上,这就是对记忆予以找回和打捞的过程,诗人必须正视幽暗的时间古井并倾听它的回声,辨析种种斑驳的倒影和幻象。因为时间意识的强化,梁平的诗歌带有生命的呼吸、时间的光影和斑驳的世相。
这是一个人和时间的对视与剖视,这是“一个我”与“另一个我”的时时校正、盘诘或辩难。梁平的诗歌真实不虚地印证了“自我和自我争辩产生的是诗歌”,比如《我是我自己的反方向》:“镜子面前我看不见自己/别人的眼睛里我看不见自己/我是我自己的错觉。”
自我辨认、自我确认、自我怀疑和自我辩难需要的就是诗人的智性能力和反思能力,而且还要由己及人、由己及物,从而打通个人时间与生存时间以及“世界时间”的精神关联和存在奥义。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说过“我们都是时间”,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则强调“诗歌是对人类记忆的表达”,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则强调“记忆渴望返回中心”,而这些“时间”和“记忆”既指向了个体生命和存在境遇又关乎整体视域下现实、时代以及历史。
由梁平的这些时间意识明确的诗歌,我想到的是奥克塔维奥·帕斯的一句诗:“所有的瞬间都是同一个瞬间”。诗人将身边之物、日常现场、外出行旅等可见之物都放置在一个又一个的瞬间,但是诗人已经自觉意识到这些瞬间不能成为一个个即时性的时感的碎片,这些瞬间必须关联为一个整体。这需要诗人具备把即时性经验、个人经验和日常经验递进、转化、过滤、变形、提升为修辞化的生存经验和普世性人类经验的能力。
“诗歌经验”既涵括了个人经验和现实经验,更容纳了语言经验、修辞经验以及超验和想象力的经验。梁平的这些“时间笔记”正好是诗歌经验和日常经验形成了相互打开、彼此沟通的过程。比如《半夜敲门》这首诗,“半夜敲门”显然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物理时间和日常举动,这一特殊节点和声响背后恰恰代表了日常中的反常时刻,因而具有了不安、紧张、猜测等等心理体验。“半夜敲门”不再指向日常个体,而是指向了精神事实。质言之,这不是语言对现实的自然反射,而是诗歌本体层面的“词与物”的关联,语言史也正是生命史和时间史,“分类和言语都起源于表象在自身内部打开的同一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是奉献给时间、记忆、反思、连续性的。”(福柯:《词与物》)
诗歌必须具有廓清当下的精神能见度。诗歌不只是要记忆,还要指认,还要重新发现。比如《城市的深睡眠》一诗,十字路口的那只“蚂蚁”,已经成为精神的喻指,局部、可见之物的背后是整体、不可见之物以及世界的表情,这考察的是一个诗人突破盲点的眼力——精神能见度层面的眼力。
也就是说,一个诗人只是描述“生活本来的样子”还远远不够,诗人最终必须通过语言、修辞和精神能力、求真意志来再造一个“拟像现实”“诗性空间”和“精神修习室”。这一“诗性空间”和“精神修习室”显然与日常空间和日常现实存在较大差异,诗人的主体性、精神能力甚至个人化的现实想象力在其中起到了催化剂一般的重要作用。《盲》中的那只“白鹭”在诗人这里已经成为精神主体的客观对应物,它来自于现实但又区别于现实,是心象的投影,是人心的折射,这一意象只属于诗人自己而不能为其他诗人所复制和仿写。
每个诗人观察世界的方式都不同,因为他们持有各自的取景框。梁平的一部分诗是在四川的日常空间展开的,另一部分诗歌则是在行旅路上的所见、所感、所想。日本学者柄谷行人在考察日本现代文学起源的时候就发现认知景物的装置已经被颠倒了,“只有在对周围外部的东西没有关心的‘内在的人’那里,风景才能得以发现。风景乃是被无视‘外部’的人发现的。”(《风景之发现》)一个诗人因为现实观、世界观的不同而使得取景框与他人有别,强烈地和精神自我发生着深度呼应。在梁平这里,从来都不存在外在的、观光化的“风景”和浮光掠影的怀古幽思,而是精神和空间交互之后产生的语言视觉以及“内在化景观”,其重心在于主体的感受方式和观照的方式、角度、位置。
在梁平的“时间之诗”中,我看到了一个越来越真实、越来越理性、越来越清醒的辩难时刻,这是个人的时间也是存在的时间和精神的时间,它指向了每一个人。这是个人的精神传记,也是浮世绘的档案。正如梁平自己所说:“时间为他而凝固。”(《时间的米沃什》)
(作者系《诗刊》社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