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国三月,滴青流翠。
牵着春风的翩翩裙裾,我走进了一个小山村。
小村名曰坦洋,位于福建省福安市西南20公里的白云山脉深处。群山皱皱褶褶、缠缠绕绕,犹如一只巨大的摇篮;小村安安静静、简简单单,又宛若一个酣睡的婴儿。村外,阳光铺满的山坡上,遍布青青茶园,点缀着星星点点的采茶人,默默地移动。整个画面,仿佛一部彩色的无声电影。只有那漫天浓浓淡淡的清香,像一群群五彩斑斓的蝴蝶,在空气中飘飘忽忽、聚聚散散,撩拨着人类的鼻息和睫毛。
村头的树荫下,到处堆满茶青,油油的、嫩嫩的、颤颤的,好似刚刚从海底网上来的鲜虾活鱼。
这清新明丽的小茶村,多么动人。
但是,这个小村不寻常。南国茶村千千万,而她,是特别的那一个。
邀我踏访的文友施元辉,就出生在这里。他告诉我,清朝咸丰元年(1851年),本村茶人研制出一种特殊风味的红茶,取名坦洋工夫。此茶依靠沿海和侨乡优势,逐渐风行海外,远销荷兰、法国、日本、东南亚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更为英国皇室贵族所青睐。由此,小村成为周围七八个县的茶叶交易中心。当时,坦洋村拥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制茶工场,三层,数千平方米,名曰横楼。而全村更是膨胀成一座繁华集镇,住户达6000多人,还有戏楼、商铺、客栈、学校、教堂、医院、警所,等等。为了防备土匪,村中富户还建造了19座炮楼。1935年,国民政府在这里专门设置福建省立茶业改良场,对中国传统茶叶进行科学分析和改进。只是20世纪50年代之后,中西关系变化,红茶出口转冷,小村骤然衰落。改革开放后,中西红茶贸易恢复,国内红茶市场升温。目前,小村拥有茶山4000亩,茶场茶行数十家。
白云山上生仙茶,山间溪水清见沙。三月底,采春茶,清明前,品最佳。茶树经历霜冻,冬眠初醒,蕴含丰富,茶心鼓鼓的、满满的,像孕妇,又似新麦,若鲜果,蓄满着日月山河的精华和密码。
浑浑圆圆的山丘,高高低低的红壤,安安静静的茶园。满山采茶人,个个巧手翻飞。这鲜嫩的新芽,这天地的精英,蹦蹦跳跳、欢欢喜喜地来到人间,吟唱着、喘息着,直喘得天地芳香、如雾似纱、氤氤氲氲。
春茶过后,常采常新。仅仅几天时间,一粒粒、一层层、一丛丛新芽,又迸发出来,密密麻麻、毛毛茸茸,若狝猴的耳朵,如麻雀的舌头,像婴儿的嫩手,似少女的睫毛。
茶青萎凋之后,要经过揉捻、发酵和烘焙等几道工序。大约5斤茶青,出产1斤粗茶。但这只是毛坯啊,良莠不齐、鱼龙混杂,需要精制。
什么是精制呢。就是分别用四目、五目、六目、七目、八目、九目的细筛,进行分级筛选。1斤粗茶选出0.75斤六目规格的精茶,100斤精茶再析出5斤极品茶。
但是,这只是常规工序啊。分寸、轻重、火候不同,味道各异。就像同样的食材,厨师不同,菜品不同。有时候,同一食材,同一厨师,不同批次,也是味道有别呢。
所以,专业制茶人,在整个操作期间,务必要保持心平气和、恬淡虚静。此所谓茶禅一体吧。
我在小村里静静地走着,仿佛走进了历史深处。当年的横楼依然健在,这青石与青砖组合的中西合璧的三层楼房,委实是工业时代之前很大的手工业茶作坊了。西方人品味着中国红茶,中国人借鉴了西方建筑,东西文化在天然地追求着、吸引着、磨合着、融合着。
施先生告诉我,茶是有生命的,就像一曲灵动的音乐,去和鸣你的心弦,让你体味生命的美妙。
是的,地球上所有的动物和植物,都是一个共同的祖先,那就是从最简单的单细胞生物进化而来。凡生命,皆相通。这人类培育和钟情几千年的精灵——茶叶,伴着温润的清泉,进入口舌,流入喉咙,沁入肠胃,融入血液,沿着你的每一根神经,浸润末梢,融通一座座郁结的城堡,水到渠成。
于是,你浑身的每一个细胞,都在摇头晃脑地唱歌,都在得意忘形地舞蹈。一杯香茶,甘醇宜人,真趣真义,润身润心。细察“茶”字,果真如此呢。上是草,下为木,中间乃人。人在草木中,茶道最永恒!
(作者系第三、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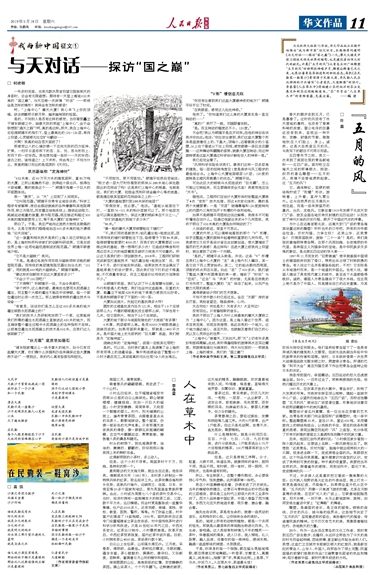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