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奇怪。
我自己知道,年轻时候的我,不是十分的“好玩”。
除了偶然有机会在酒桌上表现一点装疯卖傻,平时更多时候,就是个一本正经写作的人,也说不出好玩的话,也做不出好玩的事,内心也不觉得“好玩”有多好玩。
就这样,一个不好玩的我,写着写着,年纪就渐渐地大了,又渐渐地老了,十分出乎意料,伴随着年岁一起来的,不是成熟,不是矜持,不是拿捏,竟然是“好玩”。
这个“好玩”更多是说的内心世界,不一定是真正的实际行动。因为从实际行动来说,我仍然是喜静不喜动,不旅游,不逛街,我仍然一个人待着多长日子也不会觉得郁闷。
但是一个人的内心的力量,难道不也是一种很厉害的力量么?
一个天天在外面游山玩水的人,也不一定就是一个“好玩”的人呀。一个哑巴了或者瘫痪了的人,也许会是一个“好玩”的人呢。当然也可能正相反。那是涉及灵魂而不是涉及肉体的事。
我如果一直一个人呆坐,岂不等于是哑巴和瘫子吗?但是每天每天,我的内心都会翻跟斗,十分好玩。
我觉得自己简直有点老不正经,就像《灭籍记》的那个郑见桃,我一直感觉那就是我自己,我在写她种种“好玩”的时候,好几次笑得哈哈哈哈,眼泪都掉下来了,擦也擦不干。
也许是这种贪“玩”的心态,直接影响了我的写作。
先自我反省一下,这种心态是怎么演变、怎么发展来的呢?
这就要说到世界、说到生活、说到我们所处的时代了。我曾经在2016年的某段时间,几乎在同一天里,接受到三条内容,一是诺贝尔文学奖给了美国摇滚歌手鲍勃迪伦(接下来假新闻不断、真假新闻混淆);第二是希拉里和特朗普的同台演讲被恶搞成情歌对唱,还是粤语版的呵呵(难解百般愁,相知爱意浓);三是我们记忆中印象非常深的地道战中鬼子进村了那段音乐,原来是俄罗斯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第七交响乐中的片段(至今不知真假)。
世界变得很有趣,变得奇怪,无厘头,好玩,但绝对不是简单的傻傻笑那种好玩,是暗含着错综复杂内容的不可捉摸的有趣,是有着特殊分量的奇怪,是让人感叹的沉重的好玩。
在这样一个时代写作,写的又是时代的故事,我们已经无法用从前的一本正经的老眼光、老观念去看待、去提升,我觉得自己已经“回不去”,回不到一本正经的状态,已经无法不追求“好玩”了。
所以,这样看起来,也许是我的写作让一个不好玩的人,在老了的时候,变得“好玩”了。这和刚才我所说的“这种贪‘玩’的心态,直接影响了我的写作”这句话,恰好关系倒置。
关系的倒置,真假的难辨,观念的对峙,一地的鸡毛,满脑子的混乱,组合成了时代的风貌,世界在变化,文学怎么样?至少我想,我们的写作可以有、也应该有更多的路径。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我的小说,就是写好玩的故事,然后在“好玩”的背后,埋伏很多东西,或者说,在“好玩”的背后,天生就埋伏着很多东西。至于这些东西,读者能不能读出来,那就要看我们的缘分了。
卡尔维诺有一个短篇小说,写一家人逛超市,所有人都尽情地欢快地挑选自己喜欢的东西和家里需要的物品,堆放了满满一推车,当然,最后他们必然是要把这些东西一一地放回原处的,因为他们身上根本就没有钱。但是小说的结尾出现了意外,超市的管理出了事故,使得他们意外地带走了货物。
这个意外是轻逸的,好玩的,但却是更沉重、更痛的。
再说说《灭籍记》中的“好玩”的人物:郑见桃。一个必须冒名顶替才能生存下去的老太太。年轻的时候为了追求真理和爱情,丢失了身份,一辈子都无法做回自己。在从前,做回自己就要被治罪,到后来,做回自己就会被饿死。这个人的遭遇忒悲惨了,可是因为她在人生的最后一程,冒名了一个有钱的老太太,所以她活得姿意自在,爱吃吃,爱喝喝,想骗人就骗人,爱捉弄人就捉弄人,谁也不敢惹她,一个好玩的老不正经的老太,自以为足智多谋,无往不胜,可她的人生到底是赢家还是输家呢?她已经有多长时间没有听到过郑见桃这个名字了?所以,这个活得姿意自在自以为好玩的老太太,真的是郑见桃吗?
好玩的故事承载历史的命运,“好玩”的背后,是对现实的剖析和生存的思考。这是我想做的事情。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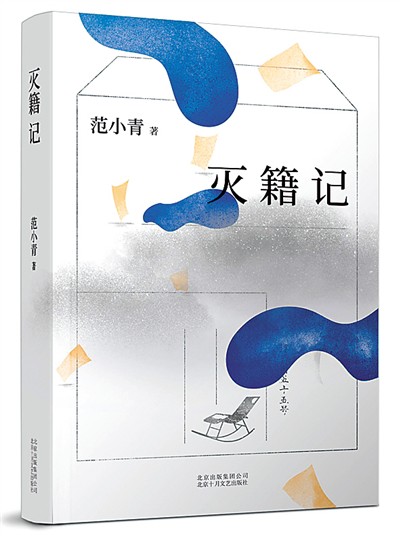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