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快过年了。小妮站在东厢的廊下,仰头望着夜空,很久以前,有人曾在那里升起一朵绚烂的烟花。
鼻端一缕甜香,是腊梅又开了。
那时候,小妮和父母住在四合院的西厢和北厢,东厢和南厢住着一位阿婆。每年一进腊月,阿婆便去火车站排队买票,她的儿子、儿媳都在省城工作,她要去省城和他们一起过年。阿婆说:“他们就放7天假,时间短,我孙子还要补课。我老婆子时间多,不怕路上折腾。”就这样,阿婆总要过了正月十五才回来。每年放鞭炮、吃饺子时,阿婆的房子都空着,腾出一个干干净净、四四方方的小院,方便小妮的爸爸妈妈邀请亲戚来家。
小妮初二那年腊月,阿婆破天荒地没有去火车站买票,而是兴冲冲地在家打扫、做吃食,小院一连好几天弥漫着各种食物诱人的香味。原来是阿婆的孙子今年考上了北大,他们一家要回来过年了。
大年三十傍晚,小妮随爸妈去城外给先人送过亮,回来看见阿婆的门关着,里面电视开着,有客人,言笑晏晏的。
第二天是年初一,一大早,小妮就被鞭炮声吵醒,觉得外面特别亮,隔着木格窗子,看见外面下雪了!对面东厢的屋顶上白白的一片,院子里的花木也一夜白了头。小妮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穿好衣服来到院子里。
她看到了什么?一树被雪覆盖的腊梅花下面,一个少年正用手指轻轻拨去积雪,深嗅那雪中腊梅的清香。他穿着蓝色的休闲装,系着灰色的羊毛围巾。感觉到有人看他,便朝小妮扭过头来。小妮也忙低头看自己:粉色短款羽绒服,牛仔裤,粉色毛毛拖鞋——真土气啊,她觉得脸发起烧来。少年朝小妮笑了笑,干净透明。
那一天,小妮任爸妈怎么唤都不肯回屋,她收集积雪做了很多只雪鸭子,每一只都比茶杯大不了太多,姿态各异,栩栩如生,从雪地里排到院中的石桌上,从屋檐下排到白色的冬青树上,好像小鸭子们列队在走。
终于,阿婆家贴着“福”字的棉门帘一挑,嗅腊梅的少年——阿婆的孙子,小妮叫他小哥哥,出来了,看见雪地里的小鸭子,眼睛一亮,朝小妮笑了起来,说:“心思好巧的小妹妹。”小妮藏起冻得通红的双手,也笑了。虽然是再普通不过的女孩子,做手工却是小妮的强项。
年初二开始走亲戚,这一走就要一直走到初七爸妈上班为止。
这一年,走亲戚格外令人厌烦,连小妮喜欢的糍粑、糯米蒸饭、粉蒸肉都变得油腻而齁甜。晚上回到家,对面阿婆家关门闭户,只有电视里重播春晚的声音传出来。好不容易到了初五,轮到小妮父母邀请亲戚们来自己家了。小妮提前几天就在心里雀跃,然而初五一大早,她眼看着阿婆一家人锁上门出去了,小哥哥还回头对她笑了笑。小妮憋得眼角疼,才没让眼泪流下来。
又是乏味而耗神的一天。到了晚上,小妮帮妈妈打扫请客后一桌的狼藉,隔窗听见阿婆一家也走亲戚回来了。过了一会儿,院子里响起了爆竹声。鞭炮一响,在小妮耳朵里就有了召唤的意味。她飞快地把洗净的盘子放进碗柜,冲进了院子。
天上新月如钩。不甚亮的院子里,小哥哥正用一根燃着的线香,探着身子去点地上竖着的一根大爆竹。爆竹的引信被点燃了,“嘭”一声升起,在高空绽开一束七彩的礼花,“噼噼啪啪”地向四周绽放,越变越繁复,越变越绚丽,流光溢彩,光芒四射。随后,于极盛处渐渐黯淡、消逝,最后只剩下一束青烟,在漆黑的夜空保持着一朵烟花的形状,久久不肯散去。
小妮一直仰头看着,直到小哥哥碰碰她:“你来放。”小哥哥手中一支细细的焰火棒,大小像妈妈织毛衣的竹针的一半,上面包裹着一层火硝。小妮退后一步,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不,不,我不敢。”小哥哥微笑:“我知道你不敢,这个不怕的。”
看见小哥哥眼里的鼓励和期待,小妮一下子来了勇气,接过那根小棒,伸长了胳膊远远地持在手中。小哥哥用线香点燃了它,绽开一朵金黄的、毛茸茸的烟花,安安静静,小巧玲珑。小妮不再害怕,把这朵小小的烟花举到眼前,好奇地看它,像看着一簇小小的希望,喜悦充塞了内心。那个夜晚,那种焰火棒,小哥哥给她点燃了一支又一支。小妮第一次知道,烟花也可以如此温柔。
第二天是初六,小妮继续被父母拖着走亲戚,傍晚回来时,只有阿婆在院子里打扫昨夜的爆竹残迹。她抬头和小妮一家打招呼,不用问也知道,小哥哥和他的父母已经回省城了。
又是一年春节。阿婆照例收拾好一切,去省城和儿子、孙子一起过年。和往常不同的是,今年她把房子卖给了小妮家——她年纪大了,以后就在省城和儿子一起生活了。欣喜的小妮父母把春联和“福”字贴遍了四合院的每一扇门窗,包括原来阿婆住的东厢和南厢。
他们终于拥有了一个完整的四合院,没人注意到小妮的忧伤。
那年烟火璀璨的一瞬,在她心里亮了好多年。
几年后,小妮早已改掉了爱吃甜食的习惯,比以前更加挺拔,轮廓也更分明了。因为小哥哥进的是北京大学,她的成绩也从班级中游升到了全县前五。
新年过后,小妮就要高考,她想考北大,如果不行,也要上北京的其他学校,她记得小哥哥的专业和班级,相信他还会在那里继续深造。
这样想着,小妮点燃一根小小的焰火棒,金黄的烟花安静绽放,温柔的,毛茸茸的,像一簇小小的希望。
本版画作为丰子恺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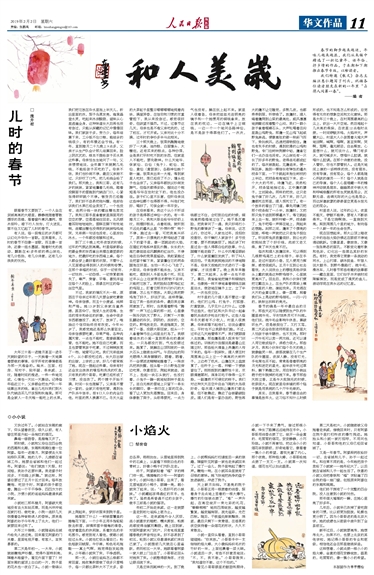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