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春节又要到了,一个人坐在京城高高的大楼里,静静梳理着零散漂浮的思绪,看着窗外寒风凛冽,草木低吟,楼下行人匆匆,灯火迷乱,禁不住又忆起了儿时的春节。
有人说,每一段难忘的岁月都可以幻化升华为一首歌。在我看来,儿时的春节不但像一首歌,而且像一首诗,还像一组水墨画,随着时光的流动,飘散在40多年前的燕山深处,有几分悠扬,有几分诗意,还有几分淡淡的忧伤。
大年三十是一进腊月甚至一进冬天就盼望的日子,一天挨着一天地算着要做的事情,似乎所有的事情都是为那一天准备的。淘米、压面、扫房、写对子、贴年画、串亲戚、上坟,随着时间的推进,一件一件地完成,心情也一天比一天激动。记得每年临近三十,父亲都会把生产队一年结算出来的钱,拿出几毛叫我们到大队代销店买几斤冻梨和秋海棠。那可是全家人一冬天唯一能吃上的水果。我们把它放在冷水里泡上半天儿,析出里面的冰,梨子乌黑发亮,海棠晶莹水灵,吃起来冰凉酸甜,滋味从心里透遍全身,这种味道长大后再也没有尝过,只能从深藏的记忆中慢慢回味。我们家孩子多,劳力少,每年结算下来,工分抵不住口粮,能结余的钱很少,有的年景还会亏钱。有一年,直到腊月二十九晚上9点多,父亲才从生产队会计那儿结算回来,脸上阴沉沉的,根本不提给孩子买水果这件事。母亲怯生生地问了一句,父亲愤愤地说,全年算下来就剩几毛钱,不能给孩子买吃的了。母亲不依,我们也吵闹不停,最后父亲拗不过,只好叹了口气,把几毛钱全给了我们。那天晚上,我和三哥,还有几岁的妹妹,紧紧地攥着几毛钱,踏着没脚面子的雪跑到代销店门口,心紧张得砰砰跳个不停。售货员已经睡了,我们好不容易把他叫醒,他却告诉我们水果已经全卖完了,一个也没有,连两分钱一块的螺丝糖也卖完了。我和三哥手里拿着家里筛面用的空空的箩,空落落地往回走。北风顺着耳际咝咝地吹,雪踩在脚下吱吱地响,连螺丝糖也没得到的妹妹呜呜地哭,兄弟俩一句话也没有,心里凉如冰水,一个年都没有暖和过来。
到了三十晚上吃年夜饭的时候,过年的气氛达到高潮。村里每家都会把最金贵的东西拿出来摆在最显眼的地方,把最好吃的东西端上桌,每个人都会穿上最好看的衣服,不管什么人见面都会得到别人的问候和夸赞。在那个幸福的时刻,似乎一切贫穷、一切忧伤、一切怨恨、一切劳累都消失了,尊严、荣誉、平等、喜悦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荡漾在村庄的每一丝空气里。
不过,我家的情况不大一样,原因在于母亲过年那几天要全家吃素敬神。母亲信佛,而且十分虔诚、纯粹和严格。她13岁到父亲家当童养媳,孤苦伶仃,饱受人生的苦难、生活的艰辛和命运的折磨,生命中很多东西都磨没了、耗光了、放弃了,唯独这个信仰始终没有改变。今年90岁了,我感觉她还是那么执著坚定。母亲信佛要吃素,非常严格,各种肉属天荤,一点也不能吃,葱姜蒜属地荤,也不能吃。她不但自己吃素,而且也要管束孩子吃素,不过稍稍放宽了一档,地荤可以吃。我们兄弟姐妹6个,从小都没吃过肉,长大后出嫁的出嫁,上学的上学,好几个都背叛了她,现在一提起这件事,母亲有时还会发出淡淡的嗔怪和浅浅的叹息。只有我的两个哥哥,吃素已经形成了习惯,没法改了。两个嫂子开始不满,时间一长也理解了。父亲是不管这一套的,全家只有他吃荤,遇到生产队杀牛宰羊,按8口人分的肉全归他,村里的男人羡慕不已。冬天火盆的大茶缸子里整日嘟嘟嘟嘟地炖着肉块,满屋异香,在信仰和习惯的双重管控下,我从来没尝过,感觉很好奇,但欲望不强烈。不过,过春节这几天,母亲也是不准父亲吃肉的,过了初五,才可开戒。父亲对此十分不满,过年时的争吵多半与此相关。
三十那天晚上,饭菜热腾腾地做好了一大桌,油炸糕、白面馒头、大糖包,还有买来的糕点,各种炒菜,全是我们平时吃不到的东西,但家里人不能吃,要先敬神。什么天地爷、保家仙、白仙(兔子)、蛇仙、狐仙、黄仙(黄鼠狼),各路神仙挨个敬一遍,饭菜夹出来一大堆,等到家里人吃时,菜已经没了不少,馒头包子也全凉了。父亲每年都抗议吵闹发脾气,但每次都得妥协,据说这个规矩是爷爷在世时定下的,他也没办法。孩子们心里不乐意,但听母亲说这些神仙哪个也得罪不得,叫他们吃好、喝好了,可保全家一年平安。
在母亲看来,我这个从小不听话的孩子是得罪过神仙一次的。有一年腊月三十,我和大哥去给爷爷奶奶上坟,刚摆好糕点,点着纸钱,就听到不远处的灌木丛里“扑愣扑愣”响个不停,跑过去一看,可把我高兴坏了,原来一只漂亮的大野鸡钻进了猎人下的套子里,像一团跳动的火焰,在猩红的皂栎林里乱扑腾,长长的大尾巴像姐姐迎风飘拂的红丝巾,不停地在白净的荒草里摇动。我赶紧跑过去把套子解下来,紧紧攥住它的两条腿抱在怀里,生怕一不小心飞走了。大哥说,母亲信佛不能杀生,父亲不能吃,落到别人手里也是个死,而且过年从山上往家带活的野物不吉祥,只能把它放了。我把脸贴在野鸡红红的鸡冠上,盯着它那双扑闪扑闪的大眼睛,怎么也不想放。大哥让我把野鸡抱了好久,好说歹说,连哄带骗,答应了我一些别的条件,最后我总算同意放了。那时,当我看着野鸡“腾愣”一声飞过山梁的那一刻,心里像一阵冷风吹灭了野火,只剩下一片散乱翻动的冷灰,阴阴的,凉凉的,空空的。野鸡放走后,我追悔莫及,哭闹了一番,没跟大哥回家,扭头一个人拿着弹弓往山沟里去打鸟了。我顺着结冰的小溪一直到那条沟的最深处,一只鸟都没打到,气也没顺过来。跑累了,就躺在山顶阳坡的一块大石头上继续生闷气。午后灿灿的阳光晒得人浑身暖暖的,晒着,晒着,不一会便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一阵凉风把我吹醒,扭头看一只小野兔在旁边吃草,欣喜若狂,爬起来就追,追不上,捡起一块石头就打,也没打着,小兔子一蹦一跳地钻到林子里去了。洁白无痕的雪地上只留下一串长长的脚印,像一串印在上面的花朵,看了让人更加失落懊恼。回来后,身体像散了架子,头疼得要死,一点力气也没有,躺在炕上起不来。家里人很着急,母亲把姐姐光洁明亮的镜子和一个她惯用的铜钱拿来,放在我的枕边,一边在镜子上立铜钱,一边一个一个地问各路神仙,是不是孩子得罪他们了。一次次,钱都立不住,念叨到白仙的时候,铜钱竟然稳稳地立住了。她于是沉着脸,把我审问了一通,我只好将打小野兔的事情讲了一遍。母亲说,这怎么行,你过年,人家也过年,没招你没惹你,你干嘛打人家孩子!多亏没打着,要不然就麻烦了。她还讲了村里过去一些人得罪白仙的故事,什么腿瘸不能走路了,什么中风嘴歪眼斜了,什么家里癫狂发疯了,听了叫人很后怕。于是我就照她说的不停地赔不是,母亲又按她的方式进行了一番破解,才说没事了。晚上我早早睡下,第二天起来,头便一点也不疼了。事后,我偷偷地把镜子和铜钱找来,也像她一样不停地拿着铜钱在碗里沾水,使劲地在镜子上立,立了半天,一次也没立住。
村子里的几个猎人是不管这一套的,他们打山鸡、打兔子、打狐狸、打黄鼠狼,几乎见什么打什么。过春节这些天,他们还和大队书记一起拿着民兵连的步枪去打狍子。这些人每年冬天都有不少收入,村里人很羡慕,母亲却看不起他们,总说会遭报应,平时也不让我跟他们跑。不过,过年这几天她管得不严,我们便跟猎人去放鹰。那些鹰是猎人捉来专门训练过的。训练的方法据说是避暑山庄建立时,那些给大清皇上养鹰的人传下来的。每年一到深秋,猎人便在村周围高山尖上立一个高高的大树杆子,上边布了机关,山鹰在天上盘旋累了,往杆子上一落,咔嚓一下便被套住了。刚刚捉到的鹰野性十足,双眼清澈犀利,浑身羽毛干净得一尘不染,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我们对这种天天在空中自由飞翔的大鸟很好奇,每次猎人捕到山鹰我们都去看,但不敢靠近,靠近了会被戳破脸皮。猎人们是有一套办法的,野性再大的鹰不让它睡觉,多熬几夜,也都乖乖驯服,听使唤了。放鹰时,猎人端着鹰爬到山梁的最高处,威风凛凛地俯瞰巡视着整个山沟,我们一群小孩子拿着棍棒石头,大声吆喝着在沟里轰山鸡野兔,那鹰一见山鸡飞起或野兔奔逃,便像离弦的箭一样斜飞而下,势如疾风,迅速把猎物捉住。鹰也有失手的时候,遇到狡猾的山鸡和野兔,专门往树林荆棘中钻,鹰拿它们一点办法也没有。大山深处有一只长了好多年的野兔,老得连毛都成红的了,每次被轰起,见鹰追来,便一阵狂奔,跑到一棵细长有弹性的灌木枝条下面,一下子跳起来抱住树枝的上半边,把枝条弯弯地压下来,成一个大大的弓形,待鹰飞近,突然松开,枝条猛地抽过去,正中鹰的膆子,立刻毙命。同样的把戏,这只老兔子演了好几次,几年下来,好几只鹰都死在那里,猎人恨死它了。有一个放羊的看出了门道,事先用镰刀把那个枝条削了一小半,放鹰时,又把那只兔子追到那棵灌木下,等它跳起来上去一抱,就听咔嚓一声,枝条断了,兔子吧嗒一声摔在地上,爬起来还想跑。刹那之间,鹰来了个漂亮的回旋,哗啦一声就把这只老兔子捉住了。听说那兔皮质量很好,到公社的收购站卖了个好价钱,肉却又老又柴,煮了半天也煮不烂。
每次和猎人放鹰回来,可以得到几根野鸡尾巴上的长翎子,举在手里,走过村里的小巷,见人便用力挥挥,感觉很威风。正月十五到公社去看戏,大人说戏台上的穆桂英杨宗保头上戴的就是这种野鸡翎子,心里就更高兴了。回去后,我和小伙伴们便把它戴在头上,在生产队的草垛上模仿戏里的人物,演起戏来。月光洒在大片的金黄谷草上,像一层霜,照着我们头上晃动的野鸡翎毛,一闪一闪的,映射出别样的亮光。
春节的确是一年中最自由的日子,那些天还可以随便到生产队的牛圈里梳牛毛,平时饲养员可不叫梳。他们说,梳牛毛会影响牛休息,算破坏生产,若是被捉住了,又打又骂,第二天还会告到老师那里去。家里大人怕孩子被牛踢伤,也不支持。那时一斤牛毛可以卖一两元钱,还可以请人用它做成毡子,诱惑力很大。那些岁月,我和小伙伴们每个冬天的晚上就像幽灵一样,游荡流窜在几个生产队的牛圈里,夜深人静,没有灯光,手电筒也买不起,常常是借着明亮的月光和迷茫的星光,趁半夜牛吃过草料,躺下熟睡之际,用自制的小铁丝筢子把牛脱掉的毛梳下来。春节那些天刚立春,正是牛大批脱毛的时候,收获很大。现在家里母亲铺的那个毡子就是用我梳的几十斤牛毛做的。
其实,在我看来,春节最自由的事情是放年火,这习俗不知什么时候形成的,也不知是怎么形成的,总觉得有无穷的想象空间和文化意味。那是大年三十晚上,在村周围最高的山尖上,砍出一大片空地,然后堆起十几米高的柴垛,在夜里12点准时点燃,一时间锣鼓齐鸣,火焰冲天,声震大山,村里大人小孩围着火堆大声地说啊,喊啊,唱啊,甚至笑啊,哭啊,骂啊,毫无顾忌,自由释放,心里想什么,就可说什么,嗓门有多大,就可喊多大,想唱什么腔调,就唱什么腔调。在那个诗意的夜晚,没人管你,你也不要管别人。这是天地间上演的一场特殊的戏,没有剧本,没有导演,没有观众,每个人都是随心所欲的演员……不!每个人就是自己的导演,每个人心里埋藏一年的精神冲动就是剧本,幽幽黑夜中被火光和呼喊唤醒的所有生灵就是观众,沉默无语、连绵无际的大山也是观众,而这深邃寂寥的渺渺星空更是永恒无边的观众。
村里老人说,过年的山火,夜里不能灭,锣鼓不能停,要有人不断添柴禾。于是它烧啊烧,一直烧到天亮,照到周围几十里的地方,射向每一个人新一年的生命世界。
现在回想起来,那大山顶上暗夜之中的汹汹火焰仿佛还在眼前不停地涌动跳跃。它像星星,像波浪,又像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不断变化着形象和色彩,幻化出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有时,我觉得它更像一条流动的河水,上山打猎、破冰捉鱼、听盲人说大鼓书、到野外撒路灯、梳牛毛、滑冰车,儿时春节那些有趣的故事都一一藏在里面,它们似乎并未被时间降解挥发,而是变成了清灵的鱼儿,游动浮现在我永远的记忆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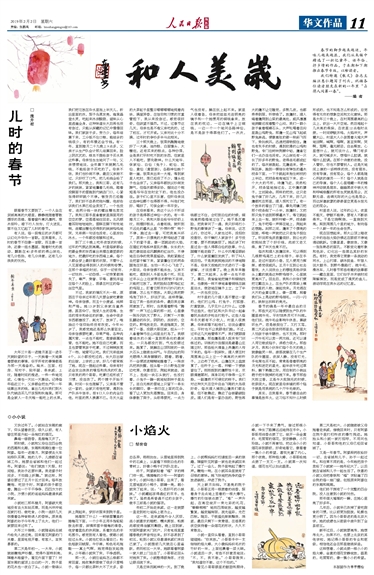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