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海外华文女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不约而同从以性别批判与关怀的文化视野,以超越自我与他者的人类家园意识,转向对女性个体生命、母系家族与家国的多面历史书写。她们通过考古式的史料挖掘与个性化的审美想象,重塑灵魂,重构真实。这种新历史小说,把混沌破碎的性别经验、家国之痛的记忆碎片,聚合成男女两性生命之花,甚至是整体人类精神进化图景。其中,重构女性与母系血缘家族谱系的历史书写,构成一道人类精神诗意栖居的靓丽风景。
用母爱之光点亮世道人心
从海外女性创作看,重构女性与母系家族历史,重塑母亲形象与重释母女关系,是从女性个体记忆出发,抑或从女性个体驾驭命运的生存浮沉,牵引出母系血缘维系的几代女性生命故事,对女性历史进行重新书写。绝不仅仅是批判封建男权对女性的压制歧视,更重要的是回望生命来路,寻找原乡记忆,试图以母爱之光点亮世道人心。
女性母系血缘家族谱系历史的书写,把母亲主体推到历史前台,展示母亲坚韧、独立与智慧的生命状态,善良、包容与博爱的母亲精神,将母亲生命意义与母爱价值镌刻于人类历史。旅英女作家虹影,有着浓厚的寻母情结。多年执著于母亲形象与母女关系的重塑。她的《饥饿的女儿》《好儿女花》《米米朵拉》,是女性自传体式的新历史小说。
马来西亚华人女作家戴小华的非虚构长篇新作《忽如归》,是一部用爱缝合被撕裂的家国痛史。小说叙事者“我”,也是女儿的“我”,小说中的母亲是远在台湾的逝世母亲,也是母国的隐喻。在从台湾到大陆还没有“三通”的年代,“我”7天之内用飞机把母亲遗体从台湾送到大陆的故土安葬,“我”坚信“冥冥之中一定有种强大的爱的力量”。小说以简朴白描,描写女儿的灵魂簇拥着母亲的灵魂回到母国故土的怀抱,一种感动天地之心的爱在浩瀚时空涌动。
美籍华人女作家严歌苓的《妈阁是座城》,加拿大华人女作家张翎的《阵痛》,这两部小说具有惊人相似的精神同构。她们以一个女人和她的孩子作为基本意象与经验主体,重建两个家族三代女性的命运历史。她们以家族喻国族与人类,以血缘遗传喻文化根脉传承,对家族基因遗传对民族性与人类性的影响进行开掘,试图为现代人寻找超越精神困境的出口。
美籍华人女作家施玮的《世家美眷》,以陆家的第四代女人的亲历口吻,讲述陆氏家族四代女性隐忍、挣扎与反抗封建男权政治的压迫,是一部塑造女性灵魂的历史;加拿大华人女作家李彦的作品从《红浮萍》到《海底》,三代母女关系水火不容的冲突如变奏的命运复调,随着时代身份的变迁,纠结延展,但母女在机场紧紧拥抱的离别场面,对海底与海天生命状态不同价值的认同,最终化成母女情感从血缘升华到精神之爱和解。
放飞现代女性生命智慧
女性成长传记的历史书写,实际上是女作家的精神自传。她们生活在女性精神生命自我重建的现实里,驾驭着理性的激情与梦想,经历灵魂涅槃,放飞现代女性生命智慧。
加拿大华人女作家王海伦的《枫叶为谁红》,描写一个失婚的华人女性历尽千辛万苦寻找家与重建新家的过程,完成自我灵魂的救赎,拥有了化梦想为生活的神奇生命。小说结尾“枫叶为谁红”有了答案:为世代传承的母爱而红,为人类美美与共的博爱而红。漫山红遍、层林尽染的枫叶意象,是个体的,也是集体的;是自然生态的,也是人文生态的。这里是一个充满爱和美好的人类灵魂诗意栖居地。
加拿大华人女作家江岚的《双面牡丹》,是以自己和周围华裔女性的生命体验为素材,书写的一部华人知识女性的成长传记。美籍华人女作家陈谦的《无穷镜》塑造的硅谷红珊科技公司的CEO珊映华人女性形象,以精神性自审卓立于世界华文女性文学长廊。陈谦在无穷镜下,把追求自我实现的精神理想——烟花”,推演到高山之巅,在一个个悖论接踵而来的瞬间里,上下求索,获得人类精神高原的巅峰体验,揭开华人女性自我意识觉醒之后,更深层的精神生命真相——渴望真爱。
《饥饿的女儿》是以女儿为主体形象的历史叙事,因双重饥饿即肉体与灵魂的饥饿所导致的母女之间的纠结,是刻骨铭心的痛。《好儿女花》则是以母亲为主体的母亲历史。女儿以参加母亲葬礼为线索的忏悔反思,营造出一个新的母亲世界,一个暖融融的母亲爱巢。女儿把母亲的身世一点点解开的同时,也抚平了母亲与女儿灵魂最深处的痛。女儿面对去世的母亲说,“前世你做我的母亲,来时你做我的女儿”。因此,虹影创作了奇幻小说《米米朵拉》,一个小女孩寻找母亲的故事。女儿再次成为小说的主角(当然也是母亲的转世)。这里的母亲隐喻是双重的,既是现实生活的母亲,也是自然母亲。小说开篇是山洪暴发和母亲缺席,其内在的因果关系是,人类自我中心膨胀的贪欲导致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的严重危机。自然是人类的母亲,人类破坏自然,母亲便会彻底离席,试图唤醒人类的家园意识。
严歌苓的《妈阁是座城》通过澳门妈阁、美国拉斯维加斯等地赌场的现世奇观与梅家日常生活事件交织,演绎了一场世代博弈的灵魂战争。第五代孙女梅晓鸥在祖奶奶梅吴娘的灵魂帮助下,拯救出自己、儿子、情人。母爱的救世力量,颠覆了男权文化歧视女性生命价值的陋根。
张翎的《阵痛》以三代母亲的生育阵痛对应三次战争历史的横断面,“三代女人,生在三个乱世,又在三个乱世里生下她们的女儿。男人是她们的痛,世道也是她们的痛,可是她们一生所有的疼痛叠加起来,也抵不过在天塌地陷的灾祸中孤独临产的疼痛。”也就是说,母亲最伤心的痛就是自己男人的不在场。一个母亲的阵痛之后,带来的是一个家族的希望;一个时代的阵痛之后,带来的是整个民族的崛起。当然母亲在场与父亲的缺席,从更深文化层面看,是复杂的隐喻,是对战争的反思,也是对人类和平的呼唤。
施玮的《世家美娟》塑造的陆家第二代女性陆文荫内心具有不可战胜的强大。她在92岁寻找爱情的生命长河里,一直渴望得到男性的真爱,但是,所有被她爱过或恨过的男人,都让她尝尽爱与性、灵与肉分裂的耻辱体验。在生命最后时刻,她毅然决然地回到陆家大院少年时代的绣房,放弃一生对所有男性偶像的膜拜,平静安详地寿终正寝。叙事者在彻底解构男权婚姻家庭历史的同时,重构女性个体生命。
在色彩斑斓的女性文学描述里,爱是人类最高境界的伦理,这是海外华文女作家在跨国界、跨文化与跨种族的生存环境中,处处有家、处处无家园的无根飘流里,化解了原生故乡与第二故乡的博弈冲突之痛,多重边缘身份的恐惧,以及异质文化认同的危机。在母国哲学“万物与我为一”的终极平等伦理理想影响下,超越西方女性写作的“为女人”,试图用文学的形式为人类寻找诗意的栖居地。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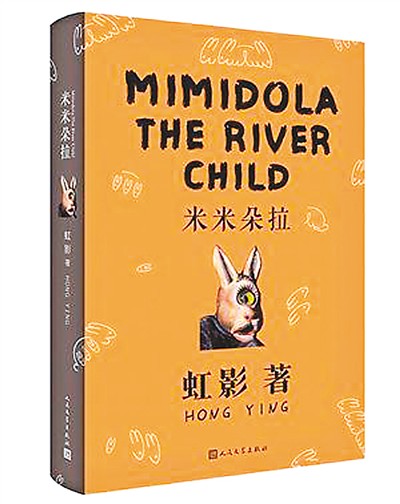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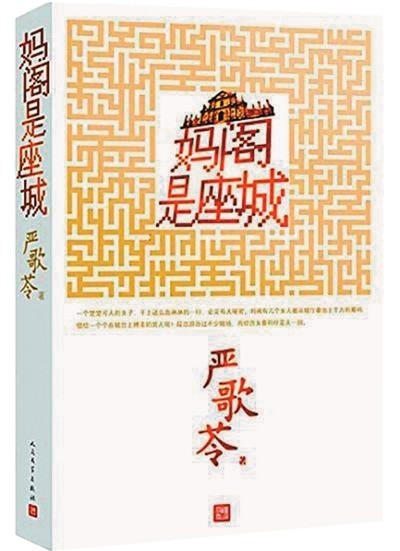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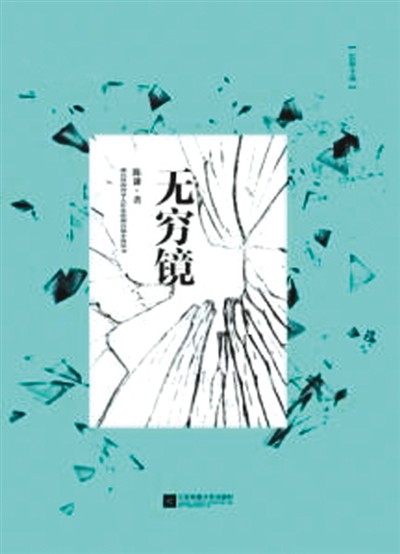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