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在家天天吃炉包,美得到现在还忘不掉。”记者的同事刘格子老家在山东,那里的高密炉包让他经常挂在嘴边,近期回家休假更是不忘恶补一番。不过,就在单位十字路口的拐角处,有一家餐厅就以炉包为招牌,但格子去过一次之后再也没有做回头客的冲动了。
“太油腻了!老家的炉包只有淡淡的油香,带肥的猪肉嚼起来也是肥而不腻,与这里的天差地别。”格子的话音刚落,同事们就七嘴八舌讨论起来。谈到自己在北京吃到的家乡美食,大家纷纷表示都有不同程度的走味,甚至完全是“挂羊头卖狗肉”。
为何曾经的家乡味道不再是记忆里的感觉?是偷工减料、荒腔走板,还是入乡随俗?在采访和调查之后,记者试着给出答案。
偷工减料,原料和手艺并未到位
事实上,刘格子感到口味不正宗的不只有在北京的高密炉包,还有潍坊的肉火烧。在他眼里,肉火烧里的猪肉、葱花、鸡蛋糕、海米都需要手工剁成泥才会吃起来津津有味,而在北京的所谓潍坊肉火烧,里面的陷儿不少都是靠机器绞制而成,两种工艺让味道相去甚远。
偷工减料,是不少受访者提到家乡美食落地北京后变味儿的首要因素。
与潍坊肉火烧变味儿的原因相似,潮汕牛肉丸也在京城有着雷同的遭遇。来自广东汕头的朱玉告诉记者,北京所谓的潮汕牛肉丸,弹性程度不够,主要是因为它们由机器压制而成,而非手工打造。
“要知道,牛肉丸的制作极其费工夫,需要手执双铁棒或其它硬物,像举锤子一样,和肉纹同一方向轮流捶打,一直打成肉酱。”朱玉表示,只有这样的工艺才能让手捏的牛肉丸变得颇具弹性,煮熟了扔在地上能够弹起来。可惜的是,北京的很多所谓潮汕牛肉丸都没有采用这样的工艺,自然在被咬一口之后就“露馅”了。
除了工艺流程上的打折扣,原料方面,不少在北京流传的家乡美食也没能准备到位。比如来自闽南地区的俊颖颇爱吃那里的传统甜品芋圆,它们主要用番薯(地瓜)、紫薯、芋头混合木薯粉制成,煮熟后加入刨冰或红豆汤往往香甜可口,饱满弹牙。但在北京,如果不是去像鲜芋仙这样的品牌连锁店,他往往会对吃到的芋圆大失所望。
“听说是因为商家为了节省成本,所以没有用相对较贵的木薯粉,而是用其他淀粉代替,然后加了些添加剂,所以不那么有嚼劲。另外,它们看上去是黄色、紫色,其实都是色素染成的,而正宗的芋圆来自番薯和紫薯的天然色泽。”
无独有偶,在木樨园一家写着“温州海鲜”的餐馆吃饭时,记者发现原本鲜美又有嚼头的温州鱼丸变得松松垮垮,鲜美程度也难以用味蕾察觉。该店的老板抱怨说,最好的鱼丸需要用鮸鱼做,加上少量淀粉。但在北京,新鲜的鮸鱼不容易买到,用多了成本就很高,所以有时就多放点淀粉“充数”,或者就用更便宜的鱼代替,口感有落差就不足为奇了。
此外,有广东朋友抱怨北京许多港式茶餐厅的“蚝粥”用的是不到广东1/4大小的生蚝,因而粥里并没有蚝在炖煮后释放出的鲜美汤汁,靠的是味精来提味;新疆的受访者认为许多北京新疆餐馆里的拌面没有用煮过西红柿的汤汁而是直接用了包装袋里的番茄酱,以至于酸味尝起来不自然,甚至有些过度;黑龙江的食客一直计较于北京东北餐馆里的杀猪菜没有用现杀猪里的内脏和血做主料,让自己觉得“不得劲”。
这些原材料方面不够悉心的做法都让在北京流传的家乡美食显得徒有虚名,而“节省开支”往往又成为店家“推卸责任”的最大理由。
荒腔走板,忽视细节的“家乡菜”
前不久,记者第一次来到中国西部的美食之城成都。在那里,记者不仅吃到比北京更有韧性的凉粉、更薄的夫妻肺片,还吃到了清汤炖煮的蹄花(猪蹄)和用糯米制作、蘸着红糖汁和花生粉吃的糍粑。成都的美食虽早有耳闻,但在成都吃到了清淡的美食对于来自中国东南沿海的记者来说实在是幸福满满。
“实际上,成都的菜肴和小吃里只有一部分是辣的,剩下相当数量的美味佳肴都属于清淡系。”成都的民间画家王德培也是一位美食家,他经常邀上三五好友到“苍蝇馆子”(意指街头巷尾的小餐馆)“打牙祭”,吃的菜里边好多都是非麻辣口味。
但在北京,记者个人对川菜被“以偏概全”地宣传有深刻感触,似乎只要是麻辣的就是川菜,或者说川菜唯一的特点就是麻辣。这种片面宣传某一地方小吃或菜肴的方式也容易让正宗的家乡美食在北京“走了味”。
“就好像宫保鸡丁,除了有辣味还必须注重放干辣椒,做到辣而不燥;而鸡肉丁必须鲜嫩,花生米也要酥脆,这样的组合才是正宗的川味。”来自四川的袁盼刚刚在公司门口吃完一份宫保鸡丁盖饭,对于里面口感偏老的鸡肉、硬化的花生米、湿湿的辣椒,他显得颇为不满。他强调,如果餐馆的经营者只知道宫保鸡丁需要辣椒、鸡肉、花生米、黄瓜,而不注重每个细节,那做出后肯定不叫座,至少不吸引四川人。
而在四川“隔壁”的重庆,烤鱼,尤其是万州和巫溪的烤鱼颇为出名。但提起北京的巫山烤全鱼时,家在重庆的小熊却向记者连连摆手:“很多店里的厨师没有学到精髓,只是单纯放辣或调制其他口味。事实上,重庆的烤鱼远比他们理解的要复杂。”
配备更多佐料、用蒜粒帮鱼产生香味、鱼要烤到皮酥肉嫩……小熊向记者列举了很多条他感觉北京的重庆烤鱼“不达标”的地方。在他眼里,单纯地把辣椒和鱼放入容器直接用火烤就能端上桌,这样对烤鱼的把握就没有“到位”,也容易让重庆以外的人误以为烤鱼就这么“简单粗暴”。
“还有像重庆火锅,一般是九宫格,不同火候和底汤的格子内涮食不同的原料。而在北京的重庆火锅,一般就简化成鸳鸯锅。实际上不同菜品在不同辣度和火候里涮出来的口感还是相当有差别的。”
像这样的现象还有很多,比如台湾菜里的三杯鸡需要九层塔(一种植物)带来特殊的香味,但很多餐馆却忽视了这点,用大葱来替代;武汉热干面有十多种佐料,在北京很可能就简化为麻酱和面;河南烩面的汤需要用羊肉和羊骨(甚至有的是放一整只羊)炖煮,但在北京有时就被理解为面与随意炖煮的白汤的结合。细节是否到位,决定了味道能否让家乡人产生乡愁。
“就上述状况而言,我们国家需要细化精品菜肴和小吃的制作标准。尤其是各地政府和行业协会,要把这些美食当做非物质文化遗产来保护,提升它的工艺性,避免随意发挥。”在采访中,中国烹饪协会副会长冯恩援对“家乡美食”在推广中不注重细节的做法给出了药方。
“比如四川就将出台川菜调味品标准,像豆瓣酱、红油等等,每种成分需要多少含量都有规定。消费者如果感觉有差异,可以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标准的存在可以让特色风味的精确程度在异地推广时变得可控,离正宗口味就更近了。”
入乡随俗,将特色让位于“大众”
在北京,大家很容易在街边找到写着“成都小吃”的店面。例如仅在北京西站方圆不到3公里的范围内,就至少5家经营着“成都小吃”或“成都美食”的小餐馆。事实上,店里并没有售卖具有成都当地特色的风味,有的只是各类盖浇饭。
在苏州街,记者在一家写着“成都小吃”的餐馆里看菜单时发现,上面写着“小笼包子”和“烫面蒸饺”的价目栏被划掉了,剩下的全部为盖浇饭。店里的厨师告诉记者,该店开业时卖过一段时间包子和蒸饺,但吃的人很少。“后来发现北京这边的人爱吃盖浇饭,索性就直接做这个了,还省事。”
而当记者来到簋街时,一家标着“川菜”字样的餐厅的厨师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告诉记者,店里最火的是麻辣小龙虾。“虽然这不是我们当地的特色小吃,但因为在北京比较火,老板认为是辣菜,就想到雇佣我们四川人来当厨子,也打着川菜的旗号吧。”
这种随波逐流的现象还有很多。比如同样在街头常见的“杭州小笼包”,不论是外皮还是肉馅都和在江浙沪地区售卖的小笼包相差很大,甚至被来自这些地方的人士戏称为“小一点的包子”。但在餐厅老板眼里,这样的包子在北京一般人都吃得惯,也很便宜,如果按照杭州的方式做可能又贵又难以有大量的客户,费力不赚钱。
当然,以上“入乡随俗”的做法有些过于“粗暴”。对于一些品牌连锁并走精致化路线的餐馆来说,改变菜品原先所属的地方口味以适应北京的大众口味是自己有意而为之的策略。例如在“外婆家”或“绿茶”这些定位为“杭帮菜”的餐厅里,不少浙江人对于很多属于川式做法的菜品有些不认同,但不能否认的是,它们总体在北京受到的欢迎程度很高。
“我想在这些所谓的浙菜餐厅里吃清蒸或者葱油的菜品时,服务员都会极力推荐烤或麻辣的方式,甚至有服务员都没有听过什么是‘葱油’。但这么火爆的人气只能说这种口味上的调和让北京大部分人适应了改良口味的浙江菜。”记者的朋友,来自浙江的思佳这样表示。
实际上,记者感受到许多地方的菜品到了北京在口味上都有适度的改良。比如川菜、湘菜在北京不再那么辣,上海菜不再那么甜,闽菜粤菜油盐含量会适度提高等等,这些都与北京的大众风味进行了“对接”。
“每一个地方的特色菜品都与原产地的自然条件、民俗习惯、价值理念有很大关联,所以形成了各不相同的特色。一旦这些菜品离开了与之息息相关的土地和人群,它们势必要入乡随俗,才能聚集新的人气。”在冯恩援眼里,家乡美食在京城的“走味”也有着必然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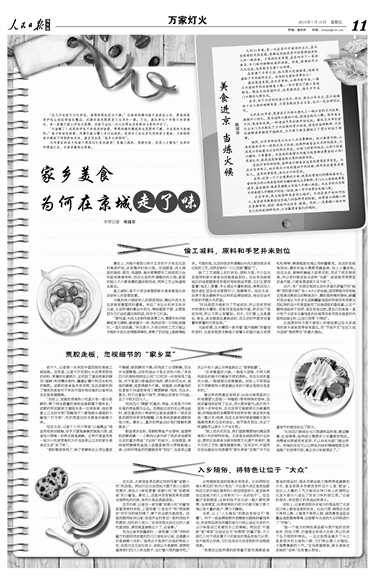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