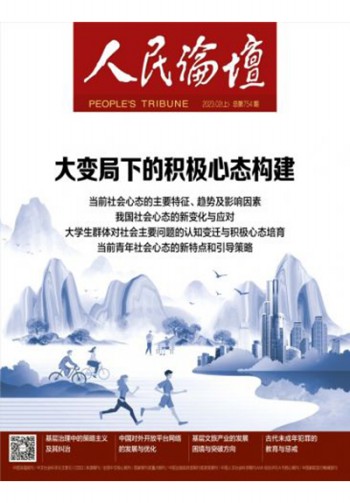【摘要】博物馆是一个流动变化的文化空间,通过不同的功能影响着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国际局势的起伏变化、疫情的持续影响,都在不同程度地加速博物馆的功能转型和价值重塑。博物馆文创是博物馆收藏、保护、研究、展览、教育等核心功能的重要拓展。博物馆文创叙事是一种知识生产与意义建构的空间表现方式,博物馆文创体验表现为一种公共气氛美学的审美公赏状态,博物馆文创运营通过创意策展、文化授权、故事驱动和跨界融合,正在推动当代博物馆建立起一套多元价值协同的创意管理体系。
【关键词】博物馆文创产业 场景体验 审美公赏 创意管理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博物馆作为人类历史“缪斯”之城和人类文化“博物”之所,是一个时空压缩的文化复合体,经历了私人珍藏、皇家典藏和大众收藏的千年嬗变,在不同时代承担着不同的社会角色。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起源于17世纪,这个时期将博物馆界定为“一个贮存和收藏各种自然、科学与文学珍品或趣物或艺术品的场所”。1683年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建立,1753年大英博物馆建成,博物馆开始走向公共性、大众性和开放性。1905年,中国近代实业家张謇建立南通博物苑,开启中国的公共博物馆时代。1912年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在国子监筹设国立历史博物馆,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博物馆成为中国现代社会蓬勃发展的见证者和推动者。博物馆既是一个凝思神游的静谧场所,也是一个知识生产的流动空间。博物馆功能体现了博物馆在特定时期的社会价值,经历了“从保护文物藏品到满足公众需求再到服务社会发展,进而向参与并推动社会变革的使命与职责回归”的发展演进过程。2022年8月,第26届国际博物馆协会大会在捷克共和国首都布拉格举行,大会通过了博物馆的新定义:“博物馆是为社会服务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研究、收藏、保护、阐释和展览物质与非物质遗产;向公众开放,具有可及性和包容性,促进多样性和可持续性;以符合道德且专业的方式进行运营和交流,并在社区的参与下,为教育、欣赏、深思和知识共享提供多种体验。”博物馆的新定义弱化了博物馆的神圣性和原真性,强调博物馆的公众视角和社区参与,彰显了博物馆面向社区与公众的开放性、包容性和渗透性特质。国际博物馆协会关于博物馆新定义的发布,将会重构收藏、保护、展览、研究、教育和文创等博物馆功能叙事的语言、载体和手段。
故宫博物院推出“故宫以东”共创计划,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平台搭建文博业态融合平台,将“故宫文创产品平台”升级为“故宫文创产业资源生态系统”。四川三星堆博物馆开发的“三星堆面具冰激淋”采用了独具特色的馆藏文物青铜面具原型,以浓浓的“出土味”和“青铜味”引领博物馆文创的潮流,逐渐构建起包含动漫、电影、小说、网游等文创产品在内的三星堆新文创体系。甘肃省博物馆以铜奔马为原型,开发出“马踏飞燕”主题文创系列产品,轻松、搞怪的“丑萌”风格成为博物馆界的爆款文创产品。这些博物馆文创实践探索,代表了博物馆叙事的表现方式和博物馆业务的展现形式,是对大众文化消费意识觉醒的积极回应,彰显了一种日常生活状态下的“博物馆力量”。在供给端的创造力生产和消费端的想象力消费的双重推动下,博物馆文创持续升温,不断冲击着博物馆展陈、研究、教育等其他功能,也考验着博物馆管理团队的运营能力:如何在文化坚守与公众迎合、社会效益与商业效益之间维持平衡。
博物馆文创叙事:构建超真实的空间场景
博物馆文创叙事是一种知识生产与意义建构的空间表现方式,实现了“物与人”“过去与现在”“个体与社会”的价值联系。博物馆文创生产是一种叙事性生产。博物馆既是以物的收藏为中心,以研究、教育、欣赏为目的的非营利文化机构,也是现有器物与知识的集合体,可以引导人类回顾、欣赏、衍发,进而创造新生文化。同时,博物馆以教育为圆心扮演着知识宝库与学习中心的角色,体现了研究叙事和教育叙事的核心功能。博物馆依赖特有的叙事载体——“物”,通过“物理重组”和“化学重构”进行展览叙事和文创叙事,经过“从客观世界中拆解——在主观世界自由重组”的过程,自觉“抗拒时空压缩的迫害”,显现出一种超现实主义的现实形式。博物馆的收藏叙事、研究叙事和展览叙事是一种静态叙事,博物馆的教育叙事和文创叙事是一种动态叙事。博物馆文创叙事推动了静态叙事与动态叙事的融合,贯穿于收藏、研究、展览与教育等博物馆核心功能的整个过程。静态性的博物馆功能通过动态性的博物馆功能,将博物馆收藏文物的膜拜价值、研究者阐释的展览价值与公众参与的体验价值联系起来,促进博物馆从内隐价值向外显价值的转换。
基于馆藏物开展多元阐释,是博物馆的核心使命。博物馆在此基础上建立起自身与参观者乃至社会的交流与沟通机制。博物馆对馆藏物的阐释包括不同的文创叙事策略。博物馆文创叙事的价值功效不同于博物馆的收藏叙事、研究叙事、展览叙事和教育叙事等核心功能,应采取不同的评价指标。博物馆作为非盈利机构,不等于其不能拓展各种市场化的收入来源。美国经济学家鲍莫尔和鲍温在合著的《表演艺术:经济学的困境》一书中提出表演艺术因“收入支出差”而带来的“鲍莫尔成本病”问题,也同样存在于博物馆的经营过程中。博物馆作为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准公共文化产品的公共空间和非营利机构,面临巨额的固定成本、高昂的机会成本、突出的变动成本、趋近于零的边际成本等,需要积极拓展除政府资助、社会捐赠、门票收益等之外的收益渠道。当然,我们不能因博物馆的文创功能而忽略、遮蔽或损害博物馆的收藏、研究、展览和教育等基本功能。
博物馆是收藏品的客观实物与参观者的主观想象同时在场的混合场域,博物馆的“在场性”是感性与理性、客观与主观、个体与社会的有效统一,体现了当代审美经验在博物馆领域的空间转向。博物馆犹如一架天平,天平的一端是供奉着神圣文物、精英艺术的神庙殿堂,另一端是融合个人体验、大众参与的公众论坛。在美国营销学家尼尔·科特勒和菲利普·科特勒看来,“博物馆已经从只限贵族进入的精英组织,演变成为更广泛基础的公共机构。博物馆重新定义自身存在的理由应该是更平等、民主和以消费者为导向”。博物馆文创叙事是博物馆从“神圣殿堂”到“公共论坛”再到“人民乐园”的内在推手,推动了博物馆收藏叙事从个人情感、家族凝聚走向公共认同,推动了博物馆研究叙事从研究者的专业成果走向社会的公共传播,推动了博物馆展览叙事从策展人的精英视角转向参观者的互动视角,推动了博物馆教育叙事从施教者的灌输立场转向受教者的接受立场,有利于彰显博物馆的公益性、公共性和开放性。
博物馆文创叙事通过新兴技术手段,构建出超真实的场景体验。法国文化哲学家让·鲍德里亚认为,“超真实”不是对真实的反叛,而是比真实更真实的状态。他指出,消费对象不是有形的、真实的物,而是无形的、抽象的符号,现代科技的发展直接影响着“物”的拟真在场方式。博物馆文创叙事借助VR/AR/MR等可穿戴式数字设备,通过场景模拟或实景复刻,构建三维立体博物馆,采用各种文化舒适物,打通实体博物馆和数字博物馆,构建元宇宙博物馆的体验场景,推动了博物馆全感知、全沉浸、全媒体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博物馆文创体验:营造公共气氛美学的审美公赏
博物馆经由真实的文物实物和虚拟的数字技术营造出一种独特的博物馆气氛美学。博物馆(museum)和娱乐(amusement)分享了缪斯(muse)的词根,博物馆的体验指向一种精神娱乐的内在状态。在学者王一川看来,“全媒体时代的艺术状况表现为传统媒介艺术与新兴媒介艺术并存交融及艺术传播者与艺术受传者之间双向互动,体现为多媒介艺术交融、跨媒介艺术传播、艺术家与观众双向互动、多重艺术文本并置等特征,导致越来越明显的艺术分赏现象,即由日常媒介接触惯习所形成的不同公众群体间相互分疏的艺术鉴赏状况”,“艺术学界可以而且应当做的事情是,在承认艺术分赏状况的前提下,呼唤艺术公共鉴赏即艺术公赏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并为艺术公赏力的正常运行创造合适的公共环境”。博物馆作为一种公共文化空间,是公众参观、讨论、参与以及学习的场所,通过博物馆式的公共气氛美学营造,实现面向公众的审美公赏。
博物馆的公共气氛美学,是跨越博物馆馆藏文物、展陈艺术品的客观美学特征和参观者各自单一的主体性美学感知而形成的一种共同在场的审美状态。博物馆的公共气氛美学调和了博物馆的文物艺术品的存在价值、参观者的选择价值和代际之间的遗赠价值。英国文化遗产保护学者伯纳德·费尔登把文物建筑遗产的价值分为情感价值(指奇观、认同性、延续性、精神的和象征的作用)、文化价值(指文献价值、历史价值、考古价值、美学和象征性的价值、建筑学的价值、市容、风景和生态学的价值、科学价值)和使用价值(指功能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政治价值),而博物馆的价值都具有审美公共性和艺术公赏力的特征。全媒体时代的博物馆文创消费是一种基于网络趣缘圈层的同类消费和公共消费。学者罗自文认为,趣缘群体是“一群对某一特定的人、事或者物有持续兴趣爱好的青年,主要借由网络进行信息交流、情感分享和身份认同而建构的‘趣缘’生活共同体”,“网络趣缘群体中独立传播的元素少,传播者和受众的融合使信息传播真正做到了‘以受众为中心’,在‘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良性循环下,实现了信息传播的真正价值——信息的交流与分享”。不同的参观者置身于博物馆整体的气氛美学之中,感受到一种共同的美学氛围、审美情调和艺术风尚,进入一种集体共情的美学宣泄和艺术公赏的体验状态。
博物馆满足了大众的公共文化利益,这种公共文化利益是通过艺术公赏力来实现的。王一川指出,艺术公赏力是“艺术的可供公众鉴赏的品质和相应的公众能力,其实质在于如何通过富于感染力的象征符号系统去建立共同体内外诸种关系得以和谐的机制”。博物馆的艺术公赏力旨在帮助共处一馆的参观者在博物馆的实物观照和展陈观展中,通过一种公共性的审美行为实现自身的审美体验和心灵放松,达到共同的文化认同和情感认同,实现从“自赏”到“公赏”的跳跃。审美公赏体现了博物馆在审美领域的公共性,可以包含可信度、可赏质、辨识力、鉴赏力和公共性几个要素。王一川在《艺术公赏力:艺术公共性研究》一书中指出:“博物馆审美公赏的可信度,即指博物馆馆藏品的可被特定共同体的公众予以信赖的程度,要维护博物馆的信誉和声誉;博物馆审美公赏的可赏质,即是博物馆藏品的可供公众鉴赏的品质,要坚持‘美善’原则;博物馆审美公赏的辨识力,即指审美公赏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观者对艺术是否可信所具备的主体辨识能力,不断提高博物馆文创消费者的艺术素养和审美能力;博物馆审美公赏的鉴赏力,是博物馆审美公赏得以发挥作用的主体要素和条件;博物馆审美公赏的公共性,特别强调博物馆中‘人与物’‘人与人’在纯审美与泛审美的现场互渗中呈现出越来越突出的公共特性。”博物馆文创体验的审美公赏效应,可以更有效地发挥博物馆的公共文化功能,实现参观者群体情感的平衡、博物馆所在社区的和谐以及城市美好生活的建设。
博物馆审美公赏的空间场景是一种基于身体在场的直接性体验,是一种包括感知、情感和精神在内的直觉体验,德国新美学家格诺特·波默称之为“气氛美学”的整体体验。气氛美学以“气氛”为核心载体,关注空间和空间性,“在以往时间占有主导地位的地方,气氛美学所挖掘和发现的却首先是空间性——正如,把夜晚当作空间现象来研究,或把音乐作为气氛来研究。因此,与普遍存在的远程通信相反,气氛美学将注意力集中于位置和身体性在场”。博物馆体验场景的空间性可以被看作一种特殊的场所精神,是一种现象学意义上赋予人与自身、人与社会、人与世界等特定意涵的空间,具有一种独有的博物馆场所精神。正如波默所言,气氛是一种被定了某种情调的空间性的东西。这个情调气氛充溢着符号象征、生命意义、审美意境。博物馆的公共气氛美学可以通过建筑、光、声音、气味等,以整体的气氛美学塑造参观者身处博物馆的空间环境,形成参观者的身体与物象(外物的客观形象)、身体与境象(人感知外物所得到的审美意象)以及身体与情象(参观者观照境象而升华的情感状态)的审美升华。
博物馆文创运营:走向价值协同的创意管理
博物馆气氛美学的空间场景赋予了日常生活以新的意义和价值,而场景体验又是数字时代创意与价值的连接机制。在美国社会学教授特里·克拉克和加拿大社会学者丹尼尔·西尔看来,场景是一种特定活动的共同兴趣,强调特定地点的某种特质,更是一种关于地方的美学视角。克拉克和西尔提出的“场景”拓宽了美国社会学家雷·欧登伯格提出的“第三空间”的边界。博物馆构成了一个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软实力,迷人、魅力和自我表达等博物馆文化元素非常适合地方创意经济的发展氛围。一座城市包括博物馆在内的文化舒适物的多少,反映了这座城市创意空间品质的好坏。博物馆文化舒适物是一种消费性集体资本,也是一种生产性创意资本,以博物馆为代表的文化舒适物的组合构成了一种吸引创意人士的创意场景,进而有利于激活地方的文化创意、科技创新、产业转型和经济活力。
博物馆文创运营的本质在于创造博物馆独特的场景体验,创造一种互联互通的真实生活情景,这种场景体验包含了戏剧视野下的故事场景、互联网视野下的生活场景、都市更新视野下的空间场景等复合层次。博物馆文创运营要实现个体创意与社会创新之间的价值转化,其创意场景的营造除了依靠气氛美学的制造、舒适物的组合,还要借助创意策展、文化授权、故事驱动、跨界融合等创意管理手段,最终实现博物馆文化生态的架构和协商价值的达成。
创意策展是博物馆文创运营的基本能力,是博物馆内生文化资源转化为外显生产要素的重要途径,可以激发博物馆所在社区和城市的创新活力。围绕博物馆的收藏、研究、展览、教育和文创等业务领域,创意策展依据科学阐释、审美提升和文化彰显的原则,可以从主题凝练、藏品遴选、陈列展示、产品设计、营销推广等各个环节体现动态性、全景式、互动型的技巧与能力。策展的重心在于艺术、人文、体验、社交的场景空间营造,为参观者打造高品质、高感知的游览经验、参观体验和文化记忆。
文化授权是博物馆文创运营的重要方式,是博物馆信息资源和品牌资源价值转换的主要途径,是推动博物馆典藏文物艺术品、研究成果转化的有效方式。博物馆文化授权是与博物馆有关的知识产权的授权及其使用过程。博物馆文化授权包括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品牌权等不同类型,是将博物馆馆藏文物的物质性形态通过非物质性的创意加工从而进行授权、研发、生产、流通、消费的全过程经营活动。2019年5月,国家文物局发布了《博物馆馆藏资源著作权、商标权和品牌授权操作指引》,就博物馆授权的内容、模式、流程以及相关的权利和义务进行约定,提供了直接授权和委托授权两种授权合同范例、资源清单表,对博物馆馆藏资源著作权、商标权和品牌授权操作路径进行了清晰的规划,加强了对博物馆授权业务的指导,促进了博物馆馆藏资源的有序开放、合理利用。
故事驱动是博物馆文创运营的关键环节,讲好博物馆故事、讲好中国故事是博物馆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博物馆的展陈、教育等各类功能都是围绕博物馆馆藏物的故事诠释而展开的。博物馆文创作为文化产业的运营范式,其核心是文化创意。文化生产的过程是以故事为核心的驱动过程,故事驱动运用无形的想象力,把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形成包括故事创作、故事改编、故事内容的跨媒体应用、跨渠道运营和跨产业融合的内在的故事产业价值链,造就庞大的博物馆文化经济。博物馆故事的讲述者是文物专家、鉴定专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收藏家与编剧、说书人、作家、设计师等多种角色的融合,要讲述博物馆的公共故事和共享的普遍价值。
跨界融合是博物馆文创运营的产业基石,是实现博物馆资源助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地方产业结构转型的表现方式。博物馆有利于营建城市的文化聚落、构建城市的创意生态、营造城市的产业集聚,“博物馆的建成不仅有助于服务与丰富市民文化生活,提升区域居民素质与创意竞争力,改变市民的艺术观念,同时有助于提升市民的文化消费能力,并培养市民文化消费的习惯”。博物馆跨界融合的文创运营,应基于博物馆文化版权和文化资本,发挥博物馆文化连接、创意赋能和协同共生的价值扩散机制,推动博物馆与社区营造、文化旅游、教育培训、文化商贸、智能制造、创意农业等各个行业和领域的融合发展,实现一二三产业的协同发展。
收藏历史文物、艺术珍品和自然标本是人类的文化天性,也是人类文明延续的重要途径。博物馆是人类文明发达的标志,是一种高级形态的社会文化现象。博物馆种类繁多,美国博物馆专家爱德华·亚历山大和玛丽·亚历山大将博物馆分为艺术博物馆、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学博物馆、科学博物馆、历史博物馆、植物园、动物园以及儿童博物馆等不同形式。博物馆是一套复杂的社会装置和传承机构,既有物态的无机物藏品,又有活态的有机物藏品;既有原物的审慎保护,又有新物的创新研制;既有静态的文物陈列,又有动态的研究教育;既有权威性的文化传承,又有生活化的创意体验。新时代的博物馆体验是一种集原物膜拜、展览参观与创意消费于一体的综合体验,兼具原真性与稀缺性、知识性与教育性、趣味性与娱乐性的多元统一的体验元素。博物馆以特定的馆藏文物为载体,连接人与物、人与人、人与社会,打破了自我封闭的知识生产,将博物馆纳入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生产的大网络之中,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博物馆也是展示全世界不同文明灿烂成果的文化窗口,是不同文明开放共享、包容互鉴的跨文化交流平台。当前,我国博物馆事业处在从“数量增长”走向“质量提升”的关键期,面对新兴技术的挑战和个体审美的崛起,博物馆不仅收藏人类的历史、保护人类的遗存旧物,而且创造人们的未来想象、丰富人们的美好生活。博物馆立身于一个多元利益相关者构成的复杂社会网路之中,需要平衡博物馆从业者、大众参与者、政府监管者、媒体监督者、专业工作者、商业开发者等不同参与主体不同的价值诉求,将文化权益与文化权利、文物保护与文创开发、社会价值与商业价值、私人视角与公共视角、本土立场与世界情怀等不同思考框架纳入博物馆生态治理体系中,平衡公共服务与商业运营的创意管理模式,探索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博物馆运营管理的新道路。
(作者为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信息技术高等研究院数字创意实验室主任)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文化产业合作共赢模式及路径研究”(项目编号:17ZDA043)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美]尼尔·科特勒、[美]菲利普·科特勒著,潘守勇译:《博物馆战略与市场营销》,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
②[法]让·鲍德里亚著、车槿山译:《象征交换与死亡》,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
③王一川:《全媒体时代的艺术状况》,《人文杂志》,2014年第11期。
④王一川:《论艺术公赏力——艺术学与美学的一个新关键词》,《当代文坛》,2009年第4期。
⑤[德]格诺特·波默著、贾红雨译:《气氛美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
⑥向勇:《创意管理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22年。
⑦单霁翔:《从“数量增长”走向“质量提升”:关于广义博物馆的思考》,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19年。
⑧张子康、罗怡、李海若:《文化造城:当代博物馆与文化创意产业及城市发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⑨[美]雷蒙德·阿古斯特著、周秀琴译:《博物馆的法定定义》,《中国博物馆》,198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