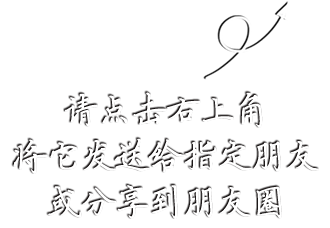小区里的叶子,带着金黄的心情,一枚枚从树上跳下,俏皮的女儿就催促我,买盆有意思的花吧,感受一下冬天里的春意。
“谁不想让春天提前到来呢?”我心想。
还没想好要买什么,妻子就买回来了,而且不是一盆,是两盆。我不知道这些花叫啥,但它们好像早就到过我心里。我常去周边的写字楼,它们就养在办公室里,形似披上了军衣,像极了人,一个个,正在忙着手头的事。
“这是什么花?”
“你没见过?”妻子不直接答我。
“见过嘛,常见着了,就是不知道名字。”
“嘿!米兰嘛,你连米兰也不知道,看你笨的。”她的眼光里有笑意,又轻轻移开,移到米兰的头顶。
把花摆放在客厅,又放到卧室、移到阳台,搬来搬去的,这看那看,斟酌着美学效果。最后固定下来,一盆在大卧室,一盆在小卧室。
天气瑟缩着身子,从刷得洁白的墙里透进寒气。冬天里的窗子,开得少了,但朝阳还是经常光顾。那米兰像隐忍着什么,总是豆绿的脸庞,没有新叶,也没有青绿,一副木木的表情。
“冬天嘛,万物都是藏着的。”我又这样想。
阳光越过窗子,摸遍架上的书籍,女儿跑进来,捧着我的脸,摇摇身子说:“爸爸,米兰好看吧?”
“怎么个好看?”
“那么多的圆叶子,都是祝福咱家的。”
我“噢”了一声,话还没说完,她的话就赶来了。
“你能数得清吗?”
“数不清哇!”
“那就好了!”她说着,撂下一句话,“你好好忙吧,大妞不打扰你啦!”
时光,在不经意中来,又在不经意中走。更多时候,我对米兰有点视而不见,没有裁剪,没有施肥,甚至连最基本的浇水,也偶尔忘了。
“我是一个不合格的家长。”我有时暗暗揶揄自己。
惩罚终于来了,米兰那豆绿的叶子,变得有点僵卷了,整个身形似被绳子捆绑过,看着它那灰溜溜的模样,我的心仿佛也抹上了灰尘。从这个卧室跑到那个卧室,我跑来跑去,巡察似的,看哪里出了异样。
“磷氮钾,这些肥料,都给施过嘛,水也浇了,咋就这样了?”
“冬天的花,本来也不好养,谁不知道?”
心里想的话,我们都没说出来,也许,没说出来,才是一种完满的交流。这交流里,那谜底各有各的妙。
春节快要来了,连响的鞭炮,提前就进入梦境里。迎新是要除尘的,最忙碌的是手,抹着、擦着、拖着……上上下下、里里外外、角角落落,都是要清洁的。我出差回来,电梯门开了,在楼道里迎接我的竟然是米兰,一盆挨着一盆,似乎有点不情愿的样子。
“它们是要去哪里?”
“好像不行了,枝头干涩涩的。”妻子的声音中,含着些许无奈。
“不行就算了,给保洁阿姨吧,看能养活不?”女儿也有点小情绪。
“先不用管,我往后再看看。”我把话留在有点萎靡的枝叶间。
物业的人,一般是很难等到的。我收拾好行李箱,就停下手里的活,挪出小梯子,给楼道换上新灯泡。那里滞留的黄昏,一下就不见了,不论什么时间,都是清晨的感觉。
我捏了捏米兰的枝干,变换着部位,那温湿还是存在的,越向下越是湿漉漉的。像医生把脉,我同样摸了摸米兰的头,茎叶还是有韧性的。
我确信米兰还活着,只不过有点像冬眠,以新的方式,闭着眼热身,把人们看不见的力攒足,根本不想外露,悄悄掩护着自己。
“再搬回来吧,活着呢。”
“活着吗?叶子掉了那么多。”
“那是假死,过了冬天就好了。”
“算了,算了吧。”
“不要算了嘛,我给你抢救……”
我把米兰又搬回家里,并且为它们互换了卧室,让它们呼吸新的空气。平日里,我把更多的视线投射在那里,在备忘录里记着每次浇水的时间,准许散光照在它们的身上,一旦发现叶子有点皱眉,那窗帘就会露出愧色似的,为它们遮身。
感觉它们一天天好了起来,没有多长时间,都是新叶了,满身青葱。那花开的,好似戴上了王冠,星星点点,怀着各自圣洁的心事,一朵呼唤着一朵;隔着一堵墙,一盆呼唤着一盆。
一盆呼唤着一盆,春天从掌心里出来,跑到哪里,哪里都有泥土。
“那么多的圆叶子,都是祝福咱家的。”我想起女儿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