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英国广播公司披露了一则消息,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创始人、首任最高领袖霍梅尼在获得政权的过程中,曾经向美国示好,表示新政权不会伤害美国利益,他对美国政府没有任何敌意。霍梅尼还称,伊朗会保护美国在伊利益,保证美国人在伊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政权将是“人道主义的”,有利于全人类。而且据说他在1963年也做过类似暗示,即他不反对美国利益,美国在伊朗的存在“能阻止苏联和英国在伊势力扩张”,等等。
这篇文章使外界对霍梅尼这位最高领袖的真实面目产生了疑问,有些人甚至认为霍梅尼有点表里不一。其实,这是对霍梅尼这位伊朗伊斯兰革命创始人的误读和浅识。
敏锐捕捉到国王与美国的矛盾
什叶派宗教领导人霍梅尼曾经长期被伊朗末代国王巴列维视为异己分子,软禁流放在伊拉克的什叶派圣城纳杰夫。他是极其精明的宗教领袖和政治家。早在1963年,他已看到了当时国王巴列维的“独裁、暴政”不符合美国时任总统肯尼迪的口味,就利用伊朗王室与美国白宫之间的嫌隙向美国示好。那时,霍梅尼已经62岁,其反美倾向在心里已深深埋下种子。从骨子里,霍梅尼反对西方、反对殖民主义和反美,但他又是精明的政治家,知道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最有利于促进事业发展。他会利用国王与美国之间的深刻矛盾从中渔利,掌握与美国斗争的节奏,时而“慷慨陈词”,时而“抑扬顿挫”,张弛有度。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埃及、叙利亚与以色列发生激烈的军事冲突,为了支援埃及,沙特阿拉伯等所有的阿拉伯产油国以及部分世界其他地区的产油国宣布对美国实施石油禁运,但伊朗是唯一没有对美国采取石油禁运的中东产油国。也是在那时,巴列维与美国时任总统尼克松之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蜜月时代。伊朗的GDP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长。大批的伊朗农民工涌入城市,基建项目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
由于石油收入来得太多、太容易,巴列维的自我感觉越来越好,声称要在25年后使伊朗的综合国力达到英国和西德的总和。同时,他对美国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对美国的石油出口价格陡然上涨了15%。这对于当时已深陷石油危机和“水门事件”丑闻的尼克松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当尼克松用哀求的口吻要求巴列维降低油价、帮助美国度过1973年寒冷的冬季时,巴列维口气很大地说:“我们已经对美国够客气的啦,我们目前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地位已发生了变化,现在不是我求你们,而是你们求我。”
尼克松下台后,继任的福特和卡特也遭遇了类似的“特殊待遇”。面对巴列维的敲诈,美国一开始束手无策。但随着沙特阿拉伯对美国石油禁运的解除,以及沙特国王与美国总统的会晤,沙特开始取代伊朗成为美国最大的石油供应国。沙特对美石油出口不仅不涨价,还保证“美国要多少就供应多少”。这一下,伊朗对美国的重要性直线下降。美国已不太信任在伊朗越来越不得人心的巴列维,开始寻找其替代者。
霍梅尼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虽然长期被软禁和流放,但并未减弱他对世界事务的判断及对伊朗国内事务的关注。巴列维是美国的朋友,有时又向苏联暗送秋波,这使得美国政府不快。而美国中央情报局认为,霍梅尼当时的反共、反苏色彩是美国所需要的。虽然没有证据显示中情局与霍梅尼有直接联系,但至少霍梅尼的反苏言论是中情局关注的。
甜言蜜语诱惑美国
1975年,时任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和伊朗国王巴列维签署划界的阿尔及尔协定。伊拉克失去了200多平方公里土地,被迫承认伊朗在波斯湾的霸权。同时,伊朗要求伊拉克驱逐流亡的霍梅尼,保证两伊什叶派“互联互通”。作为回报,伊朗不再支持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民族独立运动。萨达姆后来称这个协定是“屈辱和丧权辱国的”,这也是两伊战争的缘由之一。而巴列维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让霍梅尼埋下了回国领导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火种。
1978年下半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街头抗议以及与警察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民众的革命势头如火如荼。刚刚被萨达姆从纳杰夫驱逐到巴黎的霍梅尼坐不住了。他与顾问们仔细研究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对伊斯兰革命威胁最大的是60万几乎全部美械装备的伊朗军队,控制这支军队的是巴列维。向美国示好,就成了伊斯兰革命政权成功的关键。
精明无比的霍梅尼表示,未来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政权“无意也不可能伤害美国在伊朗的利益”,这使得美国对霍梅尼产生错觉,即他只想推翻巴列维国王,而不想与美国为敌。于是,卡特对巴列维镇压伊斯兰革命行动的态度开始变得暧昧。不仅如此,卡特还秘密派人设法与远在巴黎的霍梅尼联系,寻求双方的合作共同点。而时任法国总统德斯坦对霍梅尼与美国的秘密接触也是推波助澜。
霍梅尼指示正在进行街头革命的伊朗民众,不要对伊朗军队发难,尽量争取军队在反抗国王的斗争中保持中立甚至倒戈。这个策略发生了作用。在霍梅尼“甜言蜜语”的诱惑下,卡特开始阻止中情局策划的伊朗军队镇压伊斯兰革命,而对伊朗军队哗变、倒向霍梅尼的行动则听之任之。霍梅尼利用美国希望借助其反苏情绪遏制苏联的“小算盘”,使卡特在关键时刻没有力挺巴列维,放任军队倒戈。这是霍梅尼伊斯兰革命最终成功的因素之一。
“伊朗门”事件中的博弈
霍梅尼反对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基本意识形态决定了他在执政后必然强烈反美。但他为了伊斯兰革命胜利的大局,有时也会以退为进。这也是其政治智慧的体现——在原则问题上他从来没有让过步,同时很会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伊朗门”事件就反映了他的这种智慧。
1986年,黎巴嫩一家不起眼的杂志《船桅》周刊登载了一条新闻: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法兰曾于当年5月秘访德黑兰,同伊朗高层进行了接触,伊朗方面要求美国提供军火。随后,数架美国运输机给伊朗运送了战斗机零件和弹药。同一天晚上,时任伊朗议长拉夫桑贾尼突然宣布,麦克法兰曾秘访伊朗,时间是1986年5月28日。当时,麦克法兰带着4个人,装扮成机组人员,手持伪造的爱尔兰护照,乘一架载有武器零件的飞机抵达德黑兰国际机场。他带来了时任美国总统里根给伊朗领导人的亲笔信,信中要求改善美伊关系,要求伊朗帮助释放在黎巴嫩的美国人质。他还带来了几件礼物,其中有一本里根亲笔签名的圣经,一块象征美伊打开良好关系的钥匙形蛋糕,赠给伊朗官员的象征美国可以向伊朗提供武器的几把科特式手枪。拉夫桑贾尼声称,他下令将麦克法兰及其随从软禁在旅馆达5天,此后他们被驱逐出境。
事情要从两年前说起。1984年3月,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一等秘书、中情局贝鲁特站站长巴克利遭绑架。此后一年多内,又先后有6名美国人遭绑架,绑架者向美国政府提出了释放人质的3个条件,即释放1983年因参与袭击美国驻科威特大使馆而被抓的17名囚犯;要美国向以色列施加压力,释放被以色列和南黎巴嫩军关押的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人;提供贷款,开发南黎巴嫩。绑架者扬言,美国若不答应其条件,人质将被逐个处决。
里根一方面声称要作出强硬反应,一方面又绞尽脑汁寻求人质获释的途径。绑架者似乎不耐烦了,巴克利在囚禁一年后被杀。万般无奈的里根发现,要既不答应绑架者的条件又使人质获释,就只能与美国的冤家——伊朗打交道了。里根召集时任国务卿舒尔茨等人磋商,认为应该同伊朗谈判。而伊朗方面由于同伊拉克进行了6年战争,国库空虚,武器不足,在国际上孤立无援,也有与美国做交易的愿望。以议长拉夫桑贾尼为首的务实保守派也主张谈判。最高领袖霍梅尼虽然说过“如果我们走一步,大撒旦(指美国)就会走100步”的狠话,这次却同意了。
兴致勃勃的里根最后拍板:立即进行美伊秘密接触。其实,早在1985年初,里根就批准了一份由麦克法兰拟定的计划,通过以色列向伊朗供应武器和零部件,改善美伊关系,让伊朗帮助释放美国人质,以色列自告奋勇地承担了掮客的角色。“摩萨德”特务、军火商尼姆罗迪作为美国的代表,同伊朗实业家古尔巴尼萨尔商谈具体交易办法。1986年5月,麦克法兰亲赴德黑兰,达成交易。当年9月,以色列先后两次租用DC—8型运输机,满载“陶”式反坦克导弹、飞机零部件和弹药飞抵德黑兰,随后美国人质本杰明·韦尔获释。此后,美国人两次给伊朗运送军火,换回人质詹森、雅各布森。据美国参议员邦伯斯估计,美伊军火秘密交易总额达1亿美元以上。最终,美国人质全部获释。
但是,此事后来被媒体曝光,称为“伊朗门”。里根不得不多次向国会和公众“忏悔”,政治声望也大受影响。作为其马前卒的麦克法兰,更不得不充当替罪羊角色,在1989年被判处两年缓刑、2万美元罚款和200小时的无偿公共服务。
可以看出,霍梅尼与美国的斗法,伊朗都占了便宜。但如今,伊朗官方和学界对这些事矢口否认。有分析认为,这是因为伊朗民众将霍梅尼奉为神灵,他“永远正确”的形象已在伊朗深入人心。如果此时把他与美国“勾连”的一面展示给伊朗民众,既有损于霍梅尼的“真神”形象,也不利于其继任者哈梅内伊执行对美强硬的政策。因此,伊朗官方、军方、学术界、宗教界对此都讳莫如深。这都是出于在伊朗树立霍梅尼形象、执行对外政策和与美国斗争策略的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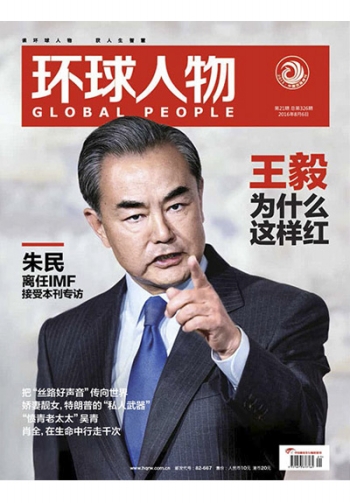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