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张赞波,1973年生,湖南邵阳人,2005年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硕士毕业。关注社会发展下的个体生存境遇,曾拍摄《天降》等。2015年出版《大路》及纪录片《大路朝天》,讲述高速公路建设背后的人生故事。
中伙铺是湖南怀化的一个村子,旧时北京到昆明的驿道从此经过;民国时,为了战事需要,修建了湘黔公路;2009年,穿越村子的溆怀高速公路开工。从那时起,中伙铺这个名字就和张赞波联系在一起了,他在此“潜伏”3年,拍下了这条公路背后的利益纠葛、人情冷暖。“从古驿道、水路、公路到铁路,再到高速公路,时代的步伐匆匆向前,一定有什么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见到张赞波,是在北京798园区的一家咖啡厅,落座,要了一杯水。他清秀谦和,有一种纯真和悲悯,偶尔也会昂扬激越。“刚从工地回来时,我还不太适应,因为已经习惯了那种生活……”
高速公路上的人造风景
张赞波的老家在湖南邵阳一个贫困山区,交通状况非常差,出行几乎只有坑坑洼洼的土路。直到1994年他到湘潭大学读书时,湖南省连一条高速公路都没有。在张赞波的想象里,高速公路应该是一条自身携有动力的道路——类似电力传输带,汽车开上去,车也走,路(传输带)也走。
大一暑假时,张赞波和同学到深圳打工。当时,梅林到观澜的高速公路通车,离他们的工厂不远,好奇的年轻人相约去参观。20岁的他这才知道原来高速公路并没有传输带,还因为自己的无知红了脸。
也是那一年,他的“发小”斌和到了湖南双峰县一个叫做“青树坪”的地方,成了一名普通的道路施工员。3年筑路生活,斌和写在了字里行间:“黑蚊子轰然之声盖过法国幻影F1战斗机”,“我的工作是管一台柴油机,一台搅拌机,一个是轰隆隆之物,一个是庞庞然之物。机械修理,加水加油,很单调的生活”。
尔后,张赞波也大学毕业,成为长沙电信局的一名员工,工作稳定,待遇也不错。但这个追求自由的人终究无法安于琐碎庸常,2001年,他考到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
2003年冬天,张赞波和斌和相遇在“路”上——他第一次真正走进斌和所在的位于湘西凤凰的工地。遍地废墟,一片尘埃,灰头土脸的民工正弯腰敲敲打打,挖土机或压路机轰隆不息地工作着,一盏大功率灯泡驱散着黑暗,制造出新的人影幢幢……他用随身带的一台小DV,走马观花地拍下了这些“人造风景”。
毕业后,张赞波放弃了留校,辞了职,咬牙花3万块钱买了台摄像机,成立了只有一个人的工作室,拍起了纪录片。而斌和也经历了国营路桥公司的改制与下岗,继续在筑路行业摸爬滚打。
个人命运会在时代裹挟和自主选择中转个弯,道路却一直在向前,向前。2008年,中国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数超过6万公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高速公路规划网正在紧锣密鼓地编织,计划把人口超过20万的城市和所有铁路、民航、水路交通枢纽、重要对外口岸连接起来,强力推进现代化进程,世界再次惊叹“中国速度”。
代表着“中国速度”的高速公路建设背后,一条路是如何筑成的?筑路的人是谁,他们来自哪儿又去向哪儿?这条路如何穿过了一家人的院落和菜地,为当地人带来了什么又带走了什么?依附于普通公路生存的人与新生的高速公路之间又有着怎样的纠葛与碰撞?……一条路不仅仅是一条路,它就像速度、发展、现代化的触手,伸进了广袤大地上的最细微的肌理与血脉,裂变正在发生,每个人的命运因它而改变。
这样的思考让张赞波和斌和第三次相遇在“路”上,前者要拍一部关于高速公路的纪录片,斌和把他介绍到了溆怀高速公路第十四合同段项目部。2010年3月,一个小伙子出现在中伙铺,此时,他不叫张赞波,而叫张赞。除了不领工资、不用上班打卡、手中多了个摄像机,他和工地上的人没什么不同。这个张赞性格随和,有时少见多怪,喜欢看热闹,喜欢追问和倾听。
施害者和受害者
“潜伏”工地3年,张赞波的镜头里有路桥公司职工、修路农民工、包工头、工程监理、当地村民与基层官员等,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斑斓而复杂的世界。
老何带着20多人的挖桩队来到了工地,住在比邻猪圈的工棚里。谁知这里地质结构复杂,已经有两拨挖桩队知难而退,老何进展非常缓慢,他不得不讨价还价甚至威胁,包工头龙老板终于同意加钱。但坏运气依旧没有结束,儿子小何差点被溶洞涌出的流泥淹没;工棚被盗证件丢失;因为工程进展缓慢老何的工钱被扣下了;小何一气之下和几个年轻人走了,队伍四分五裂;和他搭档干活的老姜在井下被石头砸断了一根肋骨,这让老何非常自责。
60多岁的民工老朱被同屋的年轻工友打断了两根肋骨,在包工头罗老板补发了3个月的工资后,悄然离开了。
工地上没有娱乐,除了看电视,就是打牌——老总和民工的区别只在于点数的大小;雄性荷尔蒙高亢的男人们聊着桥头堡“红灯区”,因为一场马戏演出没有预期中的“特殊节目”而失望。
在检查施工质量时,与项目部一向和睦的黄监理大发雷霆,被毛总拉到小屋子谈话,然后笑盈盈走出来,上车一溜烟去了县城找乐子。更大的领导来视察,对施工人员不按规定操作大加斥责,一番公关后事情不了了之。项目部的人一语道破:“他们总是习惯于用人民币去擦屁股。”
留云寺被迫为修路腾地,菩萨被临时放在防雨布搭的窝棚,只有唐老师——有着珍爱传统、愤世嫉俗的文人本性,又肯躬身世事——为寺庙搬迁重建跑前跑后。
欧婆婆一贫如洗的老房子被爆破的飞石砸得千疮百孔,她的哭声被一声声爆炸声所淹没。即便小儿子回来后,也无法拿到建房子的赔偿款,只能暂时住在破烂的窝棚里。而从事爆破的民工完全暴露在漫天飞尘中,就像白头发白胡子的圣诞老人,他们几乎没人听说过尘肺病。
在征地过程中,保护鱼塘的“刁民”欧疤子在“联合执法”时气焰全无,还给警察抓了一条四五斤重的大草鱼;挖桩队施工时破坏了地下水系,喇坪村没了水源,3个月解决问题的承诺没有兑现,村民们愤怒了,项目部的孟总被村民打倒在地。
一个村支书想从项目部承揽一些工程不得,又想要1吨水泥和河沙,包工头做不了主,只好送去400元钱让他自己去买,“没办法,他是地头蛇,我可不能得罪他。”
依附于省道的县公路局执法大队找人把项目部的人砍了——在更深层次,这是由于高速公路修建引发了利益的转移与重新分配。最终,私了了,留下的唯一印记体现在支出表上:被砍伤民工的名字、赔款数字以及一个个红色指纹。
在这些围绕高速公路展开的冷暖故事中,底层小人物是张赞波关注的。“我自己就是底层,我所拍摄的对象,只能是和我呼吸相通、患难与共、悲喜相连的人。”有时候,这种患难与共的感觉,让张赞波愤怒得想从摄像机背后跳出来,从记录者变成一名参与者。
村里有棵100多年的古樟树,主人房子拆迁了暂时住到了别处,绿化公司的大背头老总却让人把树挖出来,想卖到城里大赚一笔。树主人知道后,非常气愤,两人理论起来,大背头仗着势更是嚣张:“你再推我一下,我喊他们打死你”,“我今天要是将你打死在这,我赔你几十万就是了”。张赞波说,这一幕他至今想来都很愤怒,“当时我都不想拍了,特别想冲过去,但还是忍住了,因为用摄像机记录下这一幕会更有价值。”
然而社会与人性的复杂,并不浅尝辄止于底层、同情这些词汇。就像张赞波说的,“在一个并不尊重个人权益和尊严的环境里,并没有幸存者。”当项目部的毛总低三下四给监理说好话的时候,当孟总被村民打了的时候,他们权益和尊严同样没有保证。施害者和受害者也不过是相对的,就像项目部的狗黑皮,也是底层暴戾的受害者。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实习施工员,喜欢将夹文件的铁夹子夹在黑皮的尾巴上或脚上,看着它在办公室里痛得嗷嗷乱窜,便和一群围观者哈哈大笑。
有自尊地活着很难
2013年12月30日,溆怀高速公路正式通车。这条道路经历了2009年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2011年湖南高速系统“塌方式”腐败,此时受到八项规定影响,相比4年前繁冗而铺张的开工仪式,通车仪式仅仅两分钟就结束了。张赞波坐着朋友的车,穿过收费站,进入高速公路——这条路的前世过往,让他体会到与之相连的卑微人生和悲喜故事,也寄托了他对现代化、高速发展的观察与思考。
当发展成为时代的第一主旋律,当整个世界沉迷于速度之恋时,问题随即而来。发展一定要经历阵痛吗?张赞波觉得,发展带来的阵痛有些难以避免,但会有程度深浅的问题。普通人可以有尊严地生活吗?他说很难。在世俗意义上,张赞波称自己是一个失败者,租房子,没有固定收入,初恋女友是同学里最早的副处级干部,但再也聊不到一起去了。何谓现代化,就是到处都是高速公路和高楼大厦,人人都用上4G手机、在APP上购物?张赞波给出的答案是:只有将人当做人,一切器物都是为人服务,才具备走向现代化的基础。
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正滚滚向前,这是一条更漫长、更宽广、更有力的道路。没有人能置身其外,和这条大路背道而驰,或逃脱它制定的轨迹、方向和速度。作为记录者的张赞波也是如此。人和时光,都在这条路上,永不停息。
瓦斯菲,一人一琴慰藉一座城
他两度从美国回到战乱中的巴格达,在恐怖袭击废墟上演出
□ 本刊记者 余驰疆
人物简介
卡里姆?瓦斯菲,1972年生于巴格达,伊拉克国家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他在恐怖袭击后的演奏通过网络传遍全世界。
巴格达,这座千年古都在历经战火后又被恐怖袭击的噩梦笼罩,几乎每个月都要遭受几次炸弹袭击,人心惶惶。每次袭击过后,总有一个人身穿礼服,独自在碎瓦颓垣中演奏大提琴,他就是卡里姆?瓦斯菲。
瓦斯菲的第一次露天独奏是2015年4月29日早上,巴格达曼苏尔区的一条街道上——前一晚这里遭遇了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的炸弹袭击,10人身亡。瓦斯菲搬来一把木椅,坐定后开始演奏自创的《巴格达的悲伤》。躲在屋里的人陆续走到街上,一名残疾人哭着做起了祷告,警察抹着泪,夫妻亲吻着,开车的人也停下聆听……这些场景被瓦斯菲的好友阿马尔拍下并传至YouTube,一周的点击量就超过了10万。从此,炸后独奏成了瓦斯菲的常规演出,他称之为“和平之乐”,“当城市一片荒芜,我们的心灵就必须丰富。我希望音乐能让人们感到心有所依。”
音乐在野蛮中发出高尚的光
瓦斯菲的视频在网络上传开后,评论两极分化:有人称他战火中坚守灵魂的艺术家;有人则认为他只是为了出名,早日离开伊拉克。瓦斯菲不以为意:“我不是突然要做这件事情,也不是为了博取眼球。”
事实上,瓦斯菲完全有机会逃离伊拉克的战火。他出生于巴格达一个上流阶层家庭,父亲是伊拉克著名演员,母亲则是埃及裔钢琴师,从小浸润在艺术中的瓦斯菲6岁就开始学习大提琴。
1985年,年仅13岁的瓦斯菲就加入了中东三大交响乐团之首的伊拉克国家交响乐团。时值两伊战争,伊拉克从高歌猛进转为被动状态,国民内心充满恐惧。瓦斯菲以为人们会变得胆小,不愿出门,事实却截然相反:来听交响乐的人反而更多。年少的他意识到,音乐是最好的镇定剂,有时比粮食和水还要有用。
瓦斯菲非常崇拜美籍匈牙利裔著名大提琴家亚诺什?斯塔克,20岁那年考入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成为斯塔克的门生。
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此时,拥有美国国籍的瓦斯菲决定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回到巴格达,担任伊拉克国家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他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利用在美国的关系,带乐团前往美国肯尼迪中心演出,那场音乐会由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亲自担任主持。
与两伊战争的边境战不同,伊拉克战争一开始,巴格达等城市就遭到美军空袭。等到瓦斯菲等人回到巴格达,乐团的音乐厅已经被夷为平地。没有了栖息地,瓦斯菲只能带着乐团到处流浪,在战火中排练,借酒店的会场、学校的礼堂演出。瓦斯菲曾回忆那段时光:“我们几乎每天都要经历轰炸、停电、疏散,但我们始终相信,即便在野蛮中,音乐也会发出高尚的光。”
苦难的伊拉克,灾祸不休。2007年,IS组织开始袭击巴格达,瓦斯菲的公寓在一次汽车爆炸中被炸毁,他不得不与妻女离开伊拉克,前往美国。正当所有人以为他会和妻女一起留在美国时,瓦斯菲却选择独自回到故乡——恐怖袭击下的巴格达。
恐怖袭击下的交响乐团
瓦斯菲曾列出过一个清单,记录下在IS恐怖袭击下乐团碰到的困难:团员减少,乐器急缺,曲谱在战乱中遗失……但最麻烦的还是越来越危险的外部环境。事实上,在巴格达,手里拿一件西洋乐器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因此瓦斯菲的团员只能将乐器藏起来,排练时再偷偷带出家门。2009年,巴格达市府大楼遭袭,一枚汽车炸弹炸毁了市府80%的建筑。当时,瓦斯菲正带着乐团在同一条街的礼堂排练,顷刻间,窗户玻璃被震碎,一堵墙倒塌了。他们花了两天时间重新整理了礼堂,迎接即将到来的音乐会。为保证安全,每次音乐会开始前两天,政府军要全面搜查场地;演出当晚,观众必须把车停在很远的地方步行而来,然后经过层层安检才能入席。
尽管如此,音乐会还是场场爆满。一方面是因为受到伊拉克政府资助,乐团一年20多场音乐会,都是免费;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战乱中的巴格达人实在是太需要精神的抚慰了。渐渐地,交响乐团的音乐会成为巴格达全民保护的对象。2010年5月,瓦斯菲邀请13岁的美国钢琴天才勒维林?沃纳来演出,巴格达市长派出了自己的亲兵卫队保护沃纳。
2014年,IS组织在全球范围内的恐怖活动变本加厉,巴格达更是笼罩着死亡的气息,全年共有319位市民在恐怖袭击中丧生。在不得不减少音乐会场次的情况下,瓦斯菲决定一个人为城市演奏。从2015年4月至今,只要是巴格达城内发生了爆炸,几小时后就能听到他的大提琴声。
瓦斯菲独奏视频上传后不久,视频拍摄者、瓦斯菲的好友阿马尔就在一次恐怖袭击中丧生了。一个小时后,瓦斯菲出现在事发地,身穿一套白色西装,头发一丝不乱,为好友演奏了《E小调大提琴协奏曲》,这首曲子又被称作“战争安魂曲”。
移动的音乐教室
一琴、一椅、一人,便能慰藉一座城。对于巴格达人来说,瓦斯菲不是简单的街头表演者,而是废墟上的一朵花,黑夜里的一束光,代表着希望。在瓦斯菲的聆听者中,有一位名叫穆斯塔法的18岁少年。当时,他正盯着路上的弹坑,对时刻可能到来的袭击忧心不已。然而,当他看到西装笔挺的瓦斯菲在爆炸残骸前演奏,深受鼓舞。很快,他加入了瓦斯菲所在的交响乐团的艺术中心,学习唱歌和小提琴,“瓦斯菲让我看到,尽管恐怖分子用爆炸威胁我们,但音乐可以成为我们回击的武器。”
除了在废墟上演奏,瓦斯菲还会去清真寺为流离失所的孩子们演奏、讲课。“IS夺去了他们的家,53个孩子蜗居在一座清真寺里。除了坦克和战争宣言,他们一无所知。”瓦斯菲为孩子们演奏《巴赫大提琴组曲》,组曲由6段独奏组成,分别象征着明亮、悲伤、辉煌、庄严、黑暗与阳光,是巴格达历史的最好写照。一开始,孩子们只是争先恐后地摸琴、吵闹,随着瓦斯菲的深入讲解,孩子们开始静下心来,欣赏音乐。“战争可以摧毁城市,但难以摧毁人的心灵。越是危急的时刻,越要向下一代灌输美好的思想。”瓦斯菲说。
他的身后,是残破不堪的巴格达街道;他的眼前,是无休无止的恐怖战争。某种意义上,他是巴格达城中的另一种战士,以音乐为盾,守卫着精神的世界。
何须转型,只要成长
□ 罗振宇(著名媒体人)
很多年前我失恋了,去香山坐缆车。只有我一个人坐,车到半山腰狂风大作,觉得命就要扔在那里了,我发誓我能安全下山就好好做人。当然下山后该怎样还是怎样。我们的人生需要失恋坐缆车这种特殊时刻。
所有动物都有三种情绪:愉悦、恐惧、愤怒。人又多了爱、恨和忧伤,因为多了时间的尺度,人要是没有时间的尺度,爱不起来、也恨不起来,时间的维度开掘得越深,属于人性的光辉就越灿烂。
2015年发生了很多事情,董明珠给股东100多个亿,没人知道,但是刘强东生孩子,全国都知道;王健林去年的资本拼命往海外铺,没人知道,他的公子发微博,天下皆知……我们看到最热闹的新闻未必是这个世界的真相。2015年舞台上大人物表演的剧情,给这个时代构建的商业文明留下了什么?就像看待人的爱、恨和忧伤,看这些时同样要融入时间的尺度。
我想讲讲所谓的“互联网恐慌”。互联网像一个幽灵在中国徘徊了非常多年,2015年达到恐慌,不少企业家甘愿投入所有的身家去转型,我认为这就到了不太理性的程度。很多人说马云太坏了,把线下生意都毁掉。可事实上,线上商业占所有商业不到5%,5%可以毁掉95%吗?去年腾讯一年赚200多亿,我朋友说还没有他们公司多,他是中国烟草公司的员工,去年他们赚了1700多亿。即使我们都在唱衰中国移动,它也有1000多亿的利润。
我们感知的互联网恐慌是一个事实吗?这让我想起我小时候的事,我5岁上学,在学校里我的同桌五大三粗,天天欺负我,我最不能忍受的就是他总是说下课要揍我。互联网就像那个五大三粗的家伙,它带来的恐慌就是给我们三个字:你等着。很多企业朋友都有这样的体会:它让我们等着。
那么,怎么看待2015年弥漫中国的互联网恐慌呢?可以用生物学思维理解商业,把时间要素带到思维中——像一个小虫子,站在每一个时间点上找到最佳的策略。如果带着这样的理解方式理解转型,我们的角度和结论就会不一样。
腾讯的马化腾算是站在食物链的顶端吧,他没有恐惧吗?他在内部演讲说,每一年他都感觉自己快要死了。不久前的乌镇大会,他已经在深度忧虑下一个替代微信的物种是什么。
达尔文在晚年的时候已经写出《物种起源》,但被一个东西折磨得死去活来,那就是孔雀的尾巴——一个不适合觅食又消耗大量能量的尾巴,不适合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他后来想,问题可能出在母孔雀身上,它们不愿和没尾巴的雄孔雀做爱,所以这个种类就绝种了——时间帮他找到了答案。
时间的因素一旦被带进思维,看问题就不一样了。庞大的侏罗纪的恐龙如今安在?可最原始的单细胞细菌、蟑螂小强现在都活得好好的,互联网恐慌值得恐慌吗?
中国人得互联网恐慌还有一个因素是不愿意离开温暖的体制。我一个纽约来的朋友说纽约的报纸也在倒闭,但是媒体没有像中国媒体行业末日来临的气氛,为什么?因为对美国媒体人来说,任何一个组织的解散不是从业者的失败,是组织的失败。人类已经创造了另外的资源整合方式,而且新媒体公司开出更多的薪水和期权,大家唱着歌、小跑着去就完了。
所有人都说转型之难,但是太过于夸大这个转型。2015年的转型之难和之前企业家的转型之难怎么能比?我的电脑里面永远留着柳传志最早办公室的照片,说难就去看看那张照片。
用时间的尺度、生物学的思维来思考今天的商业,得出的结论真不一样。我给出一个结论:何须转型,只要成长。
(本文为2015年12月31日罗振宇在北京水立方以“时间的朋友”为主题的跨年演讲,有删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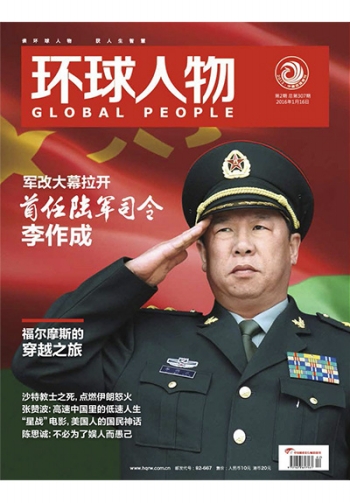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