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过后,薰衣草田结束了收割期,这意味着普罗旺斯闻香识色的时节渐行渐远了。没有了薰衣草和海滩烈日,很多人便把目光转向了更南边的西班牙,企图抓住夏天的尾巴。而也有人和我一样,反其道而行,在游客渐渐稀少的季节从巴黎来到普罗旺斯,不为薰衣草,不为乡野别墅,只为了安静地寻觅艺术大师梵高留下的足迹——在普罗旺斯大区的阿尔勒和圣雷米两座小城,梵高度过了人生最后的时光。
法国南部的阳光和星空,见证了梵高最潦倒又最辉煌的时刻。他在这里患上了精神病,却又因此灵感涌现,创作出了许多旷世名作。
那时的梵高,真是“不疯魔,不成活”。
消失的小黄屋
从巴黎坐高铁南下,4小时就能到达阿尔勒。一下火车,就能感受到强烈的南法气息。这里的房子大多刷着明黄漆,与巴黎冰冷的石灰色调反差鲜明。小城建于公元46年,被凯撒大帝指定为退休军人的定居城市,被誉为“高卢人的小罗马”。现在,这里仍保留着大约2000年前的古罗马城墙、竞技场和剧场。除了古迹,随处可见的还有梵高的画。几乎这里的每一条街都曾出现在梵高的画里,走着走着就能看见街边立着一幅梵高画作的复制品,提醒游客艺术大师曾在相同的位置作画。
我的第一站就是火车站边上,位于城北的拉马丁广场。广场很小,四周被黄色的矮房、咖啡馆和酒吧包围。从狭窄的小巷望出去,就能看见不远处穿城而过的罗讷河。我在广场上的一家纪念品店买到了那幅著名的《黄金屋》的明信片。画中一幢黄色的三层楼房,在深蓝的夜晚显得格外夺目。那是1888年,35岁的梵高初到阿尔勒时,在拉马丁广场2号的住所,又被称为“诞生了无数名作的小黄屋”。
在搬进小黄屋之前,梵高还是个半路出家的落魄画家。一直到27岁,他还在辗转于各个文艺公司做店员,但他的心思完全都在艺术和宗教上。1880年,在多次被解雇后,他干脆不工作了,开始进行艺术创作。他浪迹于安特卫普、伦敦等城市,学习文学和艺术;又前往布鲁塞尔学习透视学、解剖学;在巴黎,他开始接触强调光色、风格明亮的印象派。然而,梵高始终怀才不遇,生活穷困潦倒,只能一直靠画商弟弟提奥接济。当有人嘲讽他连一幅画也没卖出时,他回击道:“艺术难道为着‘卖’?我认为艺术家指的是一些始终在寻求,但未必有所收获的人。”
搬到阿尔勒是印象派大师塞尚给梵高的建议,他认为阿尔勒的阳光和古城韵味很适合艺术家寻找灵感。果然,惬意的南法生活大大激发了梵高的创作欲望,他开始脱离印象派追求意境的套路,在画中加入大量细节:他摘了大量向日葵装饰房间,创作出了《向日葵》系列;在城南的运河边,他找到了与家乡荷兰一样的田园风光,画下了《阿尔勒吊桥》,这座木质吊桥至今仍横跨在运河上;在市中心费洛姆广场的咖啡馆外,他用夸张的配色描绘出街灯和星空下的露天咖啡馆,画出了经典之作——《夜晚的咖啡馆》。这间咖啡馆曾毁于战火,之后又根据梵高画作复建,现在仍保留着当年黄色的外棚、座椅,每天都门庭若市。在阿尔勒生活不到一年,梵高创作了近百幅作品,数量超过了他之前的总和。
我绕着拉马丁广场寻找让梵高灵感如泉涌的小黄屋,但走遍广场四周,怎么也寻觅不到。这时,一位当地的老人告诉我,广场北面就是小黄屋的所在地,但因道路整修已经拆除了近百年。他的口气中带着些遗憾:“如果小黄屋没有被拆掉,它将会是法国除卢浮宫外最有艺术价值的景点。”
如今在小黄屋的原址上,建起一幢米黄色的三层楼房,是一间名叫“梵高的终点”的旅馆,门口墙上挂着梵高的肖像,以及那朵著名的“向日葵”。
割下耳朵送给妓女
小黄屋激发了梵高的才华,而市中心的精神病疗养院则见证了他的疯狂。来到阿尔勒不久后,梵高的精神状态就陷入了失常。他的脾气变得暴躁,生活不能自理,阿尔勒的居民形容他“面貌丑陋、粗俗无礼,让人心生厌恶”。他很快遭到了市民的排挤,连小孩子都拿石子儿砸他。后来,一名叫雷·加歇的好心医生帮助了他,不仅让他来疗养院治疗,还鼓励他继续创作。为了表达感激,梵高送了医生一幅画像,医生的家人却把画放进了鸡窝做挡板。梵高成名后,医生的家人又从鸡窝里找到了这张画,意外获得了高额的收益。
二战后,疗养院被改建为梵高艺术中心,摆满了梵高的画作复制品。院中最著名的是一座方形花园,曾出现在梵高的《阿尔勒疗养院花园》中。在画里,树木、池水都呈现一种冷清色调,但我眼前的花园,种满了五颜六色的花朵,还有一个终日不停的小喷泉。讲解员告诉我,两个原因形成了这种差异:一是梵高创作这幅画是在1889年4月,春寒料峭;二是当时在医院里,梵高必须穿着沉重的紧身衣,不允许自由出入、擅自聊天,他的画就像心情一样阴郁。
走进医院内部,白色的逼仄楼道上挂满了梵高的作品,其中有一件吸引了我的目光。这幅画名叫《梵高割耳自画像》,画中梵高穿着军绿色大衣,戴着蓝色冬帽,神情恍惚,耳朵上还缠着绷带,与他那些正装笔挺的自画像截然不同。
画的旁边,有一段介绍文字,详细讲述了关于这幅画的疯狂故事。1888年10月,梵高在阿尔勒迎来了自己的贵客——画家高更。高更比梵高大5岁,他们相识于巴黎嘈杂热闹的文化沙龙。正是在梵高的建议下,高更也来到阿尔勒,两人在小黄屋里一起创作。梵高为人内向,但画风自由、热情;高更能说会道,作画时却像温柔的女子,技法细腻。性格互补的两人互相学习切磋,度过了两个月的“蜜月期”,共同完成了《阿尔勒舞厅》等名作。
然而,随着梵高病情的反复,两人的关系也陷入僵局。1888年12月的一天,两人又一次爆发激烈争吵。情绪失控中,梵高割下了左耳,把它装进信封寄给了一位相识的妓女。之后又画了几幅割耳自画像。
这次争吵后,高更就离开了法国南部。
孤独的天才
在阿尔勒,梵高完成了《向日葵》等作品,突破了印象派的老套路。但他真正形成“梵高特色”,却是在25公里以外的圣雷米镇。这是一座宗教氛围浓厚的小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它还是小说《达·芬奇密码》中提到的郇(音同寻)山隐修会(保护耶稣后人的神秘组织)的基地之一;也是在《诸世纪》中准确预言法国大革命、美国崛起等历史事件的伟大预言家诺查丹玛斯的家乡。但这座小镇最著名的,还是梵高住过的圣保罗修道院。
我到圣雷米小镇时,已经是中午时分。镇中心的大道两旁种满法国梧桐,旧城巷弄里藏着欧式的传统市集,空气中还带着点薰衣草精油的香味。从镇中心向南走40多分钟,就到了圣保罗修道院,如今已改建为梵高博物馆,里面有一些陈列室,包括梵高住的房间。房间里只有一张老床和一组桌椅,据说,当年梵高割耳的行为吓坏了阿尔勒居民,他们联名上书请求当地政府对他进行隔离,梵高被接到圣保罗修道院,就关在这个房间进行治疗。
房间外拱廊大门的花墙上,悬挂着梵高最著名的作品——《星空》的复制品。在正午的阳光下,我微眯着眼睛,欣赏着这幅名作:深沉的蓝色夜空,火舌般的黑色柏树,漩涡样的星辰,昏黄的月亮,变了形的圣雷米教堂,整幅画透露着一种诡异的美感。这幅画诞生于梵高病情最为反复的一段时间。当时,他孤身一人在修道院里,唯一的资金支持和精神寄托就是弟弟提奥。他几乎每天给弟弟写一封信,信中经常提起自己如何节省,如何不糟蹋兄弟的钱——他太怕失去提奥了。
1889年,提奥向梵高透露了自己即将结婚的消息,这让梵高大受打击,他认为自己很可能会被弟弟抛弃。一方面,他写信向弟弟索取了更多的资金,不时倾诉着自己的孤独;同时,他创作和表达的欲望越发强烈,把思想一股脑地投注在自己的画作上,创作了《星空》《松柏》《圣雷米修道院与教堂》等150多幅作品。这些作品充满悲剧性幻觉,又不乏蓬勃的生命力,同时表现了对“生”的绝望和渴望。
1890年5月,梵高被弟弟接到了巴黎。两个月后,在巴黎北边的一片农田上,37岁的梵高把画架靠在干草堆旁,用一把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只留下900多幅无人问津的画作。世事沧桑难料,不足百年后,1987年《向日葵》以3990万美元售出,这位精神病画家成了世人眼中的旷世奇才。
大概是看了太多梵高的画作,以至于我离开修道院时,面对院外满眼的向日葵,竟觉得它们根本比不上画中的美丽。也许,梵高正是因为得了精神病,才得以看到我们普通人不能看到的美。如此看来,疯狂,是他的不幸,也是他的幸运。
而在阿尔勒和圣雷米度过的两年,对梵高而言,同样既是不幸,也是幸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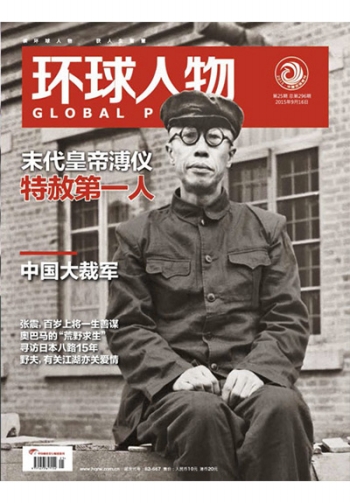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