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李洁,1957年出生,山东青岛人。历史学者,著有《百年独语》《文武北洋》《风流故居》。
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也是日俄战争结束110周年。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苦难深重,70年后不忘国仇家恨、缅怀历史,本就是炎黄儿女应担之义。然而,在东北境内生灵涂炭、晚清政府却说不上话的日俄战争,今天却似乎被人遗忘了。
历史本就是这样。虽是一幕接一幕环环相扣的戏,演过去久了,一些重要情节便被演绎、被包装,抑或被忽略、被改写。真相与细节,最终只能引起少数人的思索与注意。李洁就属于这些人之一。从去年6月开始,他一直在解读日俄战争。“我陷在这场战争里了”,李洁说。
与其说是关注历史,不如说是关注现在
李洁鲜少做公开讲座。4月3日在北京海淀区一家书店讲日俄战争,虽是清明假期前的最后一晚,厅内却座无虚席,且大多是年轻人——早在2004年,凭借一本《文武北洋》,李洁就成为读书圈中热捧的人物,迷住了不少校园学子。
他在微博上为自己写的标签是“曾经报人,冒充学人,终生旅人”。所谓“报人”,李洁上世纪80年代即调入青岛日报社,后参与创办《青岛晚报》,其实至今仍未离开单位,算不得“曾经”;至于“学人”,国内一些著名的史学家,如袁伟时、章立凡、雷颐、马勇等都对他的作品评价甚高,谈不上“冒充”;“旅人”倒是真的,他总不断地行走在路上。很多场合,李洁都强调自己不是学者,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作家,而只是一个期待在遗址上找寻和验证历史真相的旅者。靠着一辆车、一支笔,他四处驰骋,在现实与历史的世界里自如穿梭。
李洁从小喜爱文字。初中时,他就在报刊上发表作品,“当时是‘文革’,我写的都是一些应景的诗歌,现在看来,一无是处”。那时他无限崇拜鲁迅。高中毕业后下乡,他利用管理图书之便,把知青组里一堆鲁迅的书据为己有,天天诵读,至今还能背出不少句子。
“文革”结束后,李洁回到青岛,顶替母亲成为一家纺织厂的库工,每天除了搬运和清点出入库的产品之外,就是躲在狭小的更衣室里读书,直至1985年春他调入报社,从此开始了新闻生涯。
追求真相是新闻人的操守与准则,做历史研究时,李洁自动带入了这个理想。他对中国近现代史格外感兴趣,“历史是不能割裂的,我们今天遇到的所有问题,其实都能在100年前找到相应的源头,与其说是关注历史,不如说是关注现在。作为一个读书人,应该为你遇到的困境,找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
冲开覆盖在历史上的层层污秽和金粉
30多年一直业余读近代历史,李洁的感悟很多,思考也很多,落在纸上的却少,人们读到的只有《百年独语》《文武北洋》《风流故居》3本。他把作品少的原因归结为自己太“懒”。
虽然数量不多,李洁的作品却品美质优,尤其是《文武北洋》,10多年来一直未被读者遗忘。他写历史的方式很有意思,寻访故居、遗迹,看着现在的景致,追忆历史与人物。“游走这种写法,既是我兴致所在,也是一种有益的谋局。因为我不愿领着读者一直在历史的隧道里匍匐前行,我要不断地伸颈,到地面上透一透。此外,写当下的场景其实也是一种记录,能让读者知道这个时代的人对历史、文物的心态。”
《文武北洋》中写了段祺瑞。李洁曾说:“我对段祺瑞感兴趣其实是源于青岛的芝泉路。上世纪80年代前期,我就住在芝泉路上。青岛的路几乎全是用省、市名和本省的县名命名,但好像没听说有个叫芝泉的地方。后来看资料,得知段祺瑞曾为芝泉路附近的湛山寺帮忙化缘,我一下子想通了,一定是为了纪念这位北洋元老!因为段祺瑞,字芝泉。”这就是为历史找答案的乐趣所在,“就像爬山,爬得很困很累,一到山顶,忽然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李洁为这种感觉而痴迷。他不断地寻访、追查历史,每到一地,除了看老朋友,就是看老房子,还有古墓。“鸟不高飞啊,怎知蓝天之大?人不远行啊,怎知世界之阔?”少年时背诵过的知青诗句,一直在他脑中回荡。
但最初,李洁并不敢把所见所得写成文章。“上世纪80年代,整个社会对历史反思的容忍度还很有限。”1999年,新旧世纪之交,李洁终于吐出胸中言,写了《百年独语》。他用自己的话讲述晚清、民国、共和国的几位历史人物和事件。因为与主流历史面貌颇异,“好一个李鸿章”“陈独秀被忽略”等观点让人耳目一新。有朋友开玩笑说:“你这不是对百年历史的独语,而是‘毒’语。”
笔锋一开便难收住。这之后,李洁又一口气写了《文武北洋》《风流故居》两本书,正如他后来所写:“我试图用自己的文字冲开覆盖在历史上的层层污秽和金粉——总之,我是想尽量看清我感兴趣的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和体态,再通过他们,了解一下他们那个时代的真相。”
在李洁笔下,北洋时代并非一个颟顸武夫秉政、人文思想沦陷的时代,袁世凯、段祺瑞有弱点、缺陷,但也不是彻头彻尾的窃国贼、大军阀,袁世凯自有其骨气,段祺瑞也有其文采。段祺瑞的五世孙女段殳(音同书)读了李洁的书以后,说从来没有人这么公正地写过段。对这种“翻案”写法,李洁说:“每个历史人物本质上和你我一样,都是普通人。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生老病死和我们完全一样,你只要把他们还原成一个普通人,既不仰视他们,像一个雕像上的伟人;也不俯视他们,像泥坑里的蛤蟆。你会发现,他们做的事都是可以理解的。”
日俄战争是对中国知识精英的心灵震撼
日俄战争的讲座上,李洁事无巨细地讲述着,似乎当年战争中的每个关键人物、时间点、地名、舰船都深深地印刻在他的脑海中。他对历史细节尤其关注,“细节往往是最有力的证明,一个细节胜过10个空洞的大道理。滴水映日,用细节来折射大时代,这也算是一个事半功倍的写法吧。”
《环球人物》:您为了研究日俄战争,都去过什么地方?
李洁:去年我四次奔赴昔日的战地巡访。第一次去了当年俄军在旅顺的主要炮台和要塞;第二次也是去旅顺,寻访到日军第三军司令部驻地等;第三次沿着当年日俄两军几次大会战的路线走了一遍;第四次沿着日军第一军的进军路线走完全程。今年计划再到日本和俄罗斯去寻访。
《环球人物》:晚清以来100多年的历史一直是当代学者和公众关注的热点,但日俄战争却是热点中的盲点,为什么?
李洁:现在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上,从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一步就跳到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间缺失了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对日俄战争视而不见,与人们对清王朝的全盘否定有关。
《环球人物》:有人把日俄战争称为“第零次世界大战”,可以这么说吗?
李洁:是的。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战舰和威力最大的火炮都投入了战争,双方各自动员了几十万陆军对阵厮杀。海战、攻坚战、夜袭战、白刃战,都是战史上规模空前的,无不体现了当时最高的军事对抗水平。
从战争结果来说,沙俄从此一蹶不振,并很快结束了君权专制统治,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日本从此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加速了在军国主义道路上的迅跑,覆亡朝鲜,屯兵满洲,伺机发动更大规模的战争。这对中国、朝鲜半岛乃至当时东北亚各利益相关方,都影响深远。
《环球人物》:日俄战争之前,在近代史上黄种人没有打赢过白种人。日本人胜利的原因是什么?
李洁:用推翻了沙俄的布尔什维克领袖列宁的话说,就是“专制制度的俄国被立宪的日本击溃”。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性情像钟摆一样,摇摆不定,日本睦仁天皇则非常有主见。俄国政府三巨头:军政大臣、财政大臣、外交大臣都反对打这场战争。日本则从明治维新之后上下齐心,官员从自己俸禄中拿出钱来,合资为国家买军舰,因此君主对君主、大臣对大臣,俄国必输无疑。
《环球人物》:您提到这场战争对中国影响至深,都有什么影响?
李洁:没有日俄战争,就没有东三省的建省,也不会有同盟会在东京的成立;没有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关东军就没有资格在东三省驻军;没有东三省的驻军,就没有后来的伪满洲国,更没有侵华战争。
此外,这场战争对中国早期革命的仁人志士更是一次心灵上的震撼。满清的覆亡、国体的改变,其实都和这场战争大有关系。鲁迅看到日俄战争中的麻木中国人,弃医从文;秋瑾因为日俄战争发誓要“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甚至孙中山、黄兴、周恩来等的革命,都深受日本人影响。可以这么说,正是这场战争,集合起一代中国知识精英,他们受到立宪国家战胜了封建专制国家的事实激励,合力推翻大清王朝,创建了中华民国。
所以,读懂了日俄战争,就知道我们国家是何以走到今天的。今天我们研究历史、回望历史,最主要的目的仍是振兴我们自己的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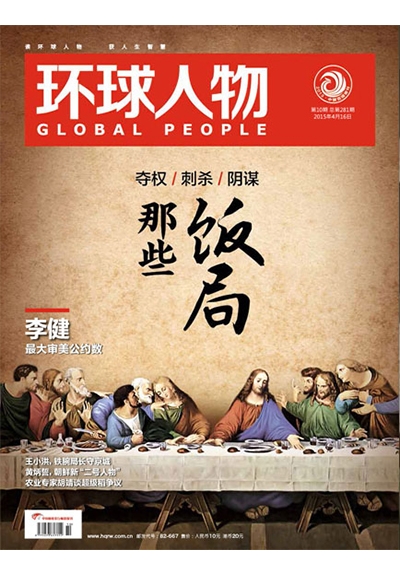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