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父亲隔绝了13年后,2008年11月7日,73岁的季承终于在301医院的病房见到了父亲季羡林。
“父亲!”季承一开口就跪下磕了个头,起身时已泣不成声。“您有什么要训斥我的吗?”
季羡林虽然也很激动,但话语仍然平静:“我有什么可批评呢,过去的事情就过去好了。” 此时,季羡林已经不能行走,终日困卧床上,视力衰减。老人能看到的,只是儿子模糊的身影。
季承带来了季老喜爱的家乡食品,亲手喂给父亲吃。经过13年的隔阂之后,季承又像普通的儿子一样回到了父亲的身边。
一个多月后,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季承红着眼圈回忆了当时的情景。“现在我们只想向前看,而我们能看到的日子,也不多了。”他感慨万千地说,记者的感情也不由地一同起伏跌宕。一段真实的父子之情逐渐还原出来。
迟来的天伦
国学大师季羡林生于1911年,按虚岁算,今年已经99岁了。2002年,他住进了301医院,之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里。
随着身体不断衰弱,季老渐渐失去了行动能力,大多数时间只能呆在15平方米的病房里,在床上或坐或卧,但只要手中有书,他就很满足。后来,季老的视力下降,连书也不能看了,只有靠别人为他读报,来了解每天的社会信息。
住院期间,只要有机会,季羡林就跟身边的人们开玩笑。有位教授来探望,临别时祝他长命百岁,季羡林笑笑说:“现在说这话就不合适了,我已经99岁,你得祝我多长几岁。”还有一次,访客要求与季羡林合影,快门按动前,他拦住了,“等一下,我得先把嘴巴闭起来。”有人问季老掉了多少颗牙,他马上接下去,“你应该问我还剩下几颗牙。”
然而,在定期给季老做口述历史笔录的蔡德贵眼中,季老其实并不开心。“他不能动,不能读书,身上有病痛,心里不痛快,但他只能默默忍耐。更重要的是,他见不到亲人,听不到家人的音讯,没有普通老人的天伦之乐。”蔡德贵1965年和季羡林相识至今,是季羡林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他告诉记者:“以前季老的座右铭是陶渊明的一句诗‘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2002年常住医院后,他的座右铭不知什么时候换成了‘为善最乐,能忍自安’”。
住院后,季羡林能见到的人十分有限,连亲属也不能接近他。秘书挡驾很严,既挡掉了季羡林不想见的人,也挡掉了他想见的人。闹得沸沸扬扬的“字画门”事件(编者注:2008年10月,有举报人称,季羡林家中的藏画被秘书盗卖。北大校方随即声明,藏品未曾外流,市场流通字画是假。事件进一步演化为财产纠纷,至今没有结果),反倒成了季老和外界联系的转折点,季承探望父亲也不再受限制。现在他通常下午4点去医院,带去妻子做的饭菜,陪父亲吃饭聊天,然后6点多离开。周末呆的时间会更久些。
“能和儿子见面,季老很高兴。”见过季承之后,蔡德贵明显感觉到季羡林情绪的变化。曾经有一段时间,季羡林的情绪起伏较大,经常提出要出院回家,见到季承后,情绪波动才逐渐平息。
病房里,父子二人尝试着敞开胸怀,吐露真心。13年来,他们从未这样亲近地交谈过,“我们现在可以像正常的父子那样谈话,这个结果我已经等了很久”。
一个被称作父亲的“陌生人”
季承对父亲的等待从襁褓中就已开始。季羡林1935年赴德国求学时,季承才3个月,姐姐季婉如刚满两岁。季羡林在德国呆了11年,季承没有机会见到父亲,“整个童年的成长,我脑子里没有父亲的概念。”
二战一开始,季羡林便中断了和家人的通信。战争结束后,尽管季羡林的导师帮他在剑桥大学谋得职位,但考虑到10年没有和妻儿见面,季羡林最终于1946年选择了回国。
消息传回季羡林的老家济南,季家上下忙碌,修整打扫房屋,给孩子们添置新衣,季承反复看了父亲的相片,以加深印象。季家老宅是济南常见的四合院,季羡林回来的当日,全家人站在堂屋门口,静静地等着他出现。
“气氛有点特别,大家都很期待地盯着门口。”季承笑了起来,“然后就看到一个男人从大门口处转了过来。有人跟我说‘这就是你爹’。”
身边有了父亲后,季承并没有感到生活有多大变化,多数时候,他只是觉得屋子里多了一个需要称作父亲的“陌生人”。“我们一直很客气,不太容易交流感情。可以说,童年那十几年的隔绝,影响了我们一生的父子关系。如果我一直在他身边长大,很可能和现在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季羡林在家中呆了不久,就又离别家人,孤身到北大任职。季承和父亲只有寒暑两个假期才能见面。
1952年,17岁的季承来到北京俄文专修学校(今北京外国语大学)读书。住校期间,差不多每个星期他都会骑上自行车去中关村,跟父亲一起吃顿饭。“谈论的都是国家大事,话题从不会涉及生活细节,我在学习、工作中遇到困难和挫折,从不会告诉父亲。在天津大学读书的姐姐也一样。”
父亲有自己的感情表达方式
1955年,季承毕业后分配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作翻译,两年后,转行从事科研管理。1962年,季承把母亲和叔祖母从济南接到北京。“我的叔祖母很尊重父亲,母亲干脆就是服从,所以,她们有什么话也不会随便跟父亲讲。父亲也从不主动问。”一家人再次团圆后,这是季承对父亲的最初印象。
渐渐地,季羡林开始体会到家人带来的温暖。季承对记者说:“家庭生活使父亲跟我们亲近了许多,大家的话题多了起来。”
感情的增进也使季承对季羡林原来的生活多了一层理解。“父亲很看重自己的精神世界,读书治学是他最重要的生活,对其他事情不是很在意。”
不幸的是,从1989年到1995年,季羡林的叔母、妻子、女儿相继离世,虽然内心沉痛不已,但他却以更加努力做学问的方式来排遣自己的感情。“父亲是学者,对生死已经看得通透,有自己一套感情的表达方式。这几年间的事情,父亲都看到眼里,有时问我一声姐姐怎么样,我说不好,他就不吭声了,一头又扎进图书馆去编唐史。”
季羡林外表看似与亲人之间感情封闭,其实内心饱受痛苦的煎熬。那些寄托深情的文字,读来感人肺腑。“夜里梦到母亲,我哭着醒来。醒来再想捉往这梦的时候,梦却早已不知飞到什么地方去了。眼前剩下的就只有母亲依稀的身影……”(引自《忆往述怀》,季羡林著)
生活中除了学问之外,季羡林最爱的事情就是养猫。读书之余,季羡林跟爱猫们亲密无间,小猫跟着他在燕园里散步的情景更是传为美谈。
浪漫的场景后面也有隐情。心境低落时,季羡林曾经写过一首词:“夜阑人静,虚室凄清。万籁俱寂,独有孤灯。往事如潮,汹涌绕缭。伴我寥寥,惟有一猫。”对这首词,季承难以释怀。“为什么猫可以伴你长夜,家人却不能?你可以对猫那么亲,对家人却不能?其实我也知道,他宠猫只是排遣感情的一种方式。”季承苦笑。
恩怨已经成过往
采访中,季承坦诚地讲述了父子之间的恩怨。“这里面有父亲的责任,有我的责任,也有其他人的责任。”季承说。略显犹豫之后,他对记者讲起了父母的婚姻。
“父母的结合不理想,是旧式的包办婚姻。他不得不接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种满意情绪一直延续下来。”
季羡林的妻子彭德华比他大4岁,只念过小学,认字不多。季羡林出国或是他们在国内分居两地时,彭德华没有给他写过一封信。但在打理季家日常生活上,她却勤勤恳恳,含辛茹苦。
对这样一位妻子,季羡林口头上评价颇高,情感上却又很平淡:“在道德方面,她可是超一流的。上对公婆,她真正尽上了孝道;下对子女,她真正做到了慈母应做的一切;中对丈夫,她绝对忠诚,绝对服从,绝对爱护。她是一个极为难得的孝顺媳妇,贤妻良母。如果中国将来要修《二十几史》,而其中又有什么‘妇女列传’或‘闺秀列传’的话,她应该榜上有名。”(引自《真情季羡林》,蔡德贵著)
在季承看来,父亲没有把这桩婚姻终止,是好事,但也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夫妻俩没有感情,维持下来,就有牺牲,有后果,这后果不仅影响到父亲和母亲,也影响了家里每一个人。”
长期的感情封闭,对事情的不同看法,日积月累,终于使父子矛盾激化。季承母亲病重时,父子二人分道扬镳,从此不来往,一隔就是13年。
季羡林最亲密的秘书李峥过世后,他的儿子李小军成了季承联系父亲的渠道。李小军眼里,季承和他的父亲一样,都有一股沉默的倔劲。每逢过年过节,季承都会往李小军家里送大量的山东斋菜,来了以后什么都不说。李小军自己家里留一部分,其余的便送给季老。季老心知肚明,只是沉默。
“开始时我们都僵着,后来我也想见他,他也想见我,但没有机会。现在最终见了面,往事该过去的就过去吧。”季承说。
如今,季羡林父子已都老了,“两人加起来170多岁”。重新寻回失落的父子亲情,也算得上余下岁月里,对他们最温暖的补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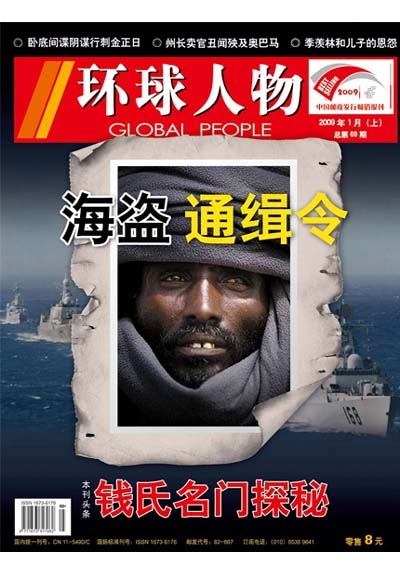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