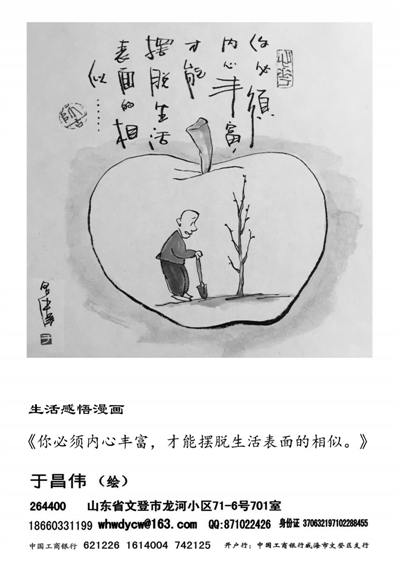我上的第一堂芭蕾舞课是在一个篮球场上。
我母亲是单身母亲,我是她6个孩子中的一个,我们面临着很多挑战——频繁搬家、更换学校,我变成了一个非常内向的孩子。我学会了闭上嘴巴,以避免其他孩子的批评。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能融入社会,我从未觉得自己属于哪里。
最初的几节芭蕾舞课也还是在篮球场上。
这门课是当地的学生俱乐部免费提供的,是为像我这样的孩子设计的——他们是各种各样的学生,否则他们可能没有机会或途径成为芭蕾舞世界的一部分。
我还记得,我一走进体育馆,走进篮球场,立刻就感觉很不自在。13岁的年龄,对芭蕾舞世界来说已经是老人了,而我来了,被推进到这个对我来说很陌生的课程,听着我从来没有听
过的音乐,而且有一位教练摆布着我的身体把它摆成不同的姿势。更不用说我是班上唯一一个没有穿连身紧身衣和芭蕾舞鞋的人,我穿着T恤、短裤和袜子。我还记得当时我是这样想的:“不,这不属于我,我不适合,我不属于这里。”
然而,一两个星期过后,我的教练老师给了我全额奖学金去她的学校接受训练。我母亲同意我去,于是我继父带我去当地的芭蕾舞用品店。我记得第一次穿上连身紧身衣时,立刻就感觉到它们像是我的第二层皮肤。它们很适合我,我也很适合它们,这就是我的归宿。
几年后,作为纽约美国芭蕾舞剧院的独舞演员,在《火鸟》芭蕾舞剧演出的那天晚上,我的一切都改变了。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晚上,那是一个差点就不会出现的夜晚,因为我把一个很严重的伤掩盖起来了,我知道如果艺术总监和理疗师知道我的疼痛的严重程度,他们就不会允许我去表演了。但我在大都会歌剧院演出的票都售罄了,而且我知道一半以上的观众都是黑人和有色人种,这在大都会歌剧院以前从未发生过。我知道他们中的许多人是第一次来。作为一个从来没有归属感的人,我知道那天晚上的演出对我有多么重要。我告诉自己:“即使这是我在舞台上表演的最后一晚,这也将会对芭
蕾舞界,对我在芭蕾舞界的群体产生巨大的影响。”
我记得,我那是第一次走上舞台,尽管我所看到的是一片黑色的海洋,但我能感受到那股能量。观众的欢呼声是那么响亮,持续时间是那么久,让我都听不到乐队演奏的声音了。我心想:“我不知道我是否对上音乐,但我要继续表演下去,看看会发生什么。”我从观众身上感受到的骄傲、爱和能量是显而易见的。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了。
这是我在那个大都会歌剧院演出季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演出《火鸟》。第二天,我告诉艺术总监我受伤了,一段时间后我接受了手术,几个月后我才恢复过来,回到舞台上。但这太值得了。
在《火鸟》演出的那个晚上我意识到,这不仅仅是我站在了舞台之上。这是我代表了所有那些没有机会做我所做的事情的了不起的黑人女性。是各个领域的黑人妇女为我铺平了道路,我才有机会站在这个舞台上。我现在知道了,我的目标不仅仅是跳芭蕾舞——这个曾经不敢说话的孩子,现在可以代表那许许多多的感觉没有归属感的人了。
(译注:米丝蒂·科普兰,MistyCopeland,美国有影响力的女性,著名的美国芭蕾舞剧院的第一位非洲裔首席舞者。)
(题有改动)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