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管理公司在打包出售不良债权后,债权买受方在追诉债权时,再次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而且更具隐蔽性和“合法性”。随着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加快处理国有商业银行剥离的不良债权,新一轮国有资产流失或将就此展开。
国企很受伤
近年来,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债权而“一案暴富”的问题引起广泛关注。国有商业银行在改制过程中,将不良贷款债权转给资产管理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再以极低的价格进行二次转让。购买者为实现债权,多以原告身份向法院提起诉讼。由于贷款都有担保,按现行法律裁判,原告极易胜诉。而且许多人从资产管理公司购买债权,其根本目的就是在投机,只是为了以小博大赚取利益,这已经成了获取暴利的快捷方式之一。
除了将部分债权推向社会公开拍卖外,资产管理公司也出现了直接起诉强硬讨债的情况。据报道,2005年10月,某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向法院起诉,要求四家国企偿还总额为8095万元的贷款。同时被起诉的还有这些欠款企业的担保方。在随后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的判决中,裁定冻结上述贷款及担保企业的银行存款,如存款不足则查封相应价值的财产。事实上,上述企业所欠贷款是2004年6月由交通银行沈阳分行协议转让给某资产管理公司的,这些贷款是企业未改制前的存量贷款,转让价格为债务总额的50%,而资产管理公司在受让上述企业债权后却要求全额还款。
对于部分国有企业与资产管理公司或其它不良债权的买受方的债务纠葛,有专家认为:国企改制前形成债务的原因错综复杂,有的甚至是由于当时政企不分被上级政府要求相互借贷担保才背上的债务负担。“资产管理公司当初从银行手中以相对低廉的价格接管企业债权,也是为了减少银行不良贷款、解决国企脱困,而现在不考虑政策背景和债务形成原因,完全用‘市场化’的手段去解决过去遗留的债务问题,只会使国企改革问题更加复杂”。
笔者也曾亲历一个案例:1999年由于政府部门出面,北京一家国企集团为某公司1800万元贷款进行了担保。2000年该公司无力偿还贷款,加上经营管理不善而倒闭。银行遂起诉担保方,要求承担连带责任,然而,担保方亦无力偿还。银行随即将此贷款剥离至某资产管理公司。此后,该笔债权又经6次转让,最后,由一家民营企业以极低的价格受让了这笔债权,连本带息滚至4300余万元。随后这家民营企业通过法院将担保方,即北京某国企集团用于发工资和缴纳社会保险的4300万元资金冻结并执行。顷刻间该国企资金链断裂。6400名职工的工资、保险停发,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严重受挫,企业岌岌可危随即被托管。该案给企业造成的危害和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是,对国有企业改制前的贷款,特别是对已经进行过资产剥离、处理并经过多次打包转让的债权,一定要考虑发生的背景和债权处理过程中看似“合法”,实质“非法”的问题本质。由于体制政策等多方面的原因,很多情况下,国企贷款和担保行为是不得已而为之,司法部门在执行上更应考虑社会成本。
从众多案例可以看出,很多不良资产经过二次或多次转卖后,国有资产确实存在流失的问题,甚至危害我国的产业安全。究其原因,在于国有资产管理和立法上存在漏洞,没有结合国企的历史背景制定相应的保护和扶持政策。自1999年国家组成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以来,与不良资产处置相关的法律依据虽有若干,但多为框架性条文,缺少不良资产处置切实可行的操作规范和监督体系。按照现有法律和政策,受让金融债权的企业或个人,只要通过法律途径追讨金融债权肯定会赢。这样的金融债权转让,等于给国有资产的再度流失穿上了合法外衣。
处理不良资产不能“一卖了之”
目前,在资产处置打包出售的过程中,由于操作程序不规范、资产评估缺乏可信性,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如某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将7家债权总额达5900多万元的不良资产打包拍卖,仅以350万的价格成交,而根据后来调查的结果,仅7家债务方中的某公司被查封的13万平方米的土地价值就高达6700多万,该打包转让行为使得债权买受方仅从该公司一家就获利不下6350万。
更应该引起重视的是在资产处置过程中忽视社会成本,容易造成新的社会矛盾。由于拍卖、出售等方式都不可避免地造成企业经营困难,大量职工的下岗分流以及因此而引发的社会问题,均是不良资产处置过程中的社会成本。尤其在我国不良资产债务人多为老国企的情况下,如果操作不当就很有可能引发强烈的社会反应。此社会成本为隐性成本,往往不为资产管理公司所重视和考虑,但这却是决策机构不容忽视的一个成本。
一些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呼吁,处置不良资产存在的漏洞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对于国有企业不良资产的处置,更多的应该采用政府主导金融机构与企业合作处置的方式进行,以地方国有资产管理公司为处置平台,把不良资产的处置同国有企业的改制重组结合起来,增加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处置收益,减轻国有企业的债务负担,避免因“一卖了之”而引发企业破产、品牌流失、产业失守、职工下岗的负面影响。
对于资产管理公司折价出售债权,买受方返回头全额追索的问题,我们的司法机关在执行上是不是应该重新审视。既然是难以实现的不良债权,就是说这个债权已经不可能原价变现。但是,买受人却能从不良债权中赚取暴利,不能不让人匪夷所思。当初国家剥离难以实现的国有资产所付出的代价最终变成巨额利益让渡给他人,这是国有商业银行和国企付出的双重代价。
没有人能够否认国企的进步与贡献,国企承担了太多的痛苦与社会责任,国企同商业银行一样需要政府的特殊关爱,这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期政府必须付出的代价。特别是对国企大额担保产生的债务,一旦遭到强制执行,国企及其职工根本无法承受。所以对于国企某些历史遗留问题,可以从市场的角度找原因,但请不要以纯市场的方式解决。
笔者呼吁,资产管理公司在债权处理上,以及司法部门在执行上应该多从防止和减少国有资产流失的角度考虑问题,比如增强不良金融债权处置程序的透明度、协商减免债务、停止衍生利息、亦或设定限售条款,转让时规定买受方多长时间不得追诉,追债时不得高于买受价的多少,赋予债务人有优先购买权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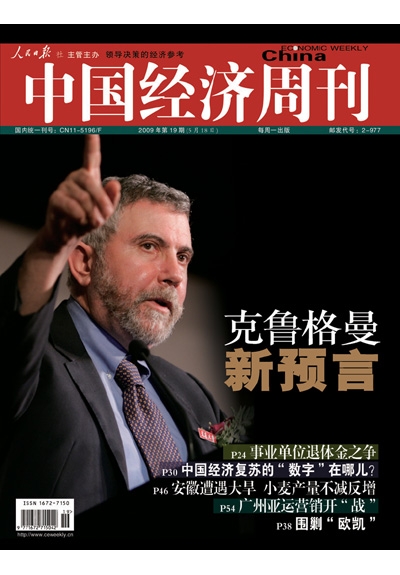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