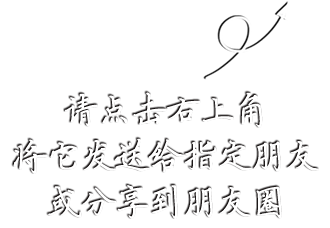韦署是突然病故的,一口气没上来,逝于法云寺的官舍。韦署有个独子叫韦式己,父亲意外离世后,他哽咽荒迷,不知所从。韦式己的两个妹妹,此刻仍在遥远的大西北,即使邮差快马加鞭,她们也要等上好几天,才能收到从扬州紧急发出的丧信。能够投寄的亲友,全在关中,这偌大的淮南,这空寂的佛寺,留给韦式己的,除了无尽悲泣,便是仰天摧绝。
韦署最后的官职是法曹参军,在扬州大都督府里,属核心僚佐,地位仅次于长史和司马。年逾七十,他才晋升到这个岗位。入府之前,他做过天长县丞,还曾到府里挂职,具体处理抓捕盗贼、畅通驿路等事务。
韦署没有私宅,他一直居住在法云寺的官舍里。不少异地就任的公职人员,他们当时来到扬州,生活上的落脚点,常与各大寺庙有关。法云寺位于罗城中央,水陆交通方便,市井风情璀璨,忙碌了一整天以后,这里是理想的休憩之所。
韦署的灵柩,自八月十三日到八月二十七日,在法云寺里足足停留了十四天。每天一抬头,不管有意无意,韦式己总能看到那两棵沧桑古桧,它们像巨伞,一左一右,撑在寺院门前。这两棵古桧,算算年纪,当时也应该有四百三十六岁了。
植桧之人,据说是东晋的谢安。坐镇扬州之前,他的身份,是高隐、大儒、宰相,于名门望族当中,他是一面迎风飘扬的凛凛旗帜。他的从兄谢尚,也就是著名的镇西将军,在扬州,曾有一座私宅。抵扬后,谢安简单收拾收拾,搬进了这座私宅。或许是对气节的推崇,或许是对长寿的渴望,亦或是要模仿孔子,要亲手兴建一组永放光芒的思想之塔,入住不久,谢安便在大宅门前,栽下了两棵令后世无数文人神魂颠倒的桧树。
谢安的姑母也住宅子里,她后来出家为尼。这宅子经几番改造,慢慢变成了一座规模可观的寺庙。姑母更名为法云后,寺庙也就跟着叫法云寺了。
法云寺的殿阁与厢房,屡修屡毁,唯有这两棵古桧,被风雨侵蚀了四百余年后,反而显得更加苍劲雄健。为了感念先贤之德,唐代那些赫赫有名的文士们,常借这两棵古树,追忆谢安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为扬州百姓所付出的努力。城北湖泊,每逢春夏,洪水肆虐,谢安克服重重困难,筑成了涝时能泄、旱时能蓄的平水埭。于是,大片农田连年丰收,低矮的屋舍可以高枕无忧。人们将谢安比作西周的召公,称其埭为邵伯埭,称其湖为邵伯湖。漫步湖畔的颜真卿,遥望古埭和祠庙,钦佩之情汩汩流淌,他摊开纸张,恭恭敬敬地写下了有名的《邵伯埭谢公庙碑》。此碑是中国书法史上的妙品,即使黄庭坚这样的大家日夜临摹,也不得其神。
法云寺的古桧,因谢安手植,因谢安筑埭,经过历史和岁月洗涤,早已超越了尘世。它在纷繁的古扬州城里,一次次为迷惘的民众点燃了希望。
刘禹锡见过双桧,它们郁郁葱葱,含烟吐雾,是禅客眼中的金殿,是将军阵前的画旗。从主干到高枝,双桧积满了力量,在空中如龙,在地上似象,它们往那儿一站,便是威严,便是依靠。张祜也见过双桧,那是一轴恬静的长卷:清晨,丹顶鹤落在树梢上,白眉僧朝新发的小枝贴面私语;入夜,秋云和树影轮番浮动,不一会儿,从风檐西边,传来了噼噼啪啪的雨点声。温庭筠有些谦逊,与双桧对视,他不敢题字,说得王羲之来,他也不敢作画,说那是顾恺之的活儿。大诗人遇到古桧树,竟像个孩子一样,变得胆胆怯怯。
双桧高峭入云,不论昏晓,均浓阴盖地。它们守在法云寺门口,文人的诗句能听得一清二楚,武夫的莽撞与对抗,也瞧得仔仔细细。法云寺的官舍,常要腾出一些,留给韦署他们,更多时候,尤其兵乱年份,这里真正的主角,一大半是各路军队。战事越烈,法云寺里便越喧闹。以至于一不小心,宋代的某一把战火,将这两棵桧树给呼呼烧尽了。
桧字,一解拨火棍。没想到法云寺门前的双桧,在看穿万事后,竟拨不了自己的火。韦署享年七十四岁,在唐人中算高寿;双桧被燃毁时,起码七八百岁,在树木中亦算高寿。可这一人一树之存,于苍茫世间,都不过是匆匆一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