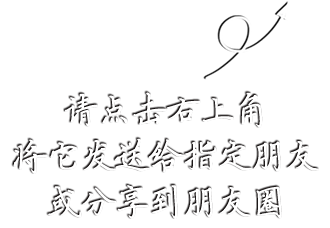几日的大雾散去,终于是迎来了太阳。
这天的阳光使我想起最近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话——“它们那灰色、黄色、脏兮兮的绿色顿时失去了阴沉沉的样子;仿佛心里敞亮了,仿佛浑身一震或被人用胳膊肘捅了一下。于是涌起新的观点,新的思绪……不可思议,太阳的光芒对人的心灵居然会有这么大的影响!”阳光这影响促使我想在室外待得久一点了,我甚至可以走远一点,沉溺于那使人心明眼亮的温馨环境中。
念头杂蹿间,过了刚才那个路口,我已经到了白塔寺门口。
与我想的一样,这个平常的下午过来,寺内果然没有多少人。阳光倒是越发热烈了,明明再过不久就要下山、隐去身影了,太阳却铆足了劲,向下极大范围地铺出一种平和的温柔。此刻,我和白塔寺都处于这种温柔中,顿时,我觉得自己有伴了。
前殿台阶旁有一棵古树,牌子上标注得清晰,它已然站了300多年。如今古树只剩下粗壮、敦实的躯干。它稳固而坚定地立着,外皮呈现深灰色的块状。它像一个专职守门的老人,只是这门,古树似乎已无力再守了。“它还活着么?”我摩挲着古树的身体,感到掌心一阵沉重。
走至大殿后门,就可以看见白塔尖从中殿屋顶露出来,似一朵出水白莲——它已经在提前迎接我了。我迫不及待地到白塔下,看清它的面目——这个元大都时期北京城的最高建筑物,已经在我心中披着面纱屹立了太久。
参观完毕走出中殿,白塔一下子填进了我的视线,我缓缓仰头注视它。不过离得越近,我越看不到它的上端,只觉得它饱满的腹部在将我的一切悲喜吸去。整个禅院内,周身显现图腾性白色的塔既仿佛一面关照情思的巨大镜子,映出了我空空的脑海以及瞬间安静下来的心。
塔下,有一个姑娘正双手合十,绕塔而行。我与她保持距离,亦缓步绕塔。我并没有将双眼紧闭,而是任由它收纳着景物,斑驳老墙、婆娑树影、五彩哈达……一切景物经由圆转轨迹,自我眼出入,化作云烟,往白塔顶端聚去。
忽而起风了,太阳更往西沉了。白塔无言,投下影子抱紧了我。
直至我走出白塔寺,立于旁边胡同内,远远望去,才得以领略白塔整体之相——塔身圆而带尖,似破土嫩笋蕴含生气;虽身处一隅,恬淡之气却紧裹周身,似一位饱经风霜又安然自得的智者,身体里潜藏着的都是智慧的秘语。
白塔周围的胡同居民区也很静。僧俗仅一墙之隔,寺墙里的平和之气也拂照了墙外的淡然世景。白塔寺周围的生活气,俨然一片裁剪整齐的粗麻布,质朴而本真。
我沿着塔根儿的一条胡同漫无目的地踱步,却十分贪婪地想要看遍胡同里、普通人家的每一处景观和每一个生活细节。公共厕所旁边聊天的老大爷们见我探头探脑地走来,突然不说话了,眼睛上下打量着我。等我走过去,他们可能便开始议论:“这大长头发不是咱们这的吧,瞎逛什么?”
胡同很窄、很静,过道里除了自行车、花圃、爬山虎和我之外,没有其他秃噜在外面的事物了,即便每个四合院的院门都是打开的。正是要做晚饭的时候,一位大妈突然从院门中走出来,手里提溜着一个用大矿泉水瓶改造的简易喷壶,向花圃里自己心爱的花花草草浇水。待花草吃饱了,她收走了门外晾晒着的豆角,转身回院了。一对夫妇回来了,他们是隔壁院的,女士手里提溜着豆腐,男士背着手,似乎在说着笑话。走到院门口,他们停下来了,低头看正在给电动车装篮子的小胖。小胖新买了电动车,还没来得及上牌,自己先把配件置办齐了。“真漂亮,真不错!”随着背手男士的一声夸赞,胡同口执勤的大爷也走过来了,看着这黑亮黑亮的新车,老大爷也开始夸赞了,并询问品牌价钱等信息。不一会儿,小胖就被五六位街坊围起来了,他还是认真地给车上配件,耳朵竖起来听大伙聊天,时不时抬头笑一下、搭个话儿。侧身绕过这段,我闻到了前面院子里飘出来的炒菜香味。旁边墙上的窄窗里,一对大手按着抹布上上下下——应该是在擦玻璃清洁。我正待凑过脸去,窄窗里突然换作一双大眼睛,她隔着玻璃看我,我隔着玻璃看她,而后,大眼睛消失了,抹布又出现了。这时我才注意到,使用抹布的不是一双大手,而是一对脚。孩子也放学了,爷爷奶奶牵着他们的手回家。刚一进胡同口,孩子们便猛地甩掉爷爷奶奶的手,朝胡同深处跑去。老人们叹了口气,习惯性地张了张嘴,朝着孩子们身影逐渐消失的方向喊了声:“慢点!”——也不知道这是他们喊的第多少句了。
我随着清洁师傅的车子走出了曲曲折折的胡同,店铺和人流出现在视野中,耳畔恢复了喧嚣声,大路旁的标识写着“赵登禹路”。我回头想要找白塔的身影,却已然看不见哪怕一点塔尖了,眼里只有通往未知与恬静流年的胡同口,那是生活的深处。我还看到一排排卫士般的大树,想要再寻白塔,得先通过它们。
华灯初上,胡同由闹变为静,不,它似乎从未太闹过,只是在夜晚更冷清了。初冬的风摇着,时间有序地流动着,白塔想必早已熟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