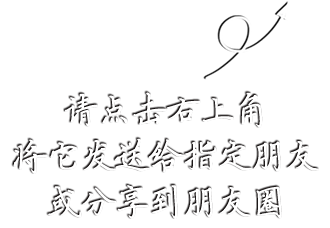仲春,小雨初霁,我沿着乡间小道,直奔清流关。
清流关距琅琊山十余公里,乡道路况不佳,正在修葺;村道狭窄,仅一车宽度。我问询一村民,他手指向不远处。循向看去,只见一座高大的石牌坊上镌刻“古清流关”。古驿道从此向北,大约两公里路便可达清流关。有不少小轿车不规则地停在路边空旷地带,许是游客前来探寻。
驿道有两米宽,地面由大小不一的石块耦合而成,一眼看去,相当平整;蹲下来端详,显得凹凸不平,与现代的水泥路和柏油路相差悬殊。路沿如刀切豆腐般齐整。路越走,坡度越大,几条车辙平行,深的有五厘米之多,像几条蛇游向关隘。从凹痕的间距来看,是马车留下的杰作;中间一条深约寸许的,像一根绳索,应该是独轮车的作品。技艺高超的车夫能娴熟地驾驭马车或推着独轮车,车轮刚好压着凹痕,一次又一次,一年又一年,日积月累,凹痕越来越深。沿着凹痕,省力省时。电影中,马车在驿道上奔跑,马蹄声声,车轮辚辚,似乎潇洒浪漫。其实,马车拉着货在石块铺就的路面奔跑,颠簸得很,车轱辘摩擦力大,费时费力,绝对是一件艰苦的差事。
从南唐至今,已越千余年,驿道路面保存完好,令人不可思议。山洪爆发,冲刷路面,多少年无人维修保养,竟然完好如初,怎能不令人惊叹称奇呢?石块之间到底使用了什么粘合剂才经久不坏呢?这是一个奇迹。现在科技发达,新材料层出不穷,路面正常养护,几十年不大修就不错了。古驿道的使用期明显比现代长——长得多呢!
《滁州志》载《清流关记》:“滁州之关山,上下十五里,由南至巅凡八里,由北至巅凡七里。”古代历朝虽毁坏了一些,但古驿道整体尚存完好,足可以说明这一带村民保护文物的意识强。听说,即使在困难年代,村民修建房屋都不取古驿道一块石头。
我一路走,一路寻,一路听,找寻古人的足迹,聆听古人的足音。有些石块上浅浅的水凼中,天光云影共徘徊。山间鸟语清脆悦耳,滴落在山坳的深潭,在山谷弥漫,惹得人思绪飞扬。路左侧的一株古树参天,伤痕累累,看样子树龄不短,与它们的祖先都是古驿道的见证者。路右边的山石更有特色,像一册册泛黄的书籍,风吹日晒雨淋,有些书页脱落。我真希望来阵强劲的山风,掀开书页,让我贪婪地阅读。我相信,只有如此古老的石头书页才能记载这里曾经的风云变幻。
到达清流关遗址,关楼不见踪迹,半券关洞尚存。洞深二三十米,高五六米,根基石块垒就,千年岿然不动。两侧各嵌一块两米高、一米宽的石碑,风霜雨雪腐蚀,字迹漫漶,难以获取多少信息。关的地面青石板规整,隔一段就有青石条高出一部分,大抵相当于如今的减速带吧。关隘南边根基处散落一些关楼的石构件,有的有文字、有的有图案。一个马食槽盛着一汪清水,可以让人联想到“车辚辚,马萧萧”的场景。础石一米见方,足见城阁关楼的崔嵬壮观。关隘北边陡峭,驿道在悬崖峭壁上延伸。
我拽着树枝,爬上高坡环视。清流山峭壁削立,峰高谷深,树木繁密,绵延数里,像一道闸割断南北。清流关南望长江,北控江淮,是古时人们由北方出入金陵(南京)的必经之地,被誉为“金陵锁钥”,有“九省通衢”等称号。
遥想当年清流关下,平时商旅邮货,设卡收税,一派繁荣景象;战时统帅派兵,攻守对垒,风云激荡。
由于地势险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在军事上,清流关的战略地位不言自明。宋太祖赵匡胤攻破李璟兵十五万于清流山下,生擒皇甫晖和姚凤;明太祖朱元璋率渡清流,灭张士诚;明末,李自成与明兵部侍郎卢象升激战清流关一带;清末,太平军罗大纲与清军胜保三千骑兵大战清流关……清流关是古时兵家必争之地,哪一场战斗不惊心动魄呢?
“潇潇寒雨渡清流,苦竹云荫特地愁。回首南唐风景尽,青山无数绕滁州。”读清人王士祯的这首《题清流关》,适合发思古之幽情,发人生之感慨。古人与旧事、战争与名利、历史与今天,总是明镜。
千年雄关不在,任凭你驰骋想象;千年驿道依存,任凭你触摸历史的脉搏。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哗与浮躁,有的只是原生态景致,以及淡定、安宁、静谧之气氛。微风不燥,阳光正暖,树影斑驳,在古驿道行走,恍如隔世,一幅幅商旅图、一场场战争画面,在我脑海里时而泛起涟漪,时而掀起波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