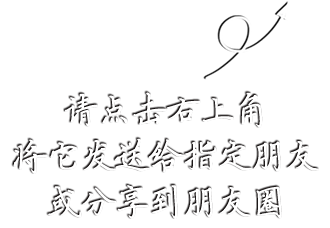南京最富浪漫气息的地方要数秦淮河。其源出溧水,西流至南京市东南,打通济门进去,从水西门流出,横贯了城市的西南角。河为秦时所开,故名秦淮河。近三十年前我因工作第一次到南京,就去夫子庙看热闹。那时十里秦淮,河水不甚丰盈,颜色亦不能用碧波来形容;朱自清笔下的桨声灯影、画舫快艇,都不曾遇见,未免沮丧极了。印象深刻的是牌楼上“天下文枢”四个大字,环肥燕瘦,宣示这是一座文学之都。
我怏怏回到长江大桥下的工地,碰见同宿舍的船工老张。他说:“小老弟逛庙会去啦?”我说:“嗯呐。”我们来自不同的省份,在这座城市里一起工作,相处甚得。老张是安徽人,开柴油机运砂船;我是工地上的技术员。南京的夏天热极了,歇工时,我们就跑到长江边游泳,或是聚在大桥下乘凉。老张会吹长笛,总吹一首曲子,旋律欢快,说是他们家乡戏里的;吹到响亮处,笛声常被铁桥上驶过的火车的隆隆声淹没。待火车过了江,他再吹时,我们就摆手,齐声喊:“扫兴,扫兴,还是散了吧。”
晚上,大桥旁边铁皮屋宿舍里不那么热了,我就着桅灯念闲书:“话说南京城里,每年四月半后,秦淮景致渐渐好了……到天色晚了,每船两盏明角灯,一来一往,映在河里,上下明亮……夜夜笙歌不觉。”在这不觉中,我的眼皮开始打架,便呼呼睡去。第二天,在工地上挥汗如雨,早把那“夜夜笙歌”忘了。老张记性好,听我念过几回,记住了。第二年春将尽时,他忽然提醒我:“技术员咋不去逛了?夫子庙的柳树兴许都抽条啦。”我说:“好呀!”
那一年春,雨多。雨点子不大,密密打在秦淮河上,泛起的涟漪一圈圈,扩到两岸的河房旁。河水涨了上来,有了载力,河面上新添了画舫和游艇。柳树果然已经抽了条,一树桃花盛开在乌衣巷口,附近的媚香楼也开张了。我在媚香楼买了本《桃花扇》,急匆匆赶回大桥下面。我想和老张商量商量,不如一起去撑画舫,能挣些外快。老张却不在工地,托工友留话说去运一船砂子,过两天回来。
老张这一去就是半月多,错过了大好机会。他回来时,运砂船上多了个人,是他闺女,叫喜妹。领导让我安排她在工地厨房帮厨。老张成天默不作声,我问喜妹才得知,她母亲得了重病,医治要花许多钱。大家都很同情父女俩。我看闲书,读到这几句:“行到那旧院门,何用轻敲,也不怕小犬哰哰。无非是枯井颓巢,不过些砖苔砌草。手种的花条柳梢,尽意儿采樵,这黑灰是谁家厨灶?”“你记得跨青溪半里桥,旧红板没一条。秋水长天人过少,冷清清的落照,剩一树柳弯腰。”我不敢念出来。
喜妹那时有十七岁了,衣服领口总是嫌紧,扣不上,前襟后片只齐到腰。袖子挽着,洗菜时露出粗胳膊。她腿长,走路快,吃饭快,从不跟其他男人讲话。一次,她向我借书,说她还想考一次大学哩。我没有课本,只能借给她闲书。她好奇问我,闲书和盖大楼有啥子关系?给我问愣了。但不久,我就挣回了面子。在新的大楼选址前,我建议单位避开城市中的古建,这样既不和考古队扯皮,耽误工程工期,又能保护城市文化,得到政府的支持。我的建议获得了领导的肯定。很快,我就成了工地上的“文化名人”。喜妹再刨根问底时,我含糊说某处恐怕是曹雪芹的家——但其实只是近代的建筑。她对我简直佩服极了,一天夜里,约我到大桥下面:“要不,你给我改个名字吧,我这个妹字,听起来可土了。”我想了想说:“改成妩媚的媚吧,等你满十八岁办身份证时,叫民警改成这个字。读音还是跟喜妹一样,你做的饭好吃,永远是我们的好妹妹。”喜妹说:“嗯,我记住了。”后半夜,老张还在大桥下面吹笛子,笛声欢快,吹得长江的波浪整夜里涌动。唉,他许是偷听了我和喜妹的谈话,又或是喜妹告诉了父亲改名字的事。
到了年底,大楼胜利竣工,单位召开了表彰大会。结束后,老张来找我:“你现在得志了,瞧不起俺老张了,可喜妹抱着你送的《红楼梦》,常常掉眼泪。”他第一次发了怒,并朝我的脚下吐了口水,以示绝交。那一晚,大桥下面,我没有听到老张的笛声。第二天清晨,我先是被大桥上隆隆的火车声吵醒,过后,忽然听到熟悉而欢快的笛声,远远近近,飘飘渺渺。我忙推门出去,看见江面上一艘运砂船正缓缓驶过大桥下面。船头立着喜妹,她已能代替父亲驾驶那艘老旧的柴油机船了。老张坐在船尾,横吹着手中的长笛,江风扯开白褂子,展露出他的胸膛。父女俩就这样离开了南京城。不久,我也离开了,告别了雄伟的南京长江大桥。
许多年后,我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老张头吹奏的那首曲子。那是南戏里的调调,曲牌叫作《相见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