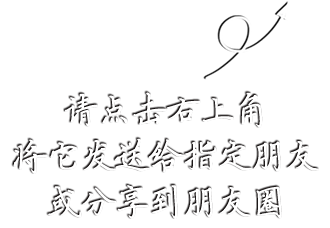风雨洗礼,布满沧桑;蔓草丛生,荒芜苍凉……瓦楞屋檐,升腾着一点一点的人间烟火气。吾乡老宅,那远远伸出的屋檐,富有弹性的屋檐曲线,由屋架形成的稍有反曲的屋面、微微起翘的屋角等屋顶形式的变化,以及在光线里闪烁的半明半暗的旧瓦,共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富有冲击力的视觉效果。
关于屋顶,德国哲学家皮珀曾有过这样的比喻:“激情和理想主义色彩的人头顶有两重世界,一重是星空,一重是屋顶。人在星空下生活,在屋顶下生存。”
的确,在星空下生活,在屋顶下生存,反映了两个奇妙的生命状态:星空是精神的,屋顶是现实的。人在星空下,可以浪漫,可以远眺,可以遐思,距离生成美;而在屋顶下,看到的都是清晰、真实的情景和细节。
有时候,屋顶是一个人生活的B面。我翻看一组老照片,翻到梁思成和林徽音于上世纪30年代的某一天,在北京天坛祈年殿屋顶的合影。一个是建筑学家,一个是传奇才女,两人并排靠坐,眯缝着双眼,打量着眼前的京华烟云,流露出一般人少有的率真之气。
抛开生活中的芜杂和烦恼,有人去关注清静的屋顶。夏加尔的画,多次描绘过巴黎的上空。他的鱼,在屋顶游来游去,杂技演员在空中行走,女人们在屋顶上飞翔。巴黎的屋顶在他的画笔下变形扭曲,象翻滚的麦浪——能调兑出那么浓烈的色彩,并将之涂抹到画布上的人,其内心,一定是梦幻且丰盈的。
民宅村落,一砖一瓦,透露出不动声色的美。乡村的屋顶,对于游走回眸的人,是一片鱼鳞细瓦的朦胧背影。古徽州山脚下的粉墙黛瓦,飘忽浓淡的水墨细烟。以至于有一只倭瓜,不喜欢睡在瓜棚中、豆架下,偏偏爬上屋顶四仰八叉,又不肯下来,确是为恣肆生长,找到了一处阳光充足、不受拘束的生活空间。在屋顶上晒谷物,人们把一年的收成高高地捧过头顶,内心有一种对天地植物的膜拜尊崇。有一年,我和朋友到皖南采风,车刚从山区公路下来,就看到有个中年妇女手拿一根竹耙,在房顶上翻晒玉米。老熟的玉米粒在阳光下泛着橙黄的光泽,那片屋顶,也就变成金黄色的屋顶。
城市的屋顶,包容着一个人静静欣赏风光的倒影。有段时间,我住进毛坯平房过上了简单粗糙的生活,曾不止一次爬上自家屋顶。我找来一架梯子,慢慢往上爬。说实话,往高处爬,我的心是虚的,双脚也不听使唤,紧张得直哆嗦。为克服一上楼顶就恐高的毛病,我尽量学会将眼光向远处张望,身旁和屋顶下的事物尽量不看。往远处看,目光与地面呈四十五度角。这样的角度,让我心里不再产生不安和恐慌。记得有一次,我竟然一屁股坐在倾斜的屋顶上,悠闲地点上一根烟,眯缝起双眼,深情地打量眼前这座油菜花般金黄的城市。
坐在屋顶,许多事物就看得真切。我跳出原来的圈子,隔着一段距离,俯看以前的生活,觉得自已的一切也就在这方圆几公里内——我的生活就像一个圈儿,熟人、熟物全在圈子里。我看到远处有一辆放着樱桃和杨梅的板车,摊主此刻正倚着一根电线杆子数钱。我看到有一户人家在门口生炉子,逸出的烟飘入空中,迎面走来的人,呛入烟尘,一阵咳嗽。我看到巷口有个老汉蜷在阳光下打瞌睡,隐隐约约能听到他的鼾声。每个老人都有着属于自己的难忘故事,只是这位老汉默默坐着打盹,他的故事也由梦乡出发,融入远处马路上嘈杂的市声里了。
诗人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可以看到更远的地方。我坐在屋顶上,回想我以前在地面上走路的样子,手提肩扛,身体前倾,重心向前;上楼捧着的是宝贝,下楼拎着的是垃圾。
那天,我站在屋顶,望到有个人在城市的河流上捕鱼。只见他坐在仅有方桌大小的简易小舟上,轻松自如地控制好平衡,悠悠地轻漂慢移。换作他人,稍不小心,或许早已一骨碌翻将河去。豆芥之舟,似乎已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布网和收网,嘤嘤作声,捕鱼人心无旁鹜。这实则上是一种大平衡:人与舟,动与静,一个人与他的内心。想到这,我一激动,忘了是在屋顶,大声和那人打招呼,他却没有听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