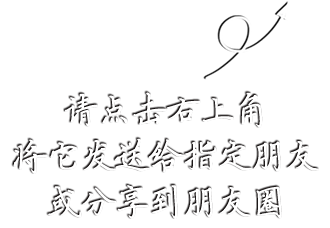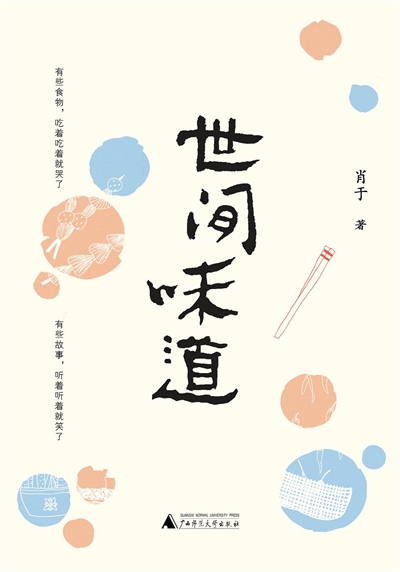 |
《礼记》有言:“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若换作今人之“心灵鸡汤”,即:人生短短几个秋,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吧。然而,身处“倍速”时代,“辜负”似为常态,唯诗家文人、游子迁客不思量,自难忘,愁肠九转念亲朋,味蕾深处是故乡——“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回不去的永远在想念。所谓思乡不过是一种告别——和旧光阴,和童年的自己告别。而告别充满疼痛。”作家肖于人在江南,心系东北,滚烫的泪珠无言地滑落,一颗又一颗,化为多情的文字,终凝成这本《世间味道》。
一个人的生命底色,总是可以追溯至童年和故乡。在年代与地域方面,亦可言在时间与空间的人生坐标系上,味蕾是无可替代的“原点”。即使你踏遍千山万水,尝尽世间百味,敏感细腻的味蕾却“恋旧”依然,像一把晶莹又湿润的钥匙,能够随时随地迅疾打开那扇直达童年、直抵故乡的记忆之门。肖于生于东北,长于东北,无疑,她的味蕾自然同人一样,极富“东北个性”,譬如,贪恋并醉溺于那些寻常的家乡小菜:糖蒜、酸菜、锅包肉、大拉皮、牛肉辣椒酱、清蒸哈什蚂……然而,若是单纯地将《世间味道》视作一本“东北美食散文集”,那又未免“只见树木”,失于偏颇。
诚然,谈及东北,我等外地人耳熟能详的,多半是二人传、《乡村爱情》以及“东北人都是活雷锋”等“招牌菜”。而我国传统餐饮文化历史悠久,论及选料、切配、烹饪等技艺,东北菜肴却并未能跻身为社会所公认的“八大菜系”之中,由此,我们自然不难理解,匠心独运的作者肖于委实是“言在此而意在彼”。通览《世间味道》全书,作者亦很少详描细绘每一道菜的制作过程,她本无意于做东北菜的“推广达人”。五辑作品,作者忆及的每一道家常小菜,通常只是一个“引子”罢了,因为文字背后立着的是人,是一段难忘的过往,是一个让人鼻酸心痛或含泪微笑的故事。咸、甜、酸、辣、鲜,姥姥、姥爷、小美、小胜、晓风、二爷、知青妈、全儿舅……菜肴五味,人生百味,无论时光怎么流转,不管世事如何变迁,在作者肖于的望眼与内心里,故乡的土,是喷香的;故乡的菜,是美味的;故乡的人,是最亲的!
在《世间味道》中,作者以情感为灶火、以文字为作料,精心烹制关于爱、关于痛、关于友情与成长、关于欢愉与忧伤、关于家族与故乡的记忆“菜肴”。当这道独具风味的“菜肴”端到了你我眼前,它早已突破了逼狭的区域限制与漫长的时光阻隔,让人目炫神迷,进而“大快朵颐”,最后在悠长的回味里,重拾童年的真纯,轻抚成长的印痕……在多数篇章里,作者叙事简明,直截了当。其语言明快,少修饰,“嘎嘣脆”,时时闪现着东北人特有的黑土地式幽默味儿。譬如,说到家乡人爱吃甜食:“五大三粗,光头戴金链子的文身大哥,带着穿貂的剥蒜小妹儿在烧烤店里撸串,很可能会突然对服务员说,给哥茶水里加点糖。”这画面感贼强啊,实在让人忍俊不禁。此外,在散文的形制下,作者却又常不动声色地融入了小说的笔法,融情入景,以景衬人,字里行间漫溢着温暖、温存与温馨,让人时不时地心弦颤而泪潸然。你看《酱》一文中描述:“姥的脑袋糊涂了,她却记得我。她说:‘姥老了,不能动了,但是你生个孩子,姥就在床上给你搂着,不让她掉到地下去。’……”明明是写“酱”,引出的却是姥姥,是深谙事理、勤劳能干的老人虽已糊涂、爱仍清醒的舐犊情深的人生素描。再如《酱茄子》一文:“大女儿慢悠悠地摘了最新鲜的紫茄子、绿叶子香菜、一根小葱和一大把小尖椒。太阳太晃眼,那孩子晃出了泪水,慢腾腾地流了一脸。太阳太大,泪水流下,就蒸发了,好像谁也没看到……”一碗家常小菜,几星红尘烟火,却道出了三姐大女儿报考中专失败后的无尽落寞与感伤,串起了三姐这个“知识青年”大半生命运多舛、悲苦煎熬,直至晚年才开怀忘忧、扬眉吐气的厚重经历……
“苦瓜微苦,莲藕清甜,白菜、胡萝卜、干豆腐各有各的味道,综合在一处,却依旧和谐适口。有点像我爸这一生,逆境顺境,全凭本事,全靠努力,把坏日子过好,把好日子过得精彩。”在《世间味道》中,与此类似的句段若春野繁花,随风摇曳间,馨香满心田。作者肖于是冷静、乐观的,她以温情又从容的文字向读者传达的是:那些不起眼的小菜,那些极平凡的亲邻,那些清淡普通的日子,皆已成为亲切的怀恋——“故事不多,宛如平常一段歌”,你渴望怎样的生活、喜欢怎样的味道,执著追求、矢志酿造便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