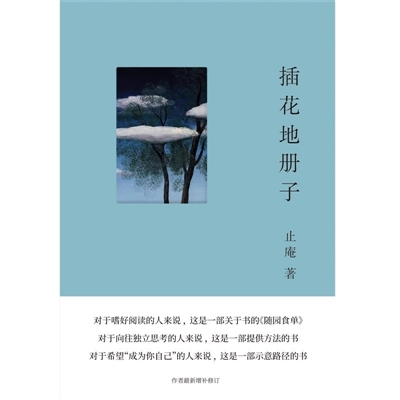“二十年前读《郑板桥集》,见其中有残篇曰‘刘柳村册子’。记述生平琐事,文笔好,这个题目也好。时间过去许久,印象仍然很深。此番追忆往事……我也学着弄个‘册子’好了。然而郑册成于刘柳村。自有一番机缘:而我半生居住北京……忽然记起‘插花地’这个词儿,插花地也就是飞地,用在这里是个精神概念,对我来讲,也可以说就是思想罢。”这是止庵对《插花地册子》书名来历的解释。读起来虽有些绕口,但饶有趣味,让我们在插花地里了解止庵。
止庵,作家、学者。在本书里,他回忆自己的阅读经历,对印象深刻的作品逐一评点,又在时间的经度和地域的纬度间勾连比较,指出作品好在哪里,或者糟在何处,评论各书自具慧眼,不跟风,不故作高深,平易亲切,耐人寻味。全书分为八章,从小时读书开始,再到少年的创作生涯以及师友之间的交往回忆,读小说、诗、散文等,止庵就像罗列《随园食单》一样,摆出一本本书。如序中所言,在范围和次序上都有很大欠缺,大体都是对读过小说的零散印象,但往往一语中的,大可作为一份寻找书的参考。
作者自小开始就读了很多书。“当然难免只是一鳞半爪,但集腋成裘,渐渐学到一些东西。”止庵说,如小时读《三国演义》,记住“依样画葫芦”;读《红楼梦》,记住“银样镴枪头”;读《水浒传》,记住“瓦罐不离井边破”……以此为基础,逐渐有了比较固定的对于历史、社会、人生的看法,以及养成一应兴趣、爱好、品位等。“将我具体的人生经验及见识与书上所讲的相对照,有如得到良师益友的点拨,人生不复暗自摸索,书也不白读了。假如当初我不读这些书,也许会成为另外一个人;正因为读了这些书,我才是现在这样的人。”
“书这个东西,根据年龄或阅读环境的不同,评价一般会微妙地发生变化……在这样的推移中,我们或许可以读出自己精神的成长与变化来。就是说,将精神定点置于外部,测算这定点与自己的距离变化,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确定自己的所在之地。这也是坚持阅读文学作品的乐趣之一。”这是村上春树《无比芜杂的心情》中的文字。止庵对此亦颇有感触:有的书昔曾视若珍宝,今却弃如敝屣。此亦如与人来往,有的一度密切,继而疏远,乃至陌如路人;有的则属交友不慎,后来幡然悔悟。不破不立,读书不违此理。
止庵读的第一部小说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他说:“我是不大喜欢这部书的,觉得一方面受历史的约束太大,以致纯属交代的内容太多;另一方面又多有编造,千万不能完全当历史来相信,此种写法流弊甚大。”关于《水浒传》,止庵认为这是中国古代最好的一部白话小说——中国古典小说描写总归较为简略,《水浒》也不例外,但是这里有限的描写却总能抓住要点……林冲误入白虎节堂,环境描写只有‘一周遭都是绿栏杆’这一句,却把他从未来过这里的那种新鲜感受给写出来了。这小说的语言似乎特别经过锤炼,一字一句都来之不易。
止庵的读书是一种系统性阅读。“多少年后我才明白,所谓散文不过是文字而已;对文字有文字的感觉,也就是散文了。”作者对五四以来的白话散文,更为留心。“大约五四一辈,只求实话实说,而这就特见性情”,譬如钱玄同谈论思想和经史的文章,率真激烈;刘半农的《半农杂文》和《半农杂文二集》,风趣滑稽,都是文如其人的。
“我这个人活到现在,差不多只做过读书这一件事,如果这能算件事的话。”止庵如此说。他毕业于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曾任医院医师、报社记者、外企工程师、出版社副总编辑等,现为自由撰稿人。止庵充分运用海量阅读带来的审美眼力,指导和磨练自己的文学创作。他去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受命》一鸣惊人,可以明显看出受莎士比亚《哈姆莱特》和张爱玲《倾城之恋》等名作的影响。作者的创作实践与他丰富阅读经历和典雅品位之间,形成了一个优美互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