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被称为“很好地将幻觉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结合在一起的中国作家”。自1981年发表第一篇小说《春夜雨霏霏》以来,来自山东高密的莫言一次次开拓中国叙事的广度和深度:从早期的小说《红高粱》,到具有先锋文学气质的《生死疲劳》《蛙》,再到近期的戏曲《锦衣》、组诗《七星曜我》……他的作品时常引起争议,但是从未让人失望。作为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获奖之后,他依旧以顽强的姿态生长在文学大地上,正像他书中所描写的人物一样,体现出无尽的生命力。“我们所熟悉的那个莫言又回来了,带着他的力量,带着他那样一种悍然不顾,非常强劲的力量又回来了。”人们如此说道。
这种力量从何而来,又将归于何处?“一张邮票大小”的高密东北乡究竟蕴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从古代齐国腹地走出来的小说家,他的内心世界与我们的想象又有多大的距离?
宫梓铭:我个人认为您的《欢乐》和《球状闪电》在这方面登峰造极。《球状闪电》里面那位鸟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此夸张的意象,也有其现实基础吗?
莫言:《欢乐》里面确实有一定的夸张,但这种夸张还是基于现实,而《欢乐》里面我描写的生活还是我比较熟悉的。
1985年,我写出了《透明的红萝卜》《爆炸》《枯河》等一批小说,在文坛获得了名声。1986年,我写出了《红高粱家族》,确立了在文坛的地位。1987年,我写了《欢乐》和《红蝗》,这两部中篇小说则引起了激烈争论,连许多一直肯定我的评论家也不喜欢我了,我知道他们被我吓坏了,很多人开始了猛烈批评,小说夸张地、赤裸裸地描写激怒了读者,他们觉得我是故意狂妄地亵渎了母亲。
其实《欢乐》表达了我对美与丑的思考。我觉得,美与善是需要节制的,节制的美才是最美的,含蓄的美才是最耐人寻味的。我为什么要把丑和恶进行一种狂欢式的夸张式的写法呢?丑和恶本身就是人性当中很有意思的一部分。实际上,我们能从丑和恶当中惊喜地认识到美的可贵,或者说丑和恶是人性当中的一面镜子,既能照出它自身,又能反衬出它的对立面。我想我的小说里面很多小人物都是不美的,从外形到他们做的一些事情,但他们灵魂深处依然有美的因素存在。我们只有把人性的丑与恶写得充分,才可以更容易看清楚人性的美,才能显出美与善的可贵。
写《球状闪电》这篇小说时,我已经读了马尔克斯的短篇小说《巨翅老人》。他的故事是有一天下大暴雨之后,突然家里来了这么一个老人,长着翅膀。他也没说这老人来自哪个地方,也没说他最终去了哪里。我在《球状闪电》里也写了这么一个老人,写作时联想到了自己的一些经历。我小时候村子里面确实是有这么一个老人,觉得自己拥有仙术,随时可以飞起来。他经常在自己身边烧很多的纸。到最后他的身体都垮了,还在天天画符念咒,烧成灰再喝下去,然后在周围点上蜡烛:“噢,飞起来了,飞起来了,飞起来了”。
关于你说的写作的“现实基础”,我是从我的村庄获得了很多“灵感”。那是胶县、高密、平度三县交界的地方,我父辈生活的村叫大栏。60年代的时候,那里水特别大,那时候我六七岁,脑海里印象最深的东西,第一就是水,我家后窗一推开,就能看到河水滚滚东去。有一年在家休假时,我睡到半夜,看到月光从窗棂射进来。我穿好衣服,悄悄地出了家门,沿着胡同,爬上河堤。明月当头,村子一片寂静,河水银光烁烁,万籁俱寂。我走出村子,进入田野,左边是河水,右边是看不到头的玉米和高粱。所有人都在睡觉,只有我一个人醒着。我突然感到占了很大的便宜。我感到这辽阔的田野,这茂盛的庄稼,包括这浩瀚的天空和灿烂的月亮都是为我准备的。我感到自己很伟大。
在故乡的那些月夜里,我自然没有找到什么灵感,但我体会了找灵感的感受。好的作家虽然写的很可能只是他的故乡那块巴掌大小的地方,很可能只是那块巴掌大小的地方上的人和事,但由于他动笔之前就意识到那块巴掌大的地方是世界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那块巴掌大的地方上发生的事情是世界历史的一个片段,所以,他的作品就具有了走向世界、被全人类理解和接受的可能性。好的作家,总是千方百计地使自己的作品具有更加广泛和普遍的意义,总是使自己的作品能被更多的人接受和理解。
宫梓铭:我最近在网络上看到了很多“鸡汤”,都号称是您说的。您怎么看新媒体平台?说实话在海量信息中,看到您对各种事物的指点,感觉挺“魔幻”的。
莫言:好多人都问是不是我说的,但那些东西真的不是我说的。手机耗费精力太多,不开微信确实也不方便,开了微信以后,有时候也陷入到朋友圈里去。有的信息确有价值,但大多数信息毫无意义。
信息太多了,并无益处,等于是信息消灭了信息。真真假假,有很多东西看起来让你不得不信,但是后来也证明是假的。一个人的时间,是恒定的一个常数,一天也就24个小时。一生也就那么多天。你真要做一点事的话,那肯定是应该从这漫无边际的信息里面逃出来。现在都说,自从有了智能手机之后,时间变得特别快,低着头捧着手机一看,一下午就没了。以前飞机晚点时,那种焦虑的等待,让人很痛苦,现在拿着手机,倒变得反而是一种愉快的享受了。我注意到在机场,大人在看,小孩也在看,每个人都在忙自己的,都在玩手机,真的是谁也不理谁。
宫梓铭:之前我看过一个新闻,说有一群人在网络上搞了一个人工智能机器人,然后让它写小说,写了1.2亿字。
莫言:这种花了一小段时间就生成出来这么大段的东西,叫做智能写作,对吧?我看过它们写的诗歌。机器人写的诗歌,模仿唐诗。从技术上来讲完全符合律诗要求,平仄格律都没有问题,但就是没有感情,没有个性。
我比较保守,总觉得这样生产出来的东西,不是真正的文学。就像刚才我们讨论的智能机器人写的唐诗一样。从技术上来讲,它符合律诗的所有要求,但是它没有创造性。另外它没有诗人那种鲜明的个人特征,它能生成一首诗,但生出不新的情感。一个活人写的哪怕平仄全错了,它还是有人的情感在里面,至少还有要表达的一种感觉。机器是不会犯错误的。这种机器写出来的小说,肯定是快,但我想,作者比较自信的一个原因是——我写的不如你写得快,甚至不如你写得好,但这是人写的东西,是有人气的。
时至今日,我感到人类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日益先进的科技与日益膨胀的人类贪欲的结合。在人类贪婪欲望的刺激下,科技的发展已经背离了为人的健康需求服务的正常轨道,而是在利润的驱动下疯狂发展以满足人类的——其实是少数富贵者的病态需求。当所有人都“抬不起头”了,就形成了科技对所有人的控制。人的所有时间都束缚在一个小小的物体上、一个屏幕上,孩子、老人都一样,谁能想到呢?过去我们认为电脑的发明会使人得到解放,我们会抬起头来。结果,现在更可怕了。
宫锌铭:这就是为什么您提出文学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莫言:是的。在这样的时代,我们的文学其实担当着重大责任。
我们应该用我们的文学作品让人们记起来,在人类没有发明空调之前,热死的人并不比现在多。在人类没有发明电灯前,近视眼远比现在少。在没有电视前,人们的业余时间照样很丰富。有了网络后,人们的头脑里并没有比从前储存更多的有用信息;没有网络前,傻瓜似乎比现在少。
我们要通过文学作品让人们知道,交通的便捷使人们失去了旅游的快乐,通讯的快捷使人们失去了通信的幸福,食物的过剩使人们失去了吃的滋味,性的易得使人们失去恋爱的能力。
我们要通过文学作品告诉人们,在资本、贪欲、权势刺激下的科学的病态发展,已经使人类生活丧失了许多情趣且充满了危机。
我们要用我们的文学作品告诉人们,维持人类生命最基本的物质是空气、阳光、食物和水,其他的都是奢侈品。当人们在沙漠中时,就会明白水和食物比黄金和钻石更珍贵,当地震和海啸发生时,人们才会明白,无论多么豪华的别墅和公馆,在大自然的巨掌里都是一团泥巴。当人类把地球折腾得不适合居住时,什么国家、民族、股票,都变得毫无意义,当然,文学也毫无意义。
我们的文学真能使人类的贪欲,尤其是国家的贪欲有所收敛吗?结论是悲观的。尽管结论是悲观的,但我们不能放弃努力。
因为,这不仅仅是救他人,同时也是救自己。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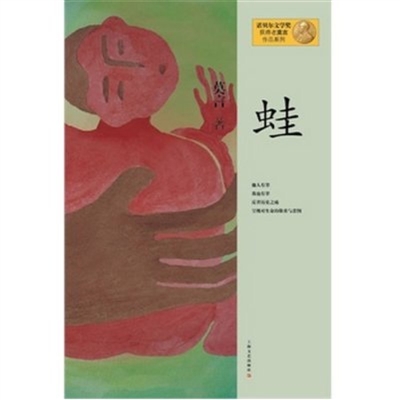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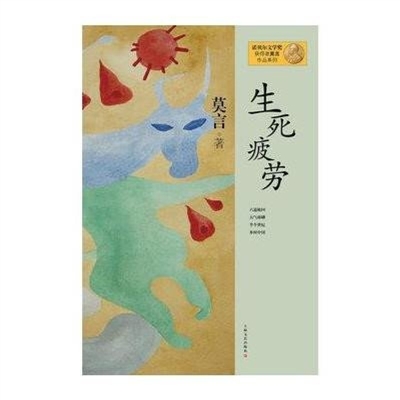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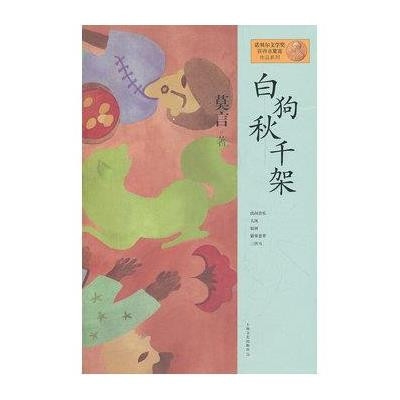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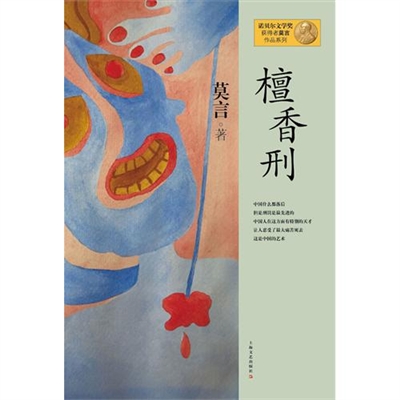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