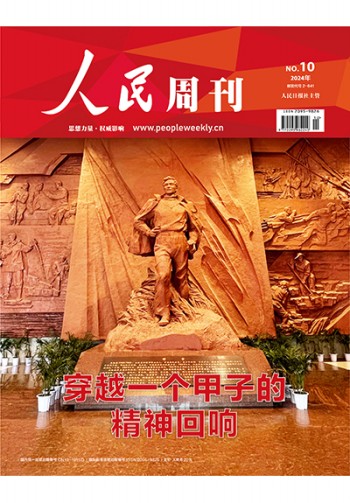徐悲鸿批评“中西合璧”实为“中西合瓦”
林风眠主张东西方艺术相糅合以登高峰
徐悲鸿的爱国主义似乎更强。1947年,他在《当前中国之艺术问题》一文中说:“……若此时再不振奋,起而师法造化,寻求真理,则中国不亡,而艺术必亡;艺术若亡,则文化顿黯无光彩。起而代之者,将为吾敌国之日本人在世界上代表东方艺术。诸位想想,倘不幸果是如,我们将有何颜面以对祖宗。”他又说:“艺术家即是革命家,救国不论用什么方式,苟能提高文化,改造社会,就是充实国力了”“不过中国倘真不幸,没落到没有一样东西出人头地时,我且问你,你那世界主义,还有什么颜面”。(王震编,《徐悲鸿文集》,第139页)
徐悲鸿强调,要发展中国画,要改良中国画,创作以中国画为主。他不能容忍“中西调和”,更反对“中西合璧”,甚至把“中西合璧”说成是“中西合瓦”,并力主“中西分璧”。1931年1月,他发表《悲鸿自述》,其中说道:“吾爱画入骨,以爱画故学画……一九二七年秋返国,倡写实主义,为求真之运动,抨击欧洲惑人耳目之牟利主义。主张中西分璧,时国人徒知中西合瓦。”(徐悲鸿,《徐悲鸿自传》,上海《读书杂志》,第3卷,第1期,1933年1月)
他又说:“故建立新中国画,既非改良,亦非中西合璧。”(徐悲鸿,《新国画建立之步骤》,《徐悲鸿文集》,第139页)
“合璧”是两件美好事物之结合;“合瓦”则是简陋低贱的结合;“分璧”是分开则为璧玉。可见徐悲鸿对中西结合的态度。
其实,几乎所有真正的思想家都不提“中西合璧”和“中西结合”,因为那是没有主体意识的。毛泽东提“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张之洞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严复认为一切外国学术都只能为中国所用,鲁迅提“拿来主义”,等等。在近现代艺术家中,徐悲鸿是最有主体意识、最有思想的一个人。
严复也说:“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上海《外交报》,第九、十期,1902年。又见《严复集》册三)
徐悲鸿从没有提出“中西结合”“中西融合”“调合中西”“中西合璧”一类话,因为那没有主体意识。但是,徐悲鸿是主张借鉴西洋画的,尤其是素描,他一生倡导写实主义,力主“素描画为一切造型艺术之基础”。他反复说:
“欲救目前之弊,必采欧洲之写实主义。”(徐悲鸿,《美的解剖》,《徐悲鸿文集》,第13页)
“素描为一切造型艺术之基础。”(徐悲鸿,《新国画建立之步骤》,《徐悲鸿文集》,第139页)
“吾学于欧既久,知艺之基础也惟描。大师无不善描,而吾尤笃好普吕东描之雄奇幽深,坚劲秀曼。国人治艺者已多,其亦有吾同嗜否?爰首布之,征吾国艺人之尚焉。”(徐悲鸿,《徐悲鸿绘画集·序》,载《徐悲鸿文集》,第6页)
“研究绘画者第一步工夫即为素描,素描是吾人基本之学问,亦为绘画表现唯一之法门。”“素描在美术教育上的地位,如同建造房屋打基础一样。房屋的基础打不好,房屋就砌不成……因此,学美术一定要从素描入手,否则是学不成功的。”(徐悲鸿,《在中央大学讲演辞》,《徐悲鸿文集》,第15页)
“吾个人对于中国目前艺术之颓废,觉非力倡写实主义不为功。”(徐悲鸿,《在大同大学讲演辞》,《徐悲鸿文集》,第16页)
和林风眠一样,徐悲鸿也认为当时的国画“颓败”,必须用西方素描的方法加以改进。但这不是“调合”,更不是“结合”,而是借来为我所用,中为主,西为客、为次。用素描来丰富国画,但仍然是国画,是有围墙的。西画可以进入围墙内,但只能化为中国画的一部分,或者作为营养被中国画所吸收。不可与国画分庭抗礼、平等地列于围墙内。
徐悲鸿强调中国画家必须发展中国画,抗战时,他这一情绪更为激烈。
日本侵略中国,当时的日本军事先进,中国落后,很多人认为中国必亡。毛泽东《论持久战》中专列一节《驳亡国论》,他说:“亡国论者看到敌我强弱对比一个因素,从前就说‘抗战必亡’,现在又说‘再战必亡’。”(《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18页)这也说明当时很多人认为中国必亡。即使是爱国的知识分子,也认为中国必亡,因为日本当时太强大了。《吴宓日记》说:“……(陈)寅恪谓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一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云云。寅恪之意,盖以胜败系于科学与器械军力,而民气士气所补实微。”(吴宓,《吴宓日记》,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册,第168页)由此可见一斑。当时一些知识分子认为中国必亡,还有一些口中不说、笔下不写,但心里有数。国亡了,怎么办呢?几百万军队都无能为力,手无寸铁的书生又能怎么办?熊十力说的一句话最有代表性:“一个国家,文化不亡,则国不亡。”所以,爱国的知识分子都一致强调中国文化,国粹派倍受欢迎。最早强调“全盘西化”的胡适,这时也不再提“全盘西化”,而反过来强调“整理国故”。他也身体力行,自此坚持研究传播中国古代文化传统。比胡适更强调“全盘西化”的陈序经也不再提“全盘西化”,反而在现实中更强调“中化”。傅斯年等一批人也不提“全盘西化”,反而反复强调“国故”。黄宾虹等人也都强调中国特色的国画,他们都抱着一颗赤子之心。中国灭亡了,中国的文化如果也西化了,那就彻底亡了。因此强调中国的文化,只要中国的文化在,中国就不亡。中国画就必须是中国画,不能变为西洋画,也不能“中西结合”“中西合璧”。
徐悲鸿的爱国热情十分强烈。在他的文集中随处可以看到他的爱国热情,他还写了《誓死以抗强暴,再来肃清国贼》等文,他的题画诗文中常见到他为国事“忧心如焚”等句。他画鹰题:“长沙战事,忧心如焚。”“日前,神鹰队袭汉口倭机,毁其百架,为长沙大胜余韵,兴奋不已,写此以寄豪情。”画狮题:“危亡益亟,愤气塞胸,写此自遣。”画马也题此句。画白皮松题“乙亥危亡之际”。画猫题:“故国灰烬里,国难剧堪悲。”画马题:“辛巳八月十日第二次长沙会战,忧心如焚,或者仍有前次之结果也。企予望之。悲鸿时客槟城。”(徐悲鸿纪念馆编,《中国艺坛巨匠——徐悲鸿》,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05年版,第288页)他在马来西亚卖画支援抗战,仍对长沙会战“忧心如焚”,可见他爱国之情怀。所以,他不能容忍“中西平等”“调合中西”等论。他声明自己学西画是为了发展中国画。他强调的是中国画。所以,他的体系中的杰出画家多是中国画画家。
徐悲鸿弟子多中国画画家
林风眠学生多西洋画面貌
1962年,林风眠62岁了,仍然教育学生:将西方艺术的高峰和东方艺术的高峰糅合在一起,才能摘下艺术的桂冠,登上世界艺术之岭。(林风眠,《林风眠画语》,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109页)
林风眠至老仍然认为艺术是不分中西的,对中西无主次之分。
吴冠中则以90岁高龄,仍力倡“推倒中国画的围墙”。
徐派杰出画家李可染则以81岁高龄,强调:“我画了70年画,一直在前进。有人说:‘李可染还要再跨一步。’我说:‘跨进一步是可以的,但不能跨到西洋画那里去。’”
李可染还说:“吾画扎根祖国大地,基于传统,发展于宏观世界。人谓吾画为国画印象派,吾不能然其说。早岁吾学过几年西画,……但吾转觉我国自有光辉文化体系,独特表现形式,学习外国旨在借鉴丰富自己,若因此妄自菲薄而卑弃传统,吾深以为耻。”(“世纪可染”组委会编,《世纪可染——纪念李可染诞辰一百周年特刊》,2007年版,第246页)他对待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是颇有自豪感的。而且,他对中西的主次分得很清楚。
吴冠中则反复说他“有意无意地崇拜西洋画”,当油画颜料不易买到时,他被迫转学中国画,但他“仍迷恋西画的色彩”,马上又改学西画了。他还说“初学时都喜欢西洋画……年轻时候喜欢强烈狂放的色彩,如粉红、粉绿”。(吴冠中,《吴冠中文丛》,团结出版社,2008年版。转引自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东西冠中》,第365页)他一直是以西方画而“他豪”。以西画为主,以国画为次。
一方要拆毁、推倒中国画的围墙,只要画得好,无所谓是否是中国画;一方则要加强中国画的围墙,强调要发展的一定是中国画。几十年过去了,林风眠系的画家如朱德群、赵无极等人成为法国科学院院士,他们的作品证明了西洋画有一定的发展潜力。徐悲鸿系统的画家,包括蒋兆和、李可染等人的作品,证明了中国画有一定的发展潜力。可见,徐悲鸿、林风眠之艺术主张不同,其影响、结果亦大不相同。
(本文为新时代美术高峰课题组、中国画“两创”课题组专稿)